埃德温·马厄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首位外籍新闻主播,来中国之前是墨尔本家喻户晓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和天气预报员,已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从事播音工作长达二十多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五十多年的记者和播音主持经验。2007年荣获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友谊奖”,2012年被中国授予拥有永久居住权的绿卡。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中国。没想过要去中国度假,更不用说去那里工作了。我们家的一个朋友从1985年开始就常去中国。我们都觉得纳闷,他到底觉得那里有什么好东西,老往那里跑。当时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无非就是:那里人特多;从那位朋友给我们看的照片上,上海和北京这两座最大的城市看上去灰蒙蒙的,人们都穿着灰色的衣服,头顶着灰色的天。我妻子萝宾和我丈母娘想让我跟她们一起参加一个七天旅行团,亲自到中国去瞧瞧,我没答应。
殊不知我来中国的因缘,是相濡以沫33年的妻子萝宾得了可怕的肿瘤去世。从妻子葬礼的那天开始,我的人生失去了方向。曾经上门帮助我们的医务人员都离开了;孩子们都大了,各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使我倍感难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份去中国给主持人做语音培训的工作。2003年5月22日,我登上了去往中国的飞机,想着今后要到新的地方,认识跟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的新人,觉得心情好一点了。没有人会问“最近应付得还行吧”这样的话,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说我的个人情况,更不用说关于萝宾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在座椅里放松了下来,等待着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这次旅程,将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旅程。
率直的中国人
中国人说话很直率,甚至跟外国人说话也是如此。问别人年龄和收入,不像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不礼貌。没有等你邀请就到你家造访,在朋友间很常见。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只是,如果你由于某种原因不方便,而你朋友突然来访的话,那就有点尴尬了。我的中国朋友要来看我的话,会提前几天打电话告诉我;但有时候,他们会当天来电话,说他们方便(至少对他们来说如此)过来看我,“就今天”。
我特喜欢中国人结束电话的方式。他们说话很快,我在电话这一头总是听不明白电话另一头讲的是什么,但是很容易听出电话什么时候突然结束。因为通话快结束时,他们会说“嗯,嗯,嗯”或者是“啊,啊,啊”,然后语速越来越快,最后是一声快速的“拜拜”,而不是以前比较传统的“再见”。
关系亲密的女性朋友一起走路时,在单位也好,在外面也好,手牵手是很正常的。2003年我来中国时,在北京常常看到男人手牵手走路——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同性恋的那种。不过,现在比较少见了。这在一些边远地区更常见,我就有一个中国“侄子”,是四川人,在北京工作。跟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性地抓着我的手。有一个在友谊宾馆工作的朋友,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不过,每次我们一起吃过饭,喝完几大瓶啤酒,离开餐馆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手来让我握着。
徐东海是我的中国家人的男主人。有一天我们一起散步时,他拉起了我的手。他儿子笑了,从后面戳我们俩,说我们是“同性恋”。于是,我们飞快地松开手。由于时代的变迁,表达纯粹的友谊的传统都被搞坏了。
不过,中国有一个传统禁忌是关于戴——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戴绿帽子的。我有一顶帽子,帽舌上有澳大利亚国徽,我以前常戴这顶帽子。有一天,我戴着它去上班,同事看到了,他问:“你知不知道中国人说戴绿帽子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了?”我问道。他故作严肃状,不过掩饰不住眼里的笑意,说道:“戴绿帽子的意思就是说你老婆或者女朋友对你不忠。”
我向同事抗议道,至少我的帽子边是黄色的。于是,他只好投降:“那么应该就不算吧。”不过他眼里的笑意更加明显了。我必须承认,友谊宾馆的一些保安看到我戴这顶帽子的时候,表情也很奇怪。不过,关于这顶帽子,我可以算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因为帽子里面的标签上用英文写着:“中国制造。”
尴尬的礼物
在西方,包礼物和拆礼物同样让人兴奋,特别是送礼的人看到接受礼物的人的表情(当然希望是高兴的表情)。说起送礼,中国人是最会送礼的。不过,在中国送礼,通常不包装礼物,而是用一个有装饰作用的纸袋子或者塑料袋把礼物装在里面。接受礼物的人打开袋子,很容易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带有品牌标识的盒子或者袋子。
在参加同事的生日聚会时我注意到,接过礼物的时候,寿星不会立刻看里面是什么,他们通常回到家后再看。当着别人的面接过礼物,然后将礼物打开,这似乎会让送礼的人觉得礼物不够好。回去拆礼物就避免大家丢面子。
中国人很喜欢互送礼物。在重要的节日,如春节,互相送礼可能有点让人吃不消。送礼也有尴尬的时候,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送月饼。似乎每个中国人都买月饼,但是我问过别人,回答通常是(轻声地):“我不喜欢吃。太甜了。”收到月饼的人,通常会转送给别人。这就可能会出现尴尬,送出去的月饼,就像澳大利亚的“飞去来”一样,最终又转回到自己手里。有时候,有一阵子没见的朋友可能会登门拜访,顺便送上最近出远门时带回的礼物,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会带礼物过来。刚来中国的前一两年,我一直拿不准,是不是出门拜访朋友时得带个礼物,或者是不是得在家里备好礼物,如果有人来家里顺便带了礼物,我好还礼。
有一次,我去贵州,在去省会贵阳的车上,司机半路停车加油。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个墨绿色望远镜,放在座位上。这是他在加油站买的。我问能不能借我看看。这时我犯了个错误,我说“真不错”,“我也应该买一个。”司机咧嘴笑了,说:“这是给你买的。”我知道他是客气,尽管我很不好意思,推了好一阵子,但他坚决要我收下。结果,那望远镜是我的了。
填塞中文汉堡
在央视英语新闻频道,我用我最熟悉的中文来开始和结束播音。我这样做,是给节目贴上自己的标签,同时也是出于对中国观众的礼貌。开播时我会说“你好”,结束时我会说“再见”。没有其他播音员侵犯我的这个“专利”。有中国观众遇到我对我说,他们很高兴我在全英语的节目中用中文,让他们觉得更有参与感。有的中国观众还说,我的中文一定说得“很好”。不过,早期有些外国人在网上评论,说我发音不准,把“再”说得像“赛”。
我把我的中文比作汉堡包,最上面是“你好”,最下面是“再见”,中间是一层薄薄的填充物,尽管每天我都会尽量加一点语言佐料。
近十年来,我买了很多书,录音带,DVD和CD,都是关于如何说中文的,也有其他的,但是没这么多。我专挑那些“简单速成”的教材。有一次我从澳大利亚度假回中国时,在香港机场的一家书店里我以为找到了答案。有一套叫《边走边学中文》的双CD教材牢牢地吸住了我的眼睛。封面的广告更是将我死死钩住——“让你充满信心地说中文——速成”。那套教材有段时间好像挺管用,不过几个月后,我就没了兴趣。其实,我是想给自己这样的懒学生找一条学中文的捷径。
《今日亚洲》节目的一个中国制片人听说我在学中文,就过来问我:“你为什么想学中文?我们喜欢这样的你,再学会改变我们对你的感觉的。”他的这番话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也许潜意识里我就用这个作为借口,不再那么努力学中文了。
2006年,有个住在北京的瑞典商人库尔特•贝里斯特伦给我打电话。他看到一个关于我的采访,在采访里我抱怨跨越不了语言障碍。他在北京创办了一所学校,是教比较“年长”的外国人中文的。这些人刚来中国的公司、使馆或者其他机构工作,可能会在学说普通话的过程中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贝里斯特伦提出让我免费上课,把我作为以后学员的“参考”广告。
接下来的三个月,有两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来我的公寓,让我从最基础的中文开始学。我学会了自我介绍,日常会话,还能够谈论我要回澳大利亚参加女儿婚礼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很自信,所以后来2007年我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友谊奖做获奖感言时,开场白用了几句中文。
中国式手语
刚开始跟中国人交流时,我不仅用上了嘴巴,而且用上了手跟脚,还有其他任何能使别人明白我意思的身体部位。使用中国手语的想法是我来中国后不久萌发的。有一次搭乘地铁的时候,在车厢的另一头,有一群年轻人谈得热火朝天。不过,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更不用说有音调了。他们都是听觉和说话方面有残障的人。
他们用手语表达,倾听,似乎没有词汇方面的障碍,这启发了我。第二天,我想买一双鞋,就去超市找。超市里的售货员通常比顾客还多。在一个塞满鞋子和袜子的货架那里,我没找到鞋带,只好开口问旁边的售货员。
我朝一位女售货员走了过去,问:“你有吗?”接着指着我的鞋带。我还提起鞋带,以清楚表明我要的是鞋带,不是鞋子。“没有。”她回答道。至少我知道不用再找了。但我还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该有鞋带的地方没有鞋带卖。
我在中国的长途旅行,最早去过东北的工业城市辽宁省的沈阳。那次从北京飞过去,很晚才到,我得找个地方过夜。出租车很容易打,我跟司机说要找一个宾馆,也不难。当他问我“去哪儿?”时,我的手语起作用了。我双手合十,头侧向一边,闭上眼睛。司机看着我,毫无疑问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是他心里肯定在想:他载了一个疯子老外。
刚开始还有一次,我想表达我的意思,但未能成功。一次经过北京老城区的一家家用器具商店时,我想起我需要买一个打蛋器。我几乎翻遍了整个店,但还是没有看到打蛋器,于是我准备用手语沟通。那个时候,我大脑里的词汇储备空间里还没有什么存货,只好完全靠手语,结果还是让那位老板不知所云。
我从货架上拿过一只碗,让他看我手心,然后,手翻过来将一个无形的蛋敲进那只真碗里。我举起左手,好像握住打蛋器的上端,右手握住把手,开始摇。老板看得一愣一愣的,完全懵了。然后,他耸耸肩,咧开嘴笑着说:“我不明白。”我怎么那么傻,应该带几个真蛋才对嘛。
(摘自《找得着北——央视洋主播的新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5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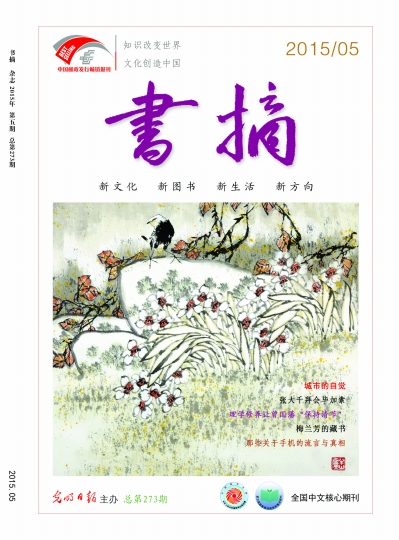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