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1年出版的《欧洲的天才》一书中,霭理士注意到,再没有什么比建筑艺术中的“拱门”,更能揭示矛盾的元素如何最终支撑起和谐的艺术:两股原本互相对立的势能彼此支持,以致达到稳定圆融,若有一方撤离,则拱门坍塌,不复存在。对梁平诗集《深呼吸》的阅读,亦如躬身从拱门中穿过。只是,那并非“此门向前,是宙斯王国”的雅典哈德良拱门,而是一座蜀地形制、精工细雕的古典朱漆拱门,上或有云龙浮雕的匾额,进一步是高堂明镜朱红印章之壮怀激烈;退一步则江湖游走,酒气浮动之慷慨悲歌。进退之间,书生与政治,高衙与江湖,金石与水气,构成了梁平诗中相悖相谐的不同努力与质地,在力量制衡当中,最终生成了他特有的既阔大又精微的格局。
人类的修道,无非“向外求”和“向内求”的两条路径。《深呼吸》中,诗人两手兼顾,其博闻强识,掌故频出。一方面以经世致用的目光回溯历史,诗句通向北宋通向南北朝;另一方面又存有周作人津津乐道的“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
既有史学之难度,又有文化之把玩;既有经史之重,又有性灵之轻,这一切需要诗人具备超高的跳台和精湛的手艺。梁平在访谈中曾谈到“题材必须具备进入高度”,他自己也有意识将“对这个民族的大思考植入自己的写作中”。与此同时,某种天赋秉异令他传承了某些古典秘方与技艺,在一粒粒汉字中炼出仙丹。《说文解字·蜀》、《惜字宫》、《犍之为犍》等诗,都显示出诗人寻找汉字源头的努力。解释“蜀”字时,诗人写道:“东汉的许慎说它是蚕/一个奇怪的造形,额头上,/横放了一条加长的眼眶。”这条横在额上的加长眼眶,可谓神来之笔,忽而让“蜀”字如同川剧中的脸谱般,拥有了令人注目不忘的人物性格。梁平对这一粒粒包了浆的汉字如此情有独钟,大概也与他早年的插队经历不无关系——在五里坡,“一本崭新的新华字典几乎翻‘泡’了”。就在这一粒粒字中,诗人看到了历史层叠的虹光和汉语体内的微光。
试看这首杂糅了历史典故与现代意识的《惜字宫》:“造字的仓颉太久远了,/远到史以前,他发明了文字,/几千枚汉字给自己留下了两个字的名字……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仓颉,/越来越多的人不识字。/与此最邻近的另一条街的门洞里,/堆积了一堆写字的,/更不如算命的,两个指头一掐,/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应有尽有,/满腹鸡零狗碎,/一脸道貌岸然。/那天仓颉回到了这条街上,/对我说他造字的时候,/给马给驴都造了四条腿,尽管,/后来简化了,简化了也明白。/而牛字只造了一条腿,/那是他一时疏忽。/我告诉他也不重要了,/牛有牛的气节,一条腿也能立地,/而现在的人即使两条腿,/都不能站直。”梁启超论及学问之道时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及欧洲文明未兴之前,皆是纸的学问。读古人书,不外摹仿与解释之类”又说,“读破学书,只知读熟,不能应用,其无用与熟读经史文学等,有如烧纸成灰而吞之。”诗人梁平深恶食而不化的痼疾,一番写史过后,最后两句狠狠打中现实七寸,像一个体操运动员,在做完回环、后空翻、托马斯旋转等一连串高难动作后,来了个稳健有力的下法。在无用之学的灰烬中,诗人掺入他阅世极深的和特有的玩世又豪气的语调,终开出地方主义与现代意识的奇异花朵。且这灰烬之花,可入药、可医心,可济世。
诚如珀威斯在《坏建筑的起源》中所指出的“被咀嚼的经验”对于建筑艺术的重要性。在诗学当中,“被咀嚼的经验”同样不可忽视,梁平说,“人生不是拿来总结的,是拿来经历的!”他大概从中咂摸出了诸多况味,因而无论谈及何等艰涩生僻的知识,只消他拿尝遍蜀中美味、人间冷暖的口齿咀嚼,即流淌出如席间妙言警句般,入耳入心的,有温度的诗句。
文字世界的经营者,也实在是苦心孤诣的建筑师。有建造迷宫者如博尔穆斯,建造精神病院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建造灵巧宫殿者如卡尔维诺,建造妓院者如亨利米勒……梁平在他的诗歌王国中建造出一个文物展馆——汉代画像砖、卫元嵩墓、龙泉驿站、万年台子、皮影灯戏、书法、民俗、印章统统入诗。现从文物馆中取一枚《青铜.蝉形带钩》,一件战国青铜饰品(武士束腰带上的蝉做的饰品),开篇即借史记的笔法勾出了久远的战事,其间豪情满怀亦承接了边塞诗的传统。同类题材的诗歌往往学究气盛。诗人梁平的强大之处在于,他总能从一派出土气象中咀出豪情干云,咀出人间冷暖,成就一种高明的抒情。
颤栗的花翎诗人
布罗茨基在描绘拜伦的面孔时用了一连串形容词——“魔性的、反刺的、冷峻的、鹰钩鼻的、浪漫的、受伤的……”英国诗人奥登那著名的横七竖八的皱纹,则有着与之对应的著名的描述——“凌乱的床铺”。可见,描述一个诗人的容貌是何其重要,或者说,一个诗人需要被历史定位,连同他的容貌!上述警言无非为了引出一个严肃的事实:在这个视觉霸权的年代里,《深呼吸》的作者梁平可说是国内诗歌圈中为数不多的面孔可称上镜的男诗人。诗言如戏台,戏台之上与其配合的“服、化、道”——大约须有回避牌、肃静牌、职衔牌、公案桌、关防盒、万民伞,当然还少不了一定外裹上缀顶珠的花翎。然而,这是一顶颤栗的花翎!当代诗人中能直面古今官场的并不多,能写出那朱漆大门之内,云龙浮雕匾额之下不为人道的痛感的,更是寥寥。自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存在的“士”的阶层,一方面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崇尚节气,“志于道”且“从道不从君”。自隋唐科举大兴之后,“士”的阶层扩大到多数官员。而随着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中国的最后一个士大夫沉入了历史的深潭。诗人梁平在这些士大夫的阴魂中找寻自己的前世《红照壁》:
我的前世,
文武百官里最谦虚的那位,
在皇城根下内急,把朝拜藩王的仪式,
冲得心猿意马。照壁上赭色的漆泥,
水润以后格外鲜艳。
藩王喜红,那有质感的红,
丰富了乌纱下的表情,
南门御河上的金水桥,
以及桥前的空地都耀眼了。
照壁上的红,
再也没有改变颜色。
红照壁所有恭迎的阵势,
其实犯了规。这里的皇城,
充其量是仿制的赝品。
有皇室血统的藩王毕竟不是皇上,
皇城根的基石先天不足,
威仪就短了几分。
照壁上的红很真实,
甚至比血统厚重。
金戈铁马,改朝换代,
御河的水,流淌一千种姿势,
那红,还淋漓。
我的前世在文献里没有名字,
肯定不是被一笔勾销,
而是大隐。
前世的毛病遗传给我,
竟没有丝毫的羞耻和难堪。
我那并不猥琐的前世,
官服裹不住自由、酣畅与磅礴,
让我也复制过某种场景,大快朵颐了。
我看见满满的红,
红了天,红了地,
身体不由自主,蠢蠢欲动。
一垣照壁饱经了沧桑,
那些落停的轿,驻足的马,
那些颤栗的花翎,逐一淡出,
片甲不留。
红照壁也灰飞烟灭,
被一条街的名字取代,
壁上的红,却已根深蒂固,
孵化、游离、蔓延,
可以形而上、下,
无所不在。我的来生,
在我未知的地方怀抱荆条,
等着写我。
一个“官服裹不住自由,酣畅与磅礴”的前世,一个“怀抱荆条”在未知处“等着写我”的来生,诗人在书写中一遍遍确认自我——“我的祖先是我,我是我的祖先。”
今生为官又为诗的梁平,和那条纱帽街一样,“目睹了这些纱帽从青到红,/从衙门里的阶级到戏文里的角色,/真真假假的冷暖。”有着切肤的亲历体现,感受到“那双官靴上的泥土有些斤两”,因而能写出那不足为常人道也的世故人情与冷暖自知。
“吃皇粮的驿夫驿丁,/人生只走一条路,不得有闪失。”“官靴与马蹄经过的路面,/印记高低深浅,/都是奴相。”“那些发票都是真的,/那些交易也是真的,/那些他们记住的脸面,/不是真的。”“一夜之间,/人模变成狗样。”这些诗句老成世故,又同时真诚激烈。在这诸多官场写实的诗歌中,顶戴花翎的诗人埋伏着箴言——“这里的银子有点烫。”
巴蜀江湖
四川一直是现代诗歌的重镇,巴山蜀水间豪客辈出,怪才云集,门派林立。顶戴花翎的诗人一生都在谋划着从高衙出走江湖,或兄弟呼拥,酒气蒸腾,“与我的一粒粒汉字通宵狂欢”;或两肩扛诗,诗中有千军万马,也有儿女情长;或引吭高歌,“煮刀光剑影,煮抒情缓慢/一样的麻辣烫。”
祖籍丰都鬼城,出身于重庆兵工世家的梁平,常年奔走于巴蜀两地,他诗中对这两地奔走的生活,有活灵活现的描绘:“成都有一把钥匙在手,/重庆有一把钥匙在手,/往往一脚油门踩下以后,/人在家门,手机开始漫游。”诗人对巴蜀两地的文化气质、历史典故、诗歌地理皆谙熟于胸,甚至专写过一本《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在谈到他的长诗《重庆书》时,作者写道,“支撑我想象力的素材上溯到3000年的远古,下究至一个人几十年在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四川特色的剧社、戏场、会馆、茶楼,甚至方言,都时不时窜进梁平的诗句。他较真儿地辨析“爵版与脚板,/四川话里没有区别”,又说成都话是“即便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争吵,/怒目相向,毒狠狠的场面,/撒一地粉言粉语。”巴蜀之地的多情亦渗入诗人的纸短情长,“我会与我的那个女人来看你,我会把看你的女人当做我的女人。”至此,一个“喝酒、打牌、写诗、形而上下,/与酒说话与诗说话,然而,把这些话/装订成册。这一生就够了”的真性情之巴蜀豪侠跃然纸上。试看其自白《陋室铭》:
“四十五年,背井离乡。一二三步,单走独唱。有诗文在,无安生床。原燕鲁公所,现老子作坊。怕不速之客,好几口黄汤。夜来摘星星,揽月亮。无官场堵清心,无红袖添乱忙。是重庆崽儿,就敢作敢当。却原来,天要我爽!”
这份江湖豪气与巨大自信,首先源自于作者对自己历史的正视与警醒——“自己走的路,无论姿势怎样,自己必须要记得。”梁平经历过插队生活,对于时代气候有着敏感和残酷的体历,这磨砺出了他诗歌中锋利的现实感和敢于担当的的品质。与此同时,他记人记事常有充满戏剧性的反转,现实的粗砺与残酷包裹在其强大的直觉和引人入胜的叙述里。苦难作为基底留在了诗人的豪情深处,他分拣灾难的诗篇由此格外动人——“这一切,只在眨眼之间,/成为悲情。”
从高衙出走,仗剑天涯,诗人的归宿又在哪里?梁平在《吊卫元嵩墓》中有几句描写那装疯卖傻的卫元嵩:“还有谁,能通晓佛儒道三教典籍?/那是曲高和寡的演出服,/那是胸中积学的保护伞,/一个贫僧,怀抱经邦济时之略”,诗句似正切中诗人自己通融又张狂的心意追求,终究是要“非佛非儒非道,非官非民,回到太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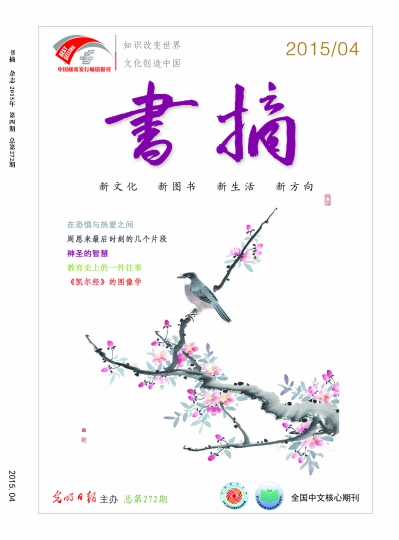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