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访碧螺峰
碧螺春是苏州名茶,过去只知道产地就在太湖之上的东山与西山,后来才知道,在东山的连绵丘岭中,有一座山,就叫碧螺峰,据说是碧螺春最早的产地,但真的上了这座山,已是2005年的初秋,而且是在无意中撞到的。
那天原是随人去东山勘察准备复建的灵源寺遗址的。灵源寺遗址在东山石桥村的山坞之中,那里丘岭连绵,果木葱茏,里面有三个自然村——上湾村、石桥村和张巷里。由石桥村北进,路畔黄色围墙下,堆满了农民新采的橘子,长长的橘阵,在天光下闪着红光,新鲜而清香。山越来越近,山前大片开阔的坡地上种满了果树,除了橘林,还有枇杷树、杨梅树、栗子树、银杏树,再往里去,快到山脚的地方,便见草木丛中有残基断墙隐现。
林中有座陋屋,其实是座陋亭,里墙嵌着一块碑,上题“奉宪永禁”四个字,从碑文中得知此寺原先建制雄伟,占地广阔,但屡遭损毁,并有和尚变卖寺产。当地士绅由此上书,于是勒令永禁寺僧出卖寺产,包括土地和树木。
在小碑亭看碑文时,我的眼睛老被近旁鲜亮的绿色所诱,常常看两眼碑文,便会不自禁地用余光觅一眼那绿色。原来,碑旁侧墙上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拱门,透过苔痕斑驳的拱门,可以看到野地里草木繁茂,翠生生的可喜,被阳光一打,绿得耀眼。
心,便在那一刻活泼泼地一跳。
要不是刚才看见满地金黄的橘子,才想到已是金秋,若只看这山坞依然青翠碧绿,真让人以为现在还是春浓之时呢。“古寺在境内,来生人外心。岚光雨余澹,树色门前阴。施食舞山鼠,经驯野禽。问春春已去,苔径石深深。”从《洞庭东山志》中选存的孔贞明《入灵源寺》诗,可知此寺在明代已为古寺,而且是在山光树色相映下的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到如今,果真是“问春春已去,苔径石深深”了。
如今就从一木一石中寻觅与解读久已远逝的天地精华与人文遗韵,背景是满目的绿叶,头上绿枝横斜,脚下绿草如茵,阳光如金片跳跃林间,行走其间无处不安宁,无处不熨帖。
咳,干吗要复建呢?现在不更好吗?下次再来,还会有这样的野趣和古意吗?走着走着,这样的念头便如丛生的野草拂之还来。
这样想着,双脚已穿过林中的庙基继续往上走。半山以上是葱绿的茶园,漫山遍野都是排列整齐的碧螺春茶树,山顶建有一亭,近前可见“碧螺亭”三字,亭畔有一卧石,上题“碧螺峰”三个红字。传说远在千年前的唐代,碧峰有野茶数枝,为仙鹤传种山人采制泡饮,这就是碧螺春最早的来历。
和近旁相连的群山一样,碧螺峰海拔不高,山头浑圆,种满了茶树,一球球,一丛丛,碧绿苍翠。有几株大杨梅树未被清除,枝叶如绿伞撑开,十分婀娜。所谓正宗碧螺春,据当地人介绍,须种植于枇杷、桂花、杨梅等果树花树之下,又叫篱笆茶,因而尽吸花香果味,前人俗称“吓煞人香”,以极言其香。就是康熙品尝之后也深以为然,惟觉俗名不雅,遂提笔改为“碧螺春”,以其色绿如碧,蜷曲似螺,又为初春采摘,故名。
留这几株大杨梅王,也算是保存了一点古风。
一位老茶农在茶园里劳作,收音机挂在旁边树杈上,正在播放越剧。初时不见其人,先闻其乐,四围青螺,那乐声仿佛是从山的肚子里飘出来的,让人在向各处张望间一时有些恍惚。
这就是碧螺峰了。秋阳淡照,四望群山如绿色螺旋。左顾右盼,忽觉茶为壶中之物,现天地如壶,以万物为茶,人也在其中,无边清气从太湖升起,将一切浸透。
下山。秋天的山林在这里变得金红绚丽,越往下走,绿色茶园便让位于丛林,那是各式各样的野树,大多叫不出名字,我认得的仅有野栗和橡树。说它们“野”,是因并非人工种植,纯然天生。这些树混杂在一起似乎都长得乱七八糟,如同小孩随意划拉出的涂鸦之作,单独取出任何一棵都难登大雅之堂,但它们集合在这无人的山腰和山谷,便有一种野趣和大气,像一群挤挤挨挨勾肩搭背的村姑,如果她们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哗哗大笑,那是风儿撩拨的结果。
就这样在无人的幽谷里经历春夏秋冬,变换枯荣红绿,让人无意闯入之时,都被这“万木霜天竞自由”的自然景象深深吸引,回到人类童年天人合一般的质朴与原始状态之中。
春日再访碧螺
2006年4月,又偶然来到碧螺峰下。一个人循旧路缓缓而行。头上树木枝叶扶疏,地上青草离离。林间静极了,只有一只鸟躲在树林里清脆响亮地鸣叫,这鸣叫似一道闪亮的声波之剑,划破笼罩山地林木的静谧之纱。
信步来到一处茶园,有农妇头戴草帽正在采茶,便站下和她攀谈起来。这农妇原本独自一人,在四周林木环绕的茶园里默默劳作,见有人来打破这寂寥,颇为高兴。
这座山是碧螺峰吧?我先开口,权当招呼。
是啊是啊,农妇热情地作答。再往上,顶上有亭有碑,写了几个大字,是碧螺峰。
山上我去过,那上面的景物也全见过,便笑着点头。转口又问这山脚的灵源寺,从遗迹看占地好大呀。又看着近旁同样用青石条砌成的山路问,这些原先也都是庙里的东西吧?
这下可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农妇告诉我,茶园这边的石阶用的料,是从附近一座大墓拆过来的。原先这座山上有好多大墓,近旁就有一座。她是外乡人,嫁到东山快三十年了,亲眼见过这座大墓的气派,长长的墓道,石牌坊石狮子,还有两块大石碑呢。
我顺她指引回望,哪里有大墓?只见身后一座山崖般的小丘,遍体荒榛野蔓。再凑近仔细辨认,才见内里确有石砌的高墙,外表全被枝枝蔓蔓的野草封住了。
好奇心被撩起。问是谁的坟?农妇摇头不知,说原先坟前有两座巨碑,写着有字,可她不识字。据说墓主后人都在海外,很长时间没人问津,这墓渐渐就荒了。“文革”期间村里在山上开荒修茶园,生产队就地取材,把大墓的青石墓圈扒来垒了山路。
说到这里,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又告诉我这墓就在前一两年被盗了。应我要求,她走过来领着我绕到墓墙后面一处残破的缺口处,果见一冢后背在地平处被挖开一小洞,像裂开一张黑洞洞的嘴缝,高仅尺余,宽与肩平,仅容一人匍匐而入,且还要体形瘦小的。
“听说墓葬很丰厚,从里面掏出来好多黄货和古董,值钱的东西不少呢。”
“是本村人干的吗?”
“不是,是外地人。可没有本地人介绍和指路,外人怎么知道内情呢?”
“这块茶园是你家承包的吗?”
“已被收购了,要开发旅游。一亩山地2.8万,山上各种树,包括这些茶树,无论大小,10元一株。”
农妇又显出辩解的样子,补充说:“不过这山现在还没有开发,这片茶树总是要有人管的,不施肥打虫,很快就完了。”
我表示理解,鼓励说:“为什么荒着呢?多可惜啊。可要是真的开发旅游不种茶了,你做什么呢?”
她很茫然地摇摇头,手不停地采着茶。
“你男人呢?”
“我老头儿吗?在村口开了个小店,卖打虫的药水儿。”
“儿子大学刚毕业,学的是城市规划设计,毕业后还没找到固定工作,现在暂时在一家私人老板处帮忙。想去考规划部门,上百人竞争一个位子,太难了,只好靠他自己去闯了。”农妇说到儿子,口气又骄傲又焦急。
“到现在还不肯谈恋爱,也不是没有姑娘看中他,可儿子自尊感太强,说还没创业,没有能力成家。二十五岁了,在农村已经不小了。只要女方愿意,招女婿也行啊。我们家里的钱,都供儿子读高中、读大学了,谁家的姑娘肯来当媳妇啊。”
春阳温温地辉映在静谧的林间茶园。戴草帽的农妇双手不停,嘴也不停。那双翻飞在茶树上的手很粗糙,摘茶的指甲发黑。
我坐在黄石之上听这位母亲聊天。常回头看一眼,再看一眼身后那座“绿堡”,在农妇停声专心采茶时,忍不住问了一句:“这墓原先的入口在哪儿呢?”
“就在你身后。没人进去,被柴草封死了。”
再扭头细看,果然在荒树杂草世界之中隐约有一处黑色入口。
索性转身近前,弯腰钻进榛莽之中。顿时感觉进入了一座植物纠结成一团的黝黑大墓之中。
内里树隙竹缝中隐现两冢,一冢前荒草乱树丛中卧一大石碑,已断成数块。另一冢前竖一巨碑,完好无损,只是也被藤树遮挡住了。
我喊起来:“我看见了,里面真的有碑,你进来一下!”
农妇寻声也钻了进来,嘴里不停地说:“呀,你胆子真大,我从来不敢到里面来的。”
她凑到近旁。用脚踏,用手折,试图帮我拂开那方竖碑前的枝蔓。但压下一把枝条,新的更多的枝条又从四面八方纷纷横斜了过来。
光线暗淡,碑上的字模糊不清。但纹样精美考究。碑上刻有“得吉山水”等字,依稀可辨。
“我们走吧。”农妇急着离开,我随其后钻出榛莽封闭的墓圈。
我要离开了。问她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如何联络?可能什么时候凑巧能帮上忙。
她一听异常兴奋,立即收工端着茶篓和我一起下山。农妇家就在村头灵源寺筹建处大殿的背后。院子水泥铺地,堆了一地的旧玻璃瓶,大约是准备用来灌药水儿卖的。一排三间简易平房,无任何装修,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农妇的男人站在院门口,旁边停着一辆装货的小三轮,他个子不高,五十出头的样子。农妇也是这个年龄。
男人拿出一张儿子的名片给我,但又说名片上的单位已不是儿子现在的单位了。问他俩的名字,都不肯说,说喊儿子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时,女人使了个眼色给男人,对我客气道:“拿斤茶叶尝尝吧?”
我知道制作一斤碧螺春茶叶大约要费多少工:最早于三月上旬采集的春茶,因尚在春寒料峭之间,那时的茶树只露出星星点点极细的小芽尖,须摘七八万个芽头才能制成一斤极品碧螺春,因在清明之前采摘,俗称“明前茶”,十分金贵。一二级的明前茶每斤也大约需6万左右的芽头;现在虽是清明过后制作的炒青,一斤茶叶也起码要摘四五万个芽头,内里付出的辛苦可见一斑。我忙告辞,边说不喜欢喝茶,不用客气,边快步走出门去。这时,家家户户在生火烧饭了。
在村庄与通往碧螺峰山脚的道路之间,隔着一道连绵的低冈丘地,冈上分布很多大石。刚才农妇说,这叫石牌山,问我像不像一只鸡的形状。
我随便看了一眼,树丛遮掩丘冈,看不出什么形状。只觉得它像一道长长的绿色天然石墙,把小村温柔地遮挡护围了起来。
(摘自《吴山点点幽》,现代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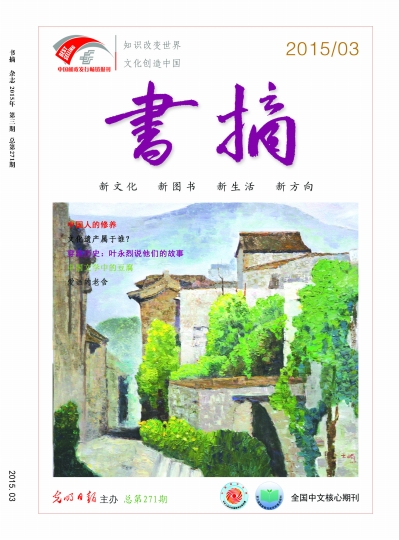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