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思想凝聚在一起,成就了当年中国最具政治色彩的文人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民主信念、政治主张大声疾呼。他们只凭文化和思想力量参与中国政治,活跃在国共两党之间,形成可圈可点的政治风景。
张澜临危受命
民盟成立之初,遭到了蒋介石的破坏和打压,先是派民盟主席黄炎培前往南洋募集救国公债,继则以重金促民盟继任主席张君劢出走云南,致使民盟群龙无首,工作难以开展。张澜临危受命,出任民盟主席,并立即做了几件大事:一是统一了在民盟纲领问题上的争执,毅然决定删除原先拟定的十二条纲领中针对共产党的两条,保留了针对国民党的四条,突出反独裁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法制的精神,正式形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政纲领》(《十大纲领》),并送往香港发表。二是1941年11月16日,张澜率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冒着被国民党打击压迫的危险,在重庆举行茶话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公开了组织。三是1941年11月25日,张澜等民盟参政员根据民盟十大纲领,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提案内容十分尖锐,直指国民党统治的要害,得到了包括中共参政员在内的二十三名参政员的联署支持。民盟初试啼声,大获成功。四是1942年1月,张澜主持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委员会,排除阻力,吸收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入盟,使民盟正式形成了“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建派、职教社、救国会)和无党派人士的内部格局,增强了民盟的战斗力。在张澜领导下,民盟很快摆脱了初创时的困境,不仅内部得以团结巩固,而且在国民党伺机打压的情况下,正式公布民盟的成立,非常巧妙地站稳了脚跟,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
张澜曾经感慨道:“我最讨厌党,因为凡是一个党,都有强烈的排他性,现在我却抓了一大把党在手里,真太奇怪!”
徐铸成谢绝加入国民党
1939年到1941年间,徐铸成在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职位上,与国民党在港领导人陈训畲和邓友德有密切来往。陈训畲是陈布雷的兄弟,对徐铸成其人其才颇为欣赏。
1942年冬,《大公报》老板胡政之委派徐铸成到重庆了解“政治情况”,以利编报。徐铸成为此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月。其间收到陈训畲的热情接待,还得知“布雷先生想见见你”。
一天,陈训畲、邓友德陪同徐铸成见到陈布雷。陈布雷说自己是张季鸾的好朋友,“季鸾作了古人,我很悲痛。幸好《大公报》有你和芸生二人,季鸾有了传人,我也很感高兴”。
接下来,有段对话——
陈:“你是否参加了政党?”
徐:“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
陈:“参加一个党,对自己的事业也有好处的。我从未介绍人参加我们国民党……但我想如铸成先生入我们的党,我自己愿当你的介绍人。”
徐:“入党是一件大事,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再答复吧。谢谢你的好意。”
事后,徐铸成立即写信给胡政之,说了陈布雷主动表示愿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的事,并说自己不想参加国民党,征求胡政之的意见。
胡政之在回信中让徐铸成把这件事说给吴鼎昌。徐铸成本来已准备乘飞机回桂林,收到胡政之的信后,专门改乘公路汽车去贵州见吴鼎昌(吴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说明是胡政之嘱其就是否入国民党事征询意见。
吴鼎昌问:“你自己的意见如何?”
徐铸成答:“《大公报》一向是超然于党派之外的。我的意见,不想参加任何党派。”
吴鼎昌说:“好,留在党外,说话方便些。”
徐铸成回到桂林后,向胡政之报告了见吴鼎昌的经过,并写信给邓友德,说明自己慎重考虑的结果是决定不参加国民党,请他向陈布雷婉谢好意。
冯亦代的“侠风”
黄宗江说——
我初识亦代是在1943年春,我方从上海卖艺到重庆,在金山遇张瑞芳之后,与尚在盛世才狱中的赵丹的妻子叶露茜合演了《家》中的觉新和瑞珏。一次日夜场之间,我未卸妆,在后台闲坐,手持一卷我从旧书摊上买来的卞之琳的《西窗集》,扉页上有“冯亦代藏”的字样,忽然在身后出现了自我介绍的冯亦代,亦缘也。他那时是著名的“后台朋友”……当时的星座“四大名旦”白杨、舒秀文、张瑞芳、秦怡都称冯为“冯二哥”。此二哥乃独生子,无排行,更非“宝二哥”……“二哥”的出处连亦代密友,二流堂堂友苗子、小丁都说无可考了。据后起之秀袁鹰追索,当由于亦代有侠风乃获此美称……“二哥”之行侠也不外于帮忙、帮穷、帮人出书等等。……他当时的专业是翻译反法西斯名著,跑跑后台,写写文章。
我们这号人当时是非常“突出政治”的,当时在陪都,是左是右,泾渭分明。我们多自命“党外布尔什维克”(后来又多成了“党内布尔什维克”,这是后话了)。冯在解放前后均可称翻译家、活动家、发言家,也就成了右派一大家。……冯亦代是被他的顶头上司吴晗抛出来的。后来的后来,吴晗被抛得更惨。冯亦代也就闭口不谈此事。
萧乾走天涯
萧乾是个遗腹子。他在回忆录中说:“给我幼小心灵打上自卑烙印的,是贫穷以及生命最初十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在那嫌贫爱富的社会里,穷就矮人一头,有时还不止一头。跑当铺,叫‘打小鼓的’,打粥,甚至断炊,都还只意味着物质上的匮乏和生理上的痛苦。我母亲为人佣工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精神上的凌辱。”
1935年,萧乾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先后为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火,《大公报》缩减大量版面,他被辞退。1939年秋,萧乾远渡英伦,负笈剑桥,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1943年,他放弃学位,当上了专业的西欧战地记者。纳粹每晚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狂轰滥炸伦敦的硝烟里,他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记录报道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列颠之战”等著名战役,并随美国第七军由法国向德国挺进。军旅中的萧乾,身穿棕黄色军装,肩佩“中国:战地记者”标牌,“踏着威廉街的废墟,去看过希特勒当年向大半个欧洲发号施令的魔窟;采访过波茨坦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也曾有过刻骨铭心感慨良多的瑞士之行”。
一位朋友用动人的笔触描述萧乾说:“在加拿大使馆举行的酒会上,看着他端着酒杯在来宾间来回走动,见他用流利的英语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交谈,用一口柔和悦耳的京白向国内的同行、朋友一一致意,我就不禁要想,他身心里正涌入与流淌着的这股悠长而甜美的酒浆,会使他如痴如醉重温过去的旧梦吗?无论怎样,与多少年驻游无定的风雨人生比较,他现在显然是已经整个地消融在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之中了。”
(摘自《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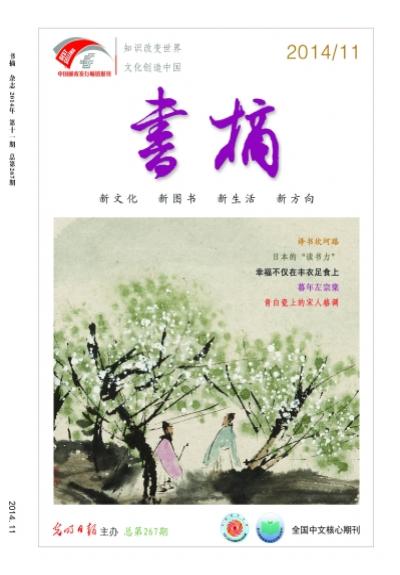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