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瑛和徐自华,是秋瑾后期走得最近的两位密友。她俩都曾以沉痛笔调,追忆秋瑾,吴芝瑛写有《秋女士传》、《纪秋女士遗事》等,徐自华写有《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悲秋记》、《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等。两人都对秋瑾的豪纵尚气、能言善辩印象深刻。吴芝瑛说秋瑾“每稠座,议论风发,不可一世”;“芝瑛守家学而秋好为高论,以此每见必以箴规之言进,秋不服即相争,争不已,家人辄进酒一醉而罢”。徐自华说,秋瑾“丰貌英美,娴于辞令,高谭雄辩,惊其座人。自以与时多迕,居常辄逃于酒”,酒酣耳热,则悲歌击节,拂剑起舞,气势如虹。秋瑾“稠人广众,论议锋发,志节矫然,人辄畏重之,无有敢一毫犯其词色者”。
吴芝瑛和徐自华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秋瑾的刚直爽烈,也让她容易树敌。吴芝瑛回忆, “女士生平好侠负气”,遇到“不达时务者”,往往当面指责,丝毫不留情面,因此不少人对她怀恨在心;徐自华也说,秋瑾口角不肯让人,遇到顽固者,甚至当面讥诮。她也劝过秋瑾:锋芒太露,恐遭人忌。
有一次,秋瑾、徐自华与吕女士在上海同游张园。小憩喝茶时,恰逢某留学生带着一个雏妓,乘马车而至。他们在临近的茶座,恣意笑谑。秋瑾喟然叹息:看到留学生的腐败模样了吧?我要过去劝谏他。徐自华笑着阻拦:这些家伙在学校待了半年,好比鸟入笼中。如今来到这花姣柳媚之地,正欲赏心悦目,关你什么事?吕女士也附和:暑假归国的留学生们,大半都携妓作快意之游,你怎么干预得过来?秋瑾不听,起身以日语问询并交谈,留学生面露惭色,雏妓则气得怒目走下台阶,独自乘车而去。徐自华打趣秋瑾,此举大煞风景。秋瑾也笑起来:“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秋瑾经常很伤心地对徐自华说,自己喜欢广交朋友,遇到妇女界名人,便会登门拜访,但所遇之人,大多沽名钓誉,徒有空言,屡次扫兴,不由得心灰意冷。相对来说,男学界倒还有几个人物,女学界少有出类拔萃、可引以为同志的。徐自华说,留日女学生里,总有佼佼者吧?你是否太自负,所以曲高和寡。她随即列举了最著名的几个人。秋瑾回答:你既然说她们有名,请问哪位肯为公益事奉献,牺牲一己?别人都说我目空一世,你与我相处,应该知道我并非自负之人,但实在不屑于搭理那些庸脂俗粉,“余之感慨,乃悲中国无人也”。
1907年春,秋瑾在杭州筹备起义时,曾与恰好去省城的徐自华相遇。她觉得首期《中国女报》比较草率,自己又头绪繁多,想让徐自华驻上海代理几个月。徐自华因母亲生病而推辞,秋瑾颇不高兴,责备她“忘公益,恋家”,并作诗规劝。就连陌生人都要干预,秋瑾对待闺蜜,当然是有话则说。
徐自华,徐小淑姐妹与秋瑾,有“异姓骨肉”之谊。秋瑾在浔溪卧病时,两姊妹伺奉汤药,无微不至。在秋瑾感召下,徐氏姐妹加入了同盟会与光复会,对秋瑾宣传排满革命与妇女解放,她们多方支持。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时,经费困难,徐自华姐妹勉力捐资一千五百元,使刊物得以投入编印。1907年5月,秋瑾筹备浙江起义,军饷匮乏,求助于徐自华,后者将自己的妆奁细软(价值三十两黄金),倾囊献出。徐自华早已丧夫,父亲又刚刚去世,并不宽裕。姐妹俩都非常赞赏、敬佩秋瑾,只是没有像她那样挥戈上阵罢了。
每个人因为性格、处境、志趣等不同,会选取不一样的人生路径。这本是人之常情,即便亲如手足,也宜彼此尊重,容忍并理解各种选择上的差异,秋瑾却有点一根筋,她见了徐氏姐妹,就一阵猛劝,遗憾于她们眷顾家庭,不能与她同泽同袍。写给她俩的诗词,也是一再劝勉。《柬徐寄尘》说:“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希望她换下闺装,拿起武器。秋瑾跟徐小淑有师生情分,所以她的《赠女弟子徐小淑和韵》更是直言不讳:“我欲期君为女杰,莫抛心力苦吟诗。”
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秋瑾,要慨然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固然胸襟广阔。但是别人那些不一样的意愿,也宜顾及,可她就这么一直说,锲而不舍地说,多少会让人感到压力吧?当一个人气场强大,能量充沛又自居正义、正确时,容易在不经意时,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人。这种狂热浓到极致,就容易构成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与偏激。
徐自华在秋瑾身上,常常能感到这种说一不二的强势。然而,她也说,秋瑾虽然喜酒善剑,放纵自豪,行事不拘小节,看似张扬,但其本心,“殊甚端谨”。她跟秋瑾亲密无间,感情深厚,所以能拨开那些蒺藜似的凌乱的尖刺,看得到秋瑾惊世骇俗外表下的端正,还能领略到她机敏有趣的真性情。
徐自华字寄尘,工诗词,后成为南社早期成员。她任吴兴浔溪女校校长时,从日本回国的秋瑾在该校短暂任教,两人成为知交。她在《秋瑾轶事》里忆起,她俩一相识,就仿佛老友,一天不见,便觉沉闷,要问妹妹小淑:你秋姐今天咋不来呢,生我的气了吗?
秋瑾与徐自华经常“拌嘴”当然不是斗气。两人都反应灵敏,言语俏皮,幽默风趣,闺蜜之间,遂有那种特别默契、快意的戏谑、调笑。有一次秋瑾预计出门三四天,结果两天就返回了。徐自华询问缘故,秋瑾笑着说,怕你“望陌头杨柳”。她以“忽见陌头杨柳色”、想念夫婿的思妇打趣徐自华,后者说她张口就开玩笑。秋瑾的玩笑,脱口就以男性自居。
有一天,两人将同赴上海。小婢晕船,未及给徐自华梳头。秋瑾自告奋勇:我替你梳,“胜尊婢万倍”。徐自华笑:“何福得此侍儿!”
徐自华在《秋瑾轶事》记载:
女士曰:“子不见陈淑兰赠外诗。”余曰:“处处欲占便宜,却出语不祥。”笑曰:“子怕我溺死,我必不如是死。”执镜自照,曰:“好头颅,孰断之?”余恶其语,夺镜,失手堕地碎。女士大笑曰:“子欲吉语,偏是恶谶。”
女诗人陈淑兰的丈夫自沉于水,她后来殉夫,之前有诗仿佛一语成谶;隋炀帝揽镜自叹,“好头颅,谁当斫之”,不久死于非命。秋瑾与徐自华都心知肚明,她的反清活动,冒着生命危险。徐自华为之担惊受怕,秋瑾自己却随口就是“死”字,略无禁忌,泰然自若。之前她也对徐自华说过:“我生平喜为人所不为之事,死且不惧。”
她俩有一次读小说《女娲石》,徐自华戏云,秋瑾很像书里的女杰琼仙,颇自负,尚义气,好胜心强。秋瑾扑哧一笑:好冤枉!我在你面前何曾自负过?徐自华也笑起来:你对我不仅不倨傲,还极其温让。这就像唐太宗看魏征,“人云疏慢,我见其妩媚耳”。
秋瑾善豪饮,有海量,酒后尤其谈笑风生。徐自华不喜欢喝酒,却常常被秋瑾灌醉。有一天,她临窗执卷,被秋瑾一把夺去:“女学士,请别看书了,看我舞刀如何?”随即取出倭刀,“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斫地之气概”。
秋瑾收刀后问徐自华,自己像哪位古人。徐自华戏云,你好兵器,刚毅英武,像孙夫人,不知哪位是你的刘(备)先生,见了你战栗而下跪?秋瑾拍着她的肩头说:你擅诗文,不亚于徐淑,我为你再觅秦嘉好吗?徐淑与秦嘉是汉代诗人,也是一对深情夫妻。徐自华以那时孀居妇人的下意识反应,失笑道:怎么说起这些匪夷所思的话。秋瑾笑着说,我跟你一样,你可以寻觅秦嘉,我也有我的刘先生。话里显然有隐情,徐自华没有再问。也可能,她不便多加透露。
秋瑾在浔溪女校的几个月,与徐自华朝夕相处,但她显然没有提到过自己的两个孩子,以至于徐自华发表于1907年11月的《秋女士历史》,颇不确定地写道:“一子一女,有云系妾出,未知孰是。”
秋瑾弃家求学后,儿子跟着奶奶,女儿王灿芝被寄养于秋瑾友人家。她在那里未受善待,衣衫褴褛,头上生了虱子。秋瑾遇难后,王灿芝由谢家女仆送归湖南,周围人冷眼斜睨。那段孤苦、凄凉的往事,让她不堪回首。而作为“女匪”的丈夫,王子芳的处境可想而知,他饱受惊吓,日渐消瘦,去世时年仅三十。
(摘自《读库1403》,新星出版社2014年6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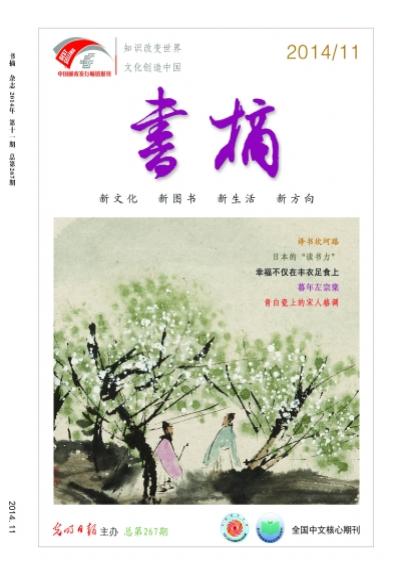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