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我们全家离开上海搬到苏州。苏州胥门内有个非常逼仄的小胡同叫寿宁弄,走进胡同不远就是我们在苏州的家“寿宁弄八号”。这是个很大的院子,以前可能是一个大官宦人家的宅子,可我们哪里顾得上去考证宅子的历史,去打听这里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细数那些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的房子。只记得院子的大门前有照壁,是逢年过节看热闹的场地。一进大门,有轿厅,再进西厢去是我姨祖母的佛堂,有个吃长斋的老姑娘常年在这里烧香供佛。院里有一株茶花、一株腊梅,两棵树下绕着茂盛的秋海棠。再进去,是一个砖砌的空院,门楣上书的是“一息景”。然后是五开间的两层楼房。逢年过节,西面两间,挂起了曾祖父母的画像,中堂祭祖宗,旁边留下一间做过道,前后来去有路可走。
爸爸同大大(母亲)的卧房就在过道东边。大大常常在过道梳头。大大楼上是对着花园池塘的窗,老鹰常在柳树上啼唤,三妹兆和最早的诗句“池旁柳上有老鹰”说的就是这里。楼下再往北,有大大的书房,她就在这个书房记账、练字。郑板桥的道情,渔、桥、耕、读、老头陀、老道人,我们都是从大大写的正楷中知道的。爸爸有时从前庭走到大大窗前,同大大交换什么意见,又去做他的事。从过道可以走向我们的操场和书房。也同当时的风气一样,大姐曾画了一幅观音,每逢初一十五,我们必去烧香磕头。院子前面的七叶枫和白玉兰开得非常热闹。旁边还有一棵榆树,三妹到老了还会背:
谁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邹。
池中罗水马,庭下列蜗牛。
燕麦纷无数,榆钱散不收。
夜来添骤富,新月挂银钩。
我们三姊妹的闺房在第三进房子的楼上,开窗就可以看到后花园。在这个童年的乐园里,我们的最大兴趣是夏天的晚上在凉床上学唱苏州话民歌。我傻乎乎地爱唱:
唔呀唔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
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
桃花园里铺房架,梅花园里结成亲。
……
小时候记熟了的歌谣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歌谣是和我们童年美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寿宁弄的花园大极了,有水阁凉亭,有假山,有花草,有果树,粉墙黛瓦,幽美雅静,此景只应天上有、梦中有、书中有、戏中有。可它不是《牡丹亭》中的花园,小姐们进去也不必红娘引路,偷偷摸摸。每天我们只要离开了书房,放鸟归林,这里就不再安静。我们有时文文雅雅地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癫癫爬山、玩水。姨祖母房间的一个保姆姓赵,赵大姐的丈夫在我们家吃闲饭,他手巧得很,常用竹子劈成竹片编成小花轿给我们玩。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囡囡就派上了用场,穿上我们给做的滚了花边的衣服、帽子,坐在花轿里,保姆郭大姐走在最前边嘴里“哐,哐”地学锣声,我们抬着轿子浩浩荡荡从花园这边走到那边,满园子笑声。几次之后觉得玩假的太没有意思了,就找来大弟当新娘。那年大弟六岁,白白的脸,头发有点长,我们把大大房中的胭脂花粉刨花水拿来,替他擦粉点胭脂,把刨花水拼命往他头上擦。大大找来红头绳给他扎了四个朝天辫,我找出十岁穿的镶着花边的殷红的中式上衣……都穿戴好了,真像一个俏新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裙子。还是大大想出了办法,找来一块很大的绸手帕塞在大弟的裤带上,又请出了二弟作新郎和穿了半边裙子的新娘拜堂,一本正经拜祖先、拜父母,拜客人磕好头起来时,新郎官踩掉了新娘的裙子,“父母高堂”、“来宾”哄堂大笑,新娘子嘴瘪瘪地要哭,大姐忙搂过去:“弟弟不哭,新娘子不能哭。”
花园中还有一个花厅,冬天我们的书房是在大厅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叫它冬宫。春暖后我们挪到花厅里念书,书房只占花厅的三分之一,放四张桌子,三姊妹和一位老师,还有两个伴读的小“春香”,是奶妈和保姆的孩子。书房前是两棵大玉兰花,一棵紫玉兰,一棵白玉兰。刚一有点春信,就满树的花,我们不但看而且吃,求伙房的厨子把玉兰花瓣放在油锅里一炸,像慈菇片一样,又脆又香。花厅还有五分之一是我们的戏台,门窗上有红绿色的玻璃。靠近书房后墙的花园里有杏子树和枣子树,摇头晃脑念书时听到屋外杏子落地的“啪,啪”声,三姊妹互相看看都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盼到老师休息一会儿,三个人抢着往外跑,大大的荷包杏子甜极了,没吃够老师又回来了,赶忙藏在书桌里。再下课又忙着去捡新掉的,三个小姐的书桌抽屉里常能找到烂杏子。
每天早上一吃过饭我们就往花厅跑,上午读书,下午唱戏,从没觉得读书是苦事情,我一生再没碰到过这么美的书房。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甜蜜、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但也留下了最痛苦难忘的记忆,一九二一年大大去世,是秋天,十月十六日,就在寿宁弄八号的家里,大大快要断气的时候,一大群孩子跪在她的床两边,哭着喊叫。我就跪在她的右枕边。大大虽然已经瘦得很,但还是很秀丽、姨祖母给我们讲过大大做新娘时,盖头一掀,凤冠下的璎珞一挑,那双凤眼一抬,闪闪发光,使每一个宾客都大吃一惊。多美多亮的眼睛,可是现在,那双凤眼紧闭了,再也不能睁开眼睛看她的孩子们了。我看到,大大眼中泪珠滚滚,滚到蓬松的鬓边、耳边。我停止了哭声,仔细瞅着她。大大是听见了我们的哭声、呼叫声,她还没有死,她现在还活着。她哭了,她知道她将要离开人间。我想,我们不能哭,不能让她伤心。我嚷着:“不要哭,大大还活着,大大在哭。”可是屋子里人们的哭声、叫声更响了。谁也没有听见我这个十二岁瘦弱小女孩嘶哑的声音。大概是嫌我碍事,我被人猛地拎了起来,推推搡搡,推到了屋子的角落里,推到了爸爸的身上。我一把抱住了爸爸,爸爸浑身在颤抖,爸爸没有眼泪,只是眼睛直瞪瞪地。
是一个多么凄凄惨惨的秋天的下午,一直到半夜,到处是孩子们、大人们的哭声。我哭倦了,蜷伏在最小的五弟的摇篮里睡着了。
冬天,我和大姐、三妹在后花园的假山石边照下了这张照片。在服丧期间,照片中我们还身着孝服:三个人都是灰色半长棉衫,黑裤子,灰黑色的棉鞋,头上戴着墨绿色丝绒的帽子。和平时我们穿戴的完全是两种样子,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小孩子的表情。
(摘自《张家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7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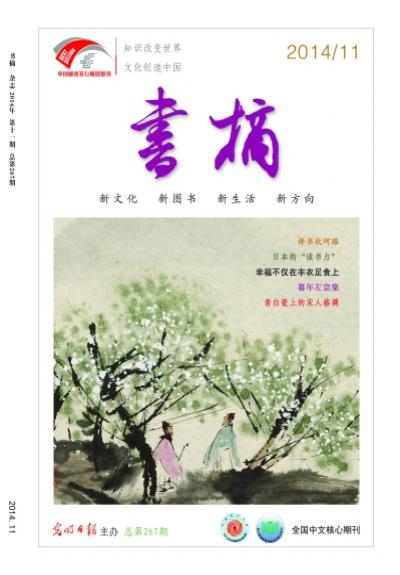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