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说我告诉了你一些东西,而是,我向你出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之前研究者不太一样的问题。现在,你必须往前走,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单读》:您最早是学数学专业的,那后来为什么开始历史研究呢?
金安平:这是很多人好奇的问题。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思想史,在长大的过程中,受我父亲的影响非常大。1962年,我们全家从台湾搬到美国的时候我11岁,当时我父亲在成功大学教建筑学,他是一位非常会讲课的老师,又很会讲故事。到了美国他先是去研究院,但为了抚养一大家人,我们四姐妹和一个小弟弟,他后来就去了建筑事务所工作。那时候他晚上工作还是很忙,但总会抽出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历史和传说都有,鬼故事也有,包括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他最喜欢的书是《庄子》,他把其中的故事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引导我们去思考其中的问题。
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受的是很严苛的日本式教育,只要考试不好就会被打,甚至带着一点虐待。我们一位英文老师,打学生打得十分之狠,1990年代我再回台湾,碰到另一位同学,还聊起这件事,这也变成那个时代最突出的记忆之一。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数学被训练得非常好。
《单读》:那时候为什么举家搬迁到美国去?
金安平:父亲离开台湾,有些人认为是他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他的想法太激进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这在台湾政治解严前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国民党人说他是亲右的,其实父亲根本不区分亲左亲右,他是一个跟着庄子走的人,根本没有派系和党别的概念。他最恨这种压制,后来很多人说是因为这样我父母才离开台湾。
但是我问父母,他们说完全是因为孩子。一方面,他们觉得在台湾体罚孩子的教育方式太不人道,太惨了,美国是另外一种宽松的教育方式,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在台湾教书收入有限,而当时家中的经济负担很重,四个姐妹要生活、念书,压力很大,而在美国,无论是教书还是进建筑设计事务所,经济压力都会有很大的缓解。
到了美国,我发现我功课最好的就是数学,他们的数学课对我来说完全是开玩笑,所以我完全集中于英文,也因此特别喜欢英文。那时候我对历史课反倒无所谓,觉得历史老师教得不太好。比如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教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只讲南方都是对的,完全不接受南方输了战争的事实,讲重建时期时,就会说北方人非常可恶。1960年代我上中学,橄榄球赛时升的还是南方的国旗(现在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唱的是Dixie’s Land,也不是美国的国歌。那个时期中学英文教的都是英国和美国文学,我对英语文学特别有兴趣,放学后就和父亲讲爱默生,说他比庄子要好,和父亲辩论。父亲很喜欢我对他的这种“挑衅”,正是通过这种和父亲的论战和“挑衅”,才帮我打下了思想史的底子。
我们姊妹读大学时,父母也完全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在美国的亚裔父母都希望孩子读科技,学法律,学商科,等孩子进入大学发现了历史之魅,发现了文学之美,执意转行,有些父母就会很不高兴。美国人认为大学是一个探索时期,一个人应该思考要怎样度过一生。我上大学时选了数学,但上了微积分、抽象几何的课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读数学的材料,反而跑去旁听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程,所以申请研究院的时候,我就自己作主,申请了中国文化思想史。
《单读》:您的爷爷金毓黻先生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1943年曾与李济、傅斯年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史学会,其《中国史学史》是国内史学史研究发端之作。这样一位有赫赫名望的长辈,他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金安平:我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爷爷,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小时候,父母亲都会跟我们讲到很多爷爷的事情,包括很多奶奶的事情。爷爷最不喜欢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抽鸦片,一个就是娶小老婆。他非常尊敬奶奶,但在日记里面几乎不写奶奶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的习惯,是对女性的一种隐晦的尊敬。
关于爷爷,现在大家提及并研究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日记,那是爷爷生前用毛笔一点一滴记下的。爷爷的书法十分漂亮,几本小册装进一小盒,现在都收在台湾中研院,保护得非常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和我们讲过爷爷的日记,但存放在大陆,我们看不到,只知道那是学者式的日记,记了很多学问方面的事,大到他的历史观,小到某一天读了什么书,对某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另外,他写的诗,他朋友给他的诗和信件,他都抄在日记里面。那是特别珍贵的史料。
《单读》:当时他们做研究的方法也是,比如说考据,做编年体例,记翔实而系统的日记,与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也有关系?
金安平:爷爷留下了很多信件、书和诗作,包括写给朋友的小传,名人小传,还有他在重庆教书的时候学生给他的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我看过不少这样的日记,但我觉得爷爷写得最好。他的方式很不一样,当时他受到清末考据派史学家的影响,他也跟着那个模式写,是一个学者系统的思想记录,而不只是日记。
《单读》:那爷爷和您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的授业恩师房兆楹先生,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金安平:房先生以前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去北大听过爷爷的课。听母亲说,爷爷完全是一个读书人,并不擅长直露地授课,所以上课时,他基本是整个人面对黑板,几乎不会转过身来面对学生,就像他仍然是在独处一样,和自己相处让他觉得自在,可以沉浸在他的学问世界中。我父亲就很不一样,父亲是个非常会讲课的人,这可能和父亲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有关。
但无论是爷爷还是我的恩师房先生,他们都是走的考据这一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沿着传统治学的方式在往前走。
*
《单读》:《合肥四姐妹》那本书,和《孔子》这样的历史写作很不一样,是纪实性更强的一本书,有大量的采访在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出来?
金安平:张家四姐妹的缘分,是因为史景迁先生(金安平女士的丈夫)认识张充和,他们是耶鲁大学的同事。一次我母亲来我家,我就把充和请过来吃饭,可能因为那一次的气氛很好,那天她的谈兴很浓,一旦开口,你才知道她的口才有多好,非常幽默,喜欢逗人,甚至会有些善意的刻薄,十分可爱。
平时充和很少讲家里的事,但那天她突然开始讲起她的祖母。因为我之前做过采访,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不停地问,把故事一直往下延续出来,我一边赞叹,她就一边丰富着她们家族的故事,十分过瘾。
第二天我就给充和打电话,问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一起聊一下?以前她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但没想到这次她马上就答应了,这也的确是一种缘分,说不清楚的。她交友的标准十分严苛,而且不是说你是大名人,她就会对你有宽容,她完全由着个性来,喜欢谁就是谁,这也是我十分欣赏充和的一点。
我没想到的是,充和不但一口答应,而且她跟我讲,说你可以回中国去见我的两个姐姐,二姐跟三姐,还有大姐是在加州,她说都没有问题,到时候跟她们写封信安排这件事。我简直不能相信!立即就开始和充和约采访的时间,生怕她有什么变卦。当然也不是正式采访,我们在一起就是聊天,录音的小时数不计其数,而且有时候她会突然问我:对了,我有没有和你讲过这件事?……后来书已经写完了,出版了,跟充和在一起时,她还会突然说:对了,我有没有和你讲过那件事?讲完之后,我就悔之不及,我说充和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讲,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很多非常打动人的事情,她都记得。
《单读》:以赛亚·伯林曾说过:研究历史需要一种想象力。在历史写作中,比如说像《孔子》的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千年前的生活细节、日常场景以及人的行为规范,是需要想象力再综合以资料才能复原的,您是怎么做到,并且把握好那个度?
金安平:首先,对于想象力,我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这可能和我小时候与父亲辩论庄子有关。其次,想象力本身有很多种,有司马迁式的想象力,有《左传》作家式的想象力,班固也有他的想象力,而庄子的想象力简直就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我非常喜欢《齐物论》,那里面就蕴含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想象力。
在写《孔子》那本书时,我看了很多史料,后来觉得像《礼记》里的很多就不是史料,而是讲故事,有关于孔子的故事。你要在多大程度对它们达成一种信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反复阅读汉代的著述,尤其是《礼记》,其中很多的记载是比较晚的,包括有一些是西汉逸闻,故事成分过重,仔细考虑之后,就决定弃之不用。主要以《左传》、《论语》加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里面就有很多历史的场景。
那是寻古的一方面,但同时我又考虑其他的因素。我非常喜欢庄子,尤其是“外篇”《山木》等,我反而觉得庄子是最了解孔子的人,他对孔子有一种“同理心”,这个“同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情,也不是某个向度上的理解,而是一种整体层面上的理解。这就回到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力的问题,历史学家在寻找史料的时候,尤其是研究千年前的主题时,他必须对研究对象有一种强烈的“同理心”,再加上他的历史想象力。
我觉得庄子就抓到这一点了。比如,庄子他对孔子和弟子颜回的关系,就有一种“同理心”的理解,而孔子在谈到教育、谈自己的各个弟子,只是一种道德想象力,这和历史想象力不一样。而庄子两方面都顾及到了,在《田子方》、《山木》篇中,他就在以一种丰富的想象力来抒写,他会嘲笑孔子,同时也会以非常低的姿态来嘲笑自己,以自身为参照系来理解孔子。每个人都有他的瑕疵和缺陷,你可以自嘲,也可以嘲笑他人,将自己和他人放在一种历史语境中,相当于把自己置身事外,来评价、想象和再现一群人,这是历史写作的精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庄子观照出了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所以我在前言中说了,我决定将《庄子》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和研究来源,当然不会太多,因为它在史实上毕竟缺乏可靠性。但从历史的整体的想象力上,它很重要,抓住了本质。
《单读》:最近这几年,中国突然兴起历史热,很多人开始关注历史、研究历史,而且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戏说历史的态度。您怎么看?
金安平: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中国没有严肃的宗教,所以一遇到问题,很容易就到历史、到家庭中去寻找原因和答案。虽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可是家族的亲情依然在,我在国外感受特别强烈,华人家族、血缘中的那种牵绊特别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维系和传承。再有,就像我和史景迁先生这样,受到很多人的恩待,一些只上过一学期的学生,可能会数十年地记得你,师生间的这种感情,对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一种本能,是一种天生的情感。
《单读》:中国的传统就在这里面。
金安平:对,我觉得传统是在这里。所以回到刚才孔子的问题,我觉得好像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一样。对一般人来讲,孔子讲的“礼”并不好懂,但它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像西方那样,“礼”不只是一种礼貌、礼节,它有一种非常深的涵义在里面,它不只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人和人之间恰当关系潜移默化的传承,将人的性情和社会的规则结合在一起,非常好。而且这就像孔子说的“述而不作”,它是我们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而不是做出来给谁看。
为什么孔子的思想历千年而不衰?当然经过了很多演变,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已经变成血脉中的一种东西。中国的思想一贯如此,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它都讲究一个“自然”,从来不强加于人。我觉得这是孔子的聪明之处,他的学说,他创造的这套人类早期文化,这种做人做事的模式,是从人的内心深挖出来的。后来的孟子跟荀子也是一样,无论如何,他们从人的内心催生出一个世俗社会。
(摘自《单读06 逃离·归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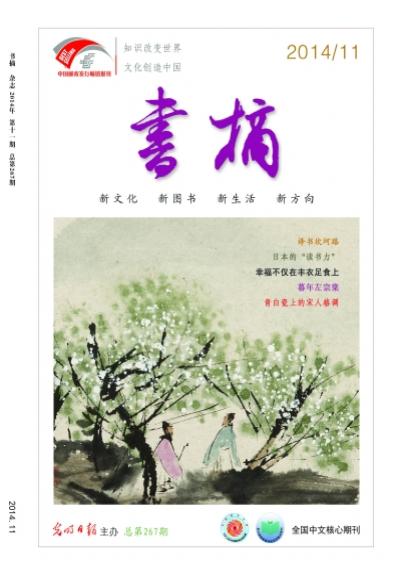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