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驱车穿越布隆迪的西南部。一路上,我总觉得那座名叫甘札的山总是不即不离地跟着我们,就好像小孩子会觉得月亮总是跟着自己似的——前行的公路穿过深卧山间的村庄,转个弯,眼前又映入甘札峰的另一片风光。
每当这个时候,德奥格拉迪亚斯——我的旅伴——就会让司机停下越野车,然后下车走到路边,拿出数码相机拍摄山景。德奥戴着黑色阔边帽,一根线头垂在帽檐的一边。路过的人有的挤在小型客车中,有的骑自行车载着成罐的棕榈油。我暗想,他们一定将德奥当成是游客,看他穿着体面、年轻挺拔、皮肤黝黑,一定是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有钱人。
和德奥一块儿站在路边时,我总会向下俯看高低起伏的山谷间窄窄的农作物带,或是抬头看看陡峭的山坡。山坡上有时是一片草地,有时是种着几片桉树和香蕉树的绿林,不经意间还会发现几间铁皮顶或茅草顶的小房子零星地点缀其中。房子上方的背景就是高高耸起的甘札峰,圆形峰顶上基本没有什么树木,也罕有人家。在基隆迪语中,甘札的意思是“统治”,这不禁让人想起曾经统治布隆迪的历代君王。
布隆迪面积不大,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位于非洲中东部,处在赤道以南地带,横跨刚果河和尼罗河的分水岭。它的南部和东部与坦桑尼亚交界,西部则以坦干依喀湖为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毗邻。布隆迪是个贫困的内陆国,以农耕为经济支柱,出口的主要是优质的咖啡和茶叶。现在,布隆迪的森林面积正在逐年减少,但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地貌。
德奥的眼一刻也离不开山峰,回忆占满了他的脑海。小时候,他和哥哥每个夏天都要沿着极陡的山路吃力地爬过这座甘札峰,头上顶着重物,膝盖不停地发抖。这样的山路每周都要走上一两次。那时候,那片地区树木茂密,他常在树上或林间看到黑猩猩、猴子,甚至大猩猩。德奥说:“现在这些动物都见不到了,可当时那儿的猴子可真多啊!”有一次,他和哥哥在爬山的中途休息,一群猴子围了上来,像一帮流氓恶棍似地故意招惹他俩,试图把他们袋子里的木薯抢走,甚至有一只猴子扇了他们几巴掌!最后,他和哥哥不得不扔下木薯溜之大吉了。
德奥笑着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已经能分辨出这种笑容就是他平日谈笑时的样子,就像他和朋友打招呼时喊的“嗨——”尾音拖得长长的,仿佛不想结束。他的笑声也和招呼一样爽朗,稍显尖锐,令人又惊又喜。他的英语带着点法语和布隆迪语的味道,偶尔也会发错重音。比如,当说“我一想到这事就想笑”时,他总会把“到”这个字发得很重。而且他用很多混合的表达,生动并有些夸张。像是“疼得我想把它从肚子里挖出来”、“像暴风雨般奔跑吧”和“真恨不得在我心上咬一口”。
德奥是在甘札东部山区长大的,他住在一个叫不坦札的小地方,那里有些农田和牧场。过去六年间,他多次回布隆迪,却都故意避开不坦札——他已经有将近十四年没有回去了。现在,他终于决定回去看看。现在看到了甘札峰,德奥显得很高兴。可是当我们东行越来越靠近他的故乡时,他虽没有完全沉默不语,但话却越来越少。要知道,他平日里是一个那么爱说爱闹的人。
又行驶了一段,车子开下了铺砌好的公路上了一条土路。这条路越来越窄,最后干脆变成了一条凹凸不平的斜坡小道。这时德奥对我说:“我们快到了。”但在那之前,我们还要沿着斜坡上行,爬到一片牧场。很多年前,他最好的朋友克洛维斯就是在那里病倒的。德奥说要到那里转转,接着他又说:“等我们到了不坦札,不能提起克洛维斯。”
“为什么?”我问。
“因为在那儿,人们不会提起死去的人,总之,不会说他们的名字。这在我们的语言中被叫做Gusimbura。比如,你说‘哦,你的爷爷’,然后你念出他的名字,人们就会说你Gusimbura他们了。这不是个好词,因为你这是在提醒人们……”德奥渐渐没了声音。
“是在提醒人们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
“没错。这可能不好理解,毕竟在西方……”德奥的思绪又断了。
“人们总愿意努力不要遗忘?”我接道。
“对。”
“而在布隆迪,人们试图能忘记?”
“嗯,就是这样。”他回答。
(摘自《生命如歌》序言,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9.50元)
虽已无法寻回那时
草之光鲜,花之芬芳
请不要悲伤
从中汲取
犹存的力量
最初的感动依稀
存在于摆脱痛苦的慰藉中
信仰超越了死亡
岁月沉淀了从容
——威廉·华兹华斯《颂:儿时记忆的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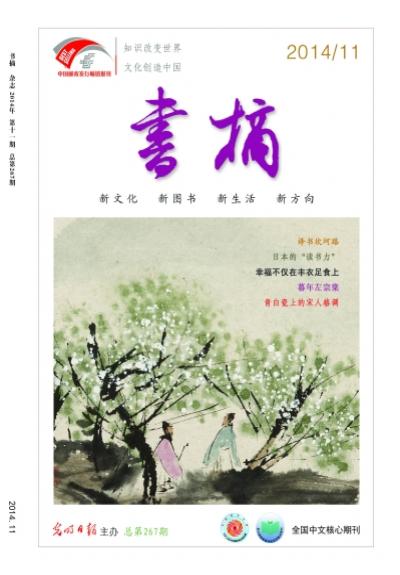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