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应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率领六人组成的访华团,开始他的中国之行。对泰戈尔的态度,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截然不同:梁启超、徐志摩等热情欢迎,而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则攻击甚力,鲁迅在杂文中谈及泰戈尔访华,语气略带嘲讽……无论如何,泰戈尔访华,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
今天集会使我记起我初到中国那一天也在这里园地上接受你们初次的款待。那时候我总算是一个生客,我也不相识那天来欢迎我的诸君。我一向总是在我的心里踌躇,究竟中国是否像我意想所构成的中国,我也踌躇究竟我能否深入这民族的心曲。那天,我的心里很是不自在,因为在你们看来我是从一个神秘的地域来的,我又是负有一个过于浮夸的名誉,因此你们对于我的盼望也许不免有不切实在的地方。所以我急于告诉你们我的有限的资格,我记得我开始就供认给你们我仅仅只是一个诗人。
我知道你们曾经邀请过欧美诸邦的名人,大哲学家与大科学家,远渡重洋到你们的国家来讲学,现在我也来到你们的中间,我很惭愧我自己的渺小,你们都曾经亲听过他们的至理与名言。那天我真是深深地引愧,因为我觉得仿佛我是穿着一身乔装来收受你们款待的至意,也许你们并不曾认识我本来的面目。我不由得想起我自己的一篇戏里那个女子齐德拉,她是承爱神的怜悯取得了一身美艳的变相,她原来并不是一个没有缺憾的妇人。但是,等到她后来凭着这神异的幻象征服了她的爱人的恋情,她反而嫉恨她的温柔的化身,因为她所渴望的他的抚摩与交抱都被这偕来的外壳掠去,剩下她的灵魂依旧在不满足的冷落中悲切。
今天是我在你们的国里最后的一天,如果你们还是准备着厚意的款待并且给我称誉的言词,我可以放心接受的了:因为我已经经过了你们的考验,我想也并不曾缴还我的白卷。所以,今天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满心热炎地只想望你们的友爱与同情与赞美。这是你们披露你们真情谊的机会,好叫我永远记住,虽则我不能不向你们告别,这最后的一次集合,像一度奢侈的落日,大量地铺陈它储积着的异样的彩色。但是,话虽如此,我还不敢十分放心。在你们中间有跟着我此次巡游的,他们最亲切地知道我的成绩,还不曾开口说话。
方才说话那位主人赞扬我的成绩,他自从我们初次会面以后一直病困在家里。他不曾有机会接近我,因此,他关于我的想象,我不敢过分的深信。因此,我还是等着要听还有几位朋友的意见,他们这一向不幸地须得伴着我起居与行旅,他们应得认识我的浅深。
同时,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对你们说。初来的时候我也有我的盼望,在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象中的中国,此后那丰流富丽的状态天朝竟变了我的梦乡;早几年我到日本时,我又得到了这古文明的一瞥。因为在那边款待我的主人有大宗中国名画的收藏,都是珍异的神品,我在他那里住着的时候,他常常一件一件取出来饱我的眼福,我也凭陪他的指导认识了不少名家的杰作。因此,我又在你们往时大艺术家的作品里取得了我的中国概念。
我心里时常存想,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创造了一个美的世界,我以为即是你们灵魂的表现。我记得每次我遇着不甚尊敬你们的那些人,我总觉得难受,他们的心是无情的,冷酷的,他们来到你们中间,任意地侵略与剥削与摧残,他们忘怀你们文化的贡献,也不曾注意你们伟大的艺术。
当然,你们也知道你们以往的历史所凝成的纯晶,不仅是真的美的,并且是神灵的,并不代表你们人民的完全的生活,虽则我同时亦深信,只有从最完美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的最真切的一斑,但理想与实现是应得放在一起看的,我们不能偏注一面。至于我此番的游历,我不能不说在简短的时期内要盼望一个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能够发现一民族最内在的真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将来也许有那一天,但绝不是造次可以得到的。要明白一民族潜在的力量与天才怎样能逐渐地发展到最完美的状态,那是千百年的事,我既没有时间又没有适当的机会,因此,我不敢想望有多大的了解。
我只感觉到一件事情,我此次在你们的国内会着的外国人也都有这样的感想。你们是很近人情的。我也觉着你们的人情的感动,因此,我已经(至少我希望我已经)接近你们的心曲。我自己的心里不仅是充满着羡慕与惊讶,但有的是真挚的情感,尤其是曾经与我有过亲密的交接的,我不由得不爱他们。这一点个人间情感的契合便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事。
有人说你们有一个特性,就是你们从来不曲解事物的本相,是什么只当是什么看待。譬如你们看重一件东西或是一个人,你们看重他,不是因为他在本身以外另有什么连带的价值,但只为是他那赤裸的现实现放在你的眼前,要求你的注意。也许就为你们有那个特性,所以,你们这一晌也只把我当作一个寻常的人看待,不当作一个诗人,更不如有的傻子以为是哲学家,尤其不如有的更傻的傻子以为我是圣人或是先觉,你们只把我看作一个干净净的个人。
有几个我新结识的小朋友对我差不多绝对地不存拘束,只当我是和他们一般年纪,不见得怎样理会我的高年,也不过分尊敬我的声名。这样的健忘本应得使我着实的懊恼,但在他们却是充分的自然,因之,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差池。实际上,他们对待我的情形常常没有丝毫的尊敬,我却是很感谢他们的随熟与失礼。世上人多的是想把我供作偶像,剥夺我现实的人情与接触。我想上帝也一定着恼,因为人们把日常的情爱分给了他们的家人与同伴,留剩给他的却只是在教堂里每星期的礼拜,我所以很喜欢我的年轻的朋友不曾把我当作偶像礼拜,他们只把我看作他们伙伴中的一个,使我得沾润他们活泼的人情。
但是,你们要我在离别以前给你们不掩讳的批评,我绝对地拒绝你们的请求。批评家随处都有,你们不怕缺乏,我却是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品级。他们曾经听受过你们的批评,谁不会批评,我却自喜我没有那样挑剔的天才。我自己也是近人情的,我自然可以体谅你们的短处,你们即使不免缺陷,我还是一样地爱你们。现在世上有的是胜利的民族,在他们的跟前我是什么样人,敢来妄肆批评?彼此同是受嘲讽的民族,我们有的是不受人尊敬与赞许的德性。我们正应得做朋友。
我没有批评给你们,所以请你们对我亦不必过于苛责。其实我此时已经不免心慌。有一天,你们青年的批评家在我的面前不容情地指责他们曾经请来讲学的几位,我那时就觉得兆头不好,我就急急地问他们将来是否预备给我同等的待遇。我始终不曾放心,我此时也不说我心里的话,我只希冀他们不会那样地忍心。我从不曾装作过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因此,我想我不必着急。假如我曾经置身在崇高的台座上,他们竟许会把我倒拉下来,闪破我的脊梁,但我幸而不曾有过那样的潜妄,我只是在同一的平地上站看,因此,我盼望我可以幸免灾难。今天,我最后分手的一天,才是你们真正接受我的一天。我上次在此地时你们给我的欢迎只是借给我的信用,我盼望我曾经付过我的代价叫你们满意,但如你们以为我不曾付清你们事前的期望,不要责备我,你们只能抱怨你们自己的糊涂。你们当初便不应得那样地慷慨,不应得滥施你们的奖宠。
我敢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可能的名分,我结识了不少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已经发生了一种情谊的关系。我并不曾妄想逾分的了解,我也只接受你们来意的至诚,如今我快走了,我带走的也就只这一层友谊的记忆。但同时我亦不须自为掩讳。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我的部分并不完全是同情的阳光。
从天际辽远的角下,不时有怒云咆哮地作响。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地不曾存心与你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你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我可吩咐他们,我并且不曾折服一个怀疑者,使他憬悟他的灵魂的实在,我不曾使他信服道德的美的价值是高于物质的势力。我敢说,他们明白了结果以后一定会得赦免我的。
[志摩附识]
那天下午听着老翁这篇告别辞的诸君,也许还记得他说话时的声调与他须眉间异样的笑客。他的声调我记得和缓中带踌躇,仿佛是他不能畅快地倾吐他的积愫,但他又不能不婉转地烘托出他的不完全愉快的款曲与感念;他的笑容,除非我是神经过敏,不仅有勉强的痕迹,有时看来真是眼泪的替身。“我的不幸的运命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我的部分不完全是同情的阳光;”这话是称过分量说出来的,就这一点不说分明,不说尽,这里面便含着无限的酸楚,无限的悱懑,我当时真觉得替他难受。
“现在世上有的是胜利的民族,在他们的跟前我是什么样人,敢来妄肆批评?彼此同是受嘲讽的民族,我们有的是不受人尊重与赞许的德性。我们正应得做朋友。”这一段话,且不论他反激得动人,我正不知这里面的成分是泪还是血,我们听了应得傲慢还是应得惭愧?
他现在已经远了,他留给我们的记忆不久也会得消淡,什么都不免过去,云影扯过了,波心里依旧是不沾印迹,也许有人盼望天光完全隐匿,那时任凭飞鸟也好,飞云也好,我们黑沉沉的水面上连影子都可以不生痕迹!
(摘自《泰戈尔:我前世是中国人》,辞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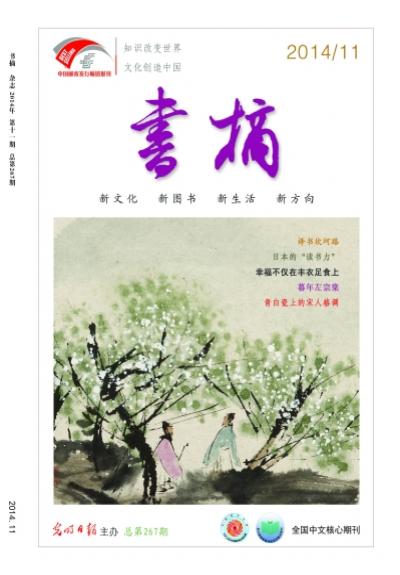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