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的作者杨显惠说,她断断续续读完《生死故乡》,脑海里出现了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在中国文坛争先取媚邀宠的大背景下,这部书写出了这三十年的农村史,难能可贵。可以说这是一部新的《生死场》。”本文摘选自书中一节。
母亲叫我试试。一件花方格上衣,红白相间,在北风洗劫、草木裸奔的南太行冬日乡村格外醒目。我刚从外面疯跑回来。虽然前几天下了一场雪,房檐上挂满了针头或小葫芦一样的冰溜子,空气冷得冬麦都拉着干土睡大觉了。而我们这些孩子不怕冷,手冻得像冰糖葫芦,鼻涕挂在上嘴唇。几个或十几个同龄孩子,拿着弹弓、弓箭、手枪、长棍等木质微缩冷兵器,你打我闹地把整座村庄冬天搅得风生水起。
大人们坐在屋里抽烟,围着火炉把脸和手心烧红。我爷爷是一个讲神鬼僵尸故事的绝顶高手,一到冬天,好多人围着他,给他香烟,让他讲一个,再讲一个嘛。
这样的日子年年如一,人还是那些人,事儿还是那些事儿,可是风和风中的树木茅草尘土却不是去年的了。从八岁那年开始,我就觉得,整个村庄的冬天单调得像一个老汉拿着一块石头翻来覆去地丢,一次次甩出,撞到南墙上,冒出点响声,然后再捡回来,这一行为当中,预示着整个世界都患了孤僻症。而一进入腊月,心里就有了一点莫名兴奋,好像一根二胡弦子,无意中被手指碰了一下,嘶哑而有快感的声音令整个南太行乡村冬天的生活有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过了腊月十八,冷不丁有人在自家院子外燃放了一枚鞭炮,脆响把乌鸦吓得往天空逃窜,小灰雀也钻进草丛或房檐。
我穿上母亲做的花方格衣服,自己看了看说,这是傻妮子们穿的嘛,我不要!母亲嗔怪说,你才豆丁大,啥妮子小子的,就穿这件过年了!我要脱,母亲说脱就脱吧,到年三十再给你穿。我哼一声,甩下红方格衣服,一扭屁股,就又钻进了裹着雪粒在村庄巷道里乱窜的北风中。晚上回家,我说,娘,人家老军蛋家买了好几挂鞭炮,大大的那种,一根炸响,俩耳朵打忽闪!咱家啥时候买?娘放下正在揉的面,把面手擦了擦,又去拿白萝卜配鸡蛋韭菜做的馅子。
我说娘你咋不理我?娘说,没见我在忙啊!
天刚发白,我就醒了。娘还在睡,灶膛里的木疙瘩火早就成了白色灰烬,偶尔有三两颗火星被从门槛下挤进来的风掀起,在尚还暗黑的房间里格外鲜亮。我摸索着穿衣服。娘醒了,看了看我说,儿子你干啥?我说我起来去代销点买鞭炮。娘说,你去吧,没钱看人家给你不!说完,又翻转了身子,朝墙睡。我大声说,那我该咋办?娘不吭声。我在炕上坐了一会,想想娘说的是真理。
我一个人无聊地在渐渐明晰的凌晨坐了一会儿,冷。母亲把我揽在怀里。我又问,爹啥时候回来?母亲说,应该快了。我又问,爹回来会带很多的鞭炮吗?娘说,能带回点钱就啥都有了,不说鞭炮,连羊肉也有了!
我说,娘你不是不吃肉吗?我也不吃。
娘叹了一口气说,你爹要吃,你弟弟也要吃。还有你爷爷奶奶,老了,当儿子儿媳的,过年得买点送去。
天亮了。外面有了人行的声音,鞋底噗噗、沙沙地,清脆而又不明所以。正要穿衣,一声爆竹声从村子上面传来,声音窜到对面山坡上,弹回来,再震响我的耳膜。从方位分辨,我知道肯定是老军蛋燃放的。他爹是大队支书,虽然也种地养牛羊,但家里好吃的好玩的总比我多。
我也问过母亲。母亲说,人家爹是大队干部。我说为什么干部的孩子就有那么多的好吃的和好玩的?母亲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
北风一天比一天紧,村子内外的树都成了光条条。黄昏,母亲正在蒸馒头,一个人背着行李卷,挎着一个黄布包踏进家门。我一看是爹。他掸掸身上薄薄的一层雪,摘掉头上的黄皮帽子,冒出一股白气。我说爹你头上冒烟了。他说是汗。歇了一会儿,父亲起来把行李卷缓慢打开,拿出几包饼干、糖块、瓜子,香烟等。我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多想那里面蹦出一串红鞭炮啊!可直到父亲把所有东西都摆出来,又从棉袄里摸出一沓子钱,递给母亲,还不见我渴望的鞭炮。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热爱鞭炮,总觉得,过年就是放鞭炮,吃什么都不要紧,鞭炮一定要有。每年大年初一凌晨两三点钟,鞭炮声就此起彼伏了,你一挂我一挂地燃放,噼噼啪啪的声响把枯寂了一年的村庄炸得热火朝天,山峦沟谷也热烈响应,整个村庄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笑逐颜开、生动吉祥。
孩子们一手拿着鞭炮,一手拿着燃着白烟的木棍,在院子、巷道、路边和碾道上炸出响声。年纪小的点着炮捻子就跑,一边捂耳朵,等炮炸响,讨论下响声大小,顺势再燃放一枚。更好玩的是把一枚鞭炮放在雪里,或用土埋住,点燃爆炸,看雪被淬黑,沙子被炸飞。还有的,是把鞭炮放进罐头瓶子或破旧瓦罐里,看瓶子碎裂或嗡响,瓦罐无奈地弹跳几下,再滚到别处。年纪稍大一些人,则喜欢燃放二踢脚,手抓中间部位,用烟头点着捻子,二踢脚爆响,下半身砘在地上,上半身腾冲而起,到半空炸响,声音大得似乎能把玉皇大帝的耳朵震聋。
我看父亲没带回鞭炮,他给我饼干和糖,我哼哼着不吃。父亲说你要啥?我说咋不带鞭炮回来。父亲说,在车上,那么多人抽烟,点着了,满车的人不都“嘣”一声震出去了吗?我说我不管,我就要鞭炮。父亲说,先吃了饭,一会儿我带你买去!我刚嗯了一声,心还没乐开花,就听母亲呵斥说,你哪儿来的钱给他买鞭炮?父亲笑着的脸立马被冻住了,说还留着点买烟的钱。
夜晚的乡村冷得穿大衣屁股也还冰凉冰凉的,领口稍微有点缝隙,风就钻进来,贼寇一样扫荡全身。我缩着脖子,父亲拉着我的手,往二里外的代销点走。老远就看到平日里黑黜黜的代销点灯火通明,很多人在,买香烟、酒、糖、瓜子、对联、灯泡以及蜡烛、柏香、冥纸和银锭等祭拜用品。父亲买了一些别的,问我要啥鞭炮,我说要大的10挂,小的10挂,再买点二踢脚。父亲说,哪有那么多钱,少买点。我说人家老军蛋家一样买了30挂,二踢脚大小500个。父亲说,少买点,等以后长大了,你当了大队支书,买1000个我都不说你半句。
父亲点了一根香烟,递给我。我拆了一挂鞭炮,放在路边,用父亲的烟头点着,转身就跑。可能太紧张,根本就没点着。再哆嗦着冻手去点着,再迅速跳开,脚还没落地,就传来一声脆响。连河沟都有了响声,冻成冰的流水下面还有水,鞭炮声似乎钻到冰下,跟着流水传到了五里外的石盆村。父亲边走边对我说,回家再放吧,不然人家不知道是你放的,鞭炮是咱买的。我想想也是,跟在父亲后面,抱着十几挂鞭炮带着寒风闯进了家门。
*
大年三十,气氛庄严肃穆,像一种古老而神圣的仪式。入夜,烛火遍布家院,光辉摇曳,柏香袅袅,味道泛滥。父亲要我把鞭炮放在桌子上,不要放在抽屉里。我说为啥。父亲说,大年初一,太阳没出来前,不能开抽屉,不然,一年的钱财就散尽了;母亲说,初一早上也不能拿针,拿了舅舅就心脏疼,也不能泼水,水也是财,连洗脸水和尿都不能倒掉。我说这都是些啥规矩?父亲说,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父亲把包好的饺子放在水瓮上,老鼠够不到,父亲把香烟糖块之类的也放在桌子上。跟着父亲去给爷爷奶奶送了些年货,回来躺下后,父亲说明早上不管谁起得晚,都不能说“还不起床”,那样说,就相当于叫人生病,连炕都不下了。要说了“起了!”
母亲拿出早先给我试过的那件花方格上衣,放在我枕边,叫我一早起来穿上。并随口说,过年了,穿新衣,人家孩子穿上的,俺也要你和弟弟都穿上。我嗯了一声,尽管心里还有些抵触,但相对于一大早起来肆意燃放鞭炮的快乐,这已无足轻重。睡到三点,我就睡不着了。闹着要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鞭炮二踢脚响了起来,不用听,还是从老军蛋家院子里传来的。我赶紧穿上衣服,跳到地上。
没有风,就是冷,手伸出去,像是有一群小虫子,使劲咬。我先点燃了一挂鞭炮,三百响或者五百响,把猪狗鸡都惊得乱哼胡叫。再看村里,一家家都打开了灯笼,一阵阵的鞭炮响彻山间,连后山的悬崖也积极回应。母亲起来了,父亲在灶台点火。开始冷冷的家里,一下子就温暖起来。我烤烤手,再出去放鞭炮。母亲把饺子煮好,我猛吃几个,又蹿到门外。父亲还没吃完,我就催他去爷爷奶奶家。
大年初一早上必给长辈磕头拜年,村村、家家如此。我和父亲端着饺子,走到爷爷奶奶家,他们正在吃饺子。我和父亲单膝跪地,父亲叫爹娘,我叫爷爷奶奶。爷爷奶奶说来了就好了。父亲会坐在灶火边,奶奶给他盛一碗饺子,说是羊肉馅的,父亲爱吃肉,几口就吃下了。然后带上我,去给其他长辈拜年。遇到比他小的人家,他在外面等着,让我一个人去。每去一家,单膝跪地,磕头,都能收获一些大大小小的鞭炮,转一圈回来,四个衣兜都装满了。
回到家,太阳还没出来,母亲就让我陪她去土地庙。她拿着馒头或饺子,去给土地爷山神磕头,念叨一些话,我在旁边燃放鞭炮。太阳刚在东山尖上露了一个头,感觉村庄崭新极了,不管房屋还是茅厕,都像涂上了一层釉彩,亮亮的,滑滑的,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大都会一家人坐在一起,围着火,喝两口酒,说些东南西北的话。我们则在院场里比看谁挣得鞭炮多。然后肆意燃放,把新出的太阳都炸得在冰溜子上晃个不停。
中午吃了一点东西,再出去玩了不大一会儿,天就又黑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嚼食的声音在处处崭新的房里响动。收拾了碗筷,父亲说,今晚好好睡会吧!我说我还想出去放鞭炮。母亲说,傻孩子,你听听谁还放鞭炮唻!等到正月十五再放!我说过年不是天天可以放鞭炮吗?父亲说,这是有规矩的,除了春节和红白事儿,放鞭炮就是糟蹋钱。
村子果真没了鞭炮声,就连老军蛋家也早关了灯笼。我才知道,所谓的春节也只是半天热闹。父亲看我闷闷不乐,帮我脱了衣裤,放在他被窝里。一家人躺下,除了风和偶尔三两声狗叫,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夜晚温热,炭火在灶膛里独自明灭。
(摘自《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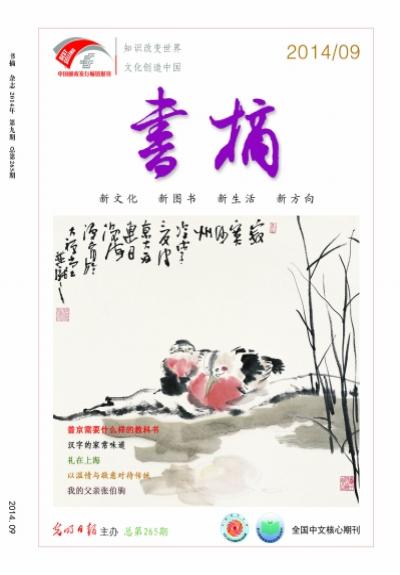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