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中,至少有两位叫我服气和喜欢。一位是史铁生,文笔细腻考究,文气舒缓沉静,有一对默默凝视宇宙的心眼。另一位是王小波。王小波同史铁生相反,文笔腾挪迅速,犀利机警,出言无忌,妙趣横生,确如一个敢说皇帝正在光屁股的顽皮的孩子。不过,我喜欢他还有一个相当私人性质的原因,那就是他和我有若干相似以至相同之处:同年来到这个世界,同年去干农活,小时候同样不愿意说话,上大学之前同样只读了七年书。这还不算;近日重看他的《我的精神家园》,发现我们两人的精神家园的缘起体验也很相似。
他的那本《我的精神家园》随笔集中有一篇文章就叫《我的精神家园》。文章说他13岁时经常从他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爸爸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德赛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因为偷书——有时是被哥哥唆使——而挨了他爸爸好几次揍,但挨揍“也不后悔”。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爸爸和他的书箱。小波的爸爸是大学教授,有书柜,而且一定是一排排装了很多很多的书的书柜。我爸爸是半山区一个“人民公社”(现已改为“镇”)小小的基层干部,没有书柜,仅有一个书箱。小时家里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装衣服的,颜色算是紫红吧,是母亲的嫁妆。不大,一个人就可以抱起。另一个即爸爸的书箱。这个大些,一个人抱不过来。但做工明显没那么好,黄色,油漆有些斑驳了。箱盖也没有回扣的四边,只是一块书桌面大小的平板。其实并非专用书箱,装什么都可以,只因爸爸用来装书,就成了书箱——他没有书柜、书橱、书架,有了也没地方放。家实在太小了,也太穷了。
书箱里装满了书,一摞摞堆起来,十几摞挤在一起。找下面的书,必须把上面的书都倒腾出来。我也从十二三岁时开始翻爸爸的书箱。里面既有《青春之歌》和《战斗的青春》,又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爸爸倒是不锁,但在箱盖内侧的正中间贴了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道“不要看旧书”,掀开箱盖这几个字正好对着眼睛。爸爸所说的旧书,指的是古书,即使封面很新也是旧书。而我偏偏喜欢看这样的旧书。趁爸爸下乡或去县城开会一连几天不在家时赶紧把书箱翻个底朝上,把压在最下面的旧书找出一两本,再尽可能按原样把上面的书放回摆好。每次这样做时心里都怦怦直跳,不时瞄一眼窗外,生怕爸爸忽然从外面回来。我不知道爸爸到底是从未觉察还是觉察也佯作不知,总之一次也没被他骂过,更没像王小波那样因此挨过揍。于是,我得以一本接一本看爸爸书箱里的书。看完旧书看新书,看完新书看旧书。回想起来,书箱里充其量也就一二百本书,但在当时我的眼里,无疑是书库、书山、书海。晚上趴在书箱盖上点一盏煤油灯或白天在西山坡松树林里靠着树干看书,是我一天中最欢喜的时光。
说来也怪,那时候看书我就对字本身很着迷。也就是说,较之故事情节,很多时候我对词语的节奏感和文采更有兴趣。每看一本书都要把描写风景、人物的长相和心情、志向的漂亮句子抄在硬壳本上,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复习一遍。即使“文革”爆发后在乡下务农期间也没完全停止。这样,早上出工时望着田野上方轻轻飘移的白色雾霭,傍晚收工路上望着远方天际璀璨的夕晖,夜里躺在炕上望着窗外银灿灿的满天星斗,脑海每每现出相应的漂亮句子。如果没有书,没有书上的漂亮句子,没有对书和字的迷恋,我恐怕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在很多人沉沦的蹉跎岁月里随之沉沦,也不会在日后不少同学下海经商或改行从政的风潮中始终以书为友——看书、教书、译书、写书。
看书,至今仍为一句漂亮的表达兴奋不已,那是神奇的邂逅;教书,最快意的莫过于目睹语言在教室学生脸上激起的浪花,那是交流的快慰;译书,任凭笔锋捕捉另一种语言的律动和喘息,那是转达的喜悦;写书,眼看胸中所感所思接连注满绿色的方格,那是创作的幸福。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字。我时常想,如果生活中没有书没有字,而只有图像、手机、汽车、烟酒和山珍海味,那会是怎样的生活呢?那会是健全的生活吗?至少对于我不是。我害怕图像掏空我的想象,手机劫掠我的修辞,汽车惊散晨雾和夕晖,烟酒忽悠爸爸的书箱……一句话,怕它们侵蚀或置换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还有一点让我觉得我和他共享一个精神家园——他在那篇《我的精神家园》后半部分提到了牵牛花: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喧嚣都考虑在内的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其实,小波在这里并不是想说服安徒生,也不是想评说维特根斯坦的事业,他只是想说牵牛花,只是想在“我的精神家园”里说牵牛花,那有可能是他的精神家园里开放的唯一的花。这让我觉得我和他“是一头儿的”。一棵牵牛花,长蔓这一头牵着我,那一头儿连着他,两头儿也是“一头儿的”。
牵牛花是我最早认识和嵌入记忆的花。从十二三岁开始,就和爷爷奶奶住同一座草房,我和父母住东头,爷爷奶奶住西头,院是一个院。奶奶最喜欢种牵牛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场景:我在东屋放下从爸爸书箱里翻出的书,走到院子就看见西屋窗前的牵牛花。是的,每到夏秋时节,小院木篱笆就忽一下子爬满牵牛花,平日寂寞的小院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就好像突然来了一群花枝招展、唧唧喳喳顽皮的小姑娘。不过花的颜色并不全是小波笔下的紫色。紫色固然最多,但也有其他颜色,粉色的、白色的、淡蓝色的、白蓝相间或白紫相间的,五彩缤纷,争妍斗艳。牵牛花比人醒得早,人还没睁眼没张嘴,牵牛花就悄悄张开嘴巴,张成一个个玲珑剔透的小喇叭。薄薄的,颤颤的,嫩嫩的,艳艳的,水灵灵,娇滴滴,玲珑剔透,楚楚动人。真想上去吻一口,用舌尖把上面晶莹的露珠舔进嘴里。那是真正的花篱。花篱外面跑着叫着七八只芦花鸡和三五只白鸭,花篱里面有一排金灿灿的向日葵,有好多架黄瓜和两三垄西红柿。说来也怪,六个孙子孙女,奶奶单单喜欢我这个长孙。鸡鸭下蛋了,第一个煮给我吃;黄瓜长大了,第一根塞给我啃;西红柿变红了,第一个留给我尝。奶奶屋梁上悬一个不大的柳条篮,她每每从篮里摸出小红灯笼似的西红柿给我。记得最好吃的是一种叫毛柿子的西红柿,桃形,不大,顶部有尖,毛茸茸的,咬一口能甜得人发抖。奶奶自己却不舍得吃,笑咪咪看着我狼吞虎咽。对了,篱笆西端有一棵不高的杏树,牵牛花在篱笆上爬不开了,就爬到杏树上去。杏熟的时候,嫩黄色的杏有的贴着牵牛花,有的在牵牛花下捉迷藏。它们当然逃不过奶奶的眼睛。奶奶拎个小筐摘下来,等我放学回来吃或第二天塞进书包让我在上学路上受用。那时不比现在,艰苦岁月,贫穷乡间,有杏吃已经美上天了。
现在,看见牵牛花,眼前有时就浮现出已经去世三十多年的奶奶慈祥的面影,甚至嗅出嫩黄瓜的清香,舌底生出毛柿子和黄杏那甜甜黏黏的汁液,心头泛起悠悠忽忽的乡愁……
不过,我的生命旅途中有好多好多年没有牵牛花开放。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乡,远走天涯,南下广州。广州以花城著称,木棉花,玉兰花,紫荆花,鸡蛋花,扶桑花,到处是花,四季皆花,正可谓“花花世界”。唯独没有牵牛花。那些花当然美丽,但对于我仅仅是视觉上感官上的美丽,而没有精神上的联系和情感上的沟通。一句话,那里的花不属于我,那不是之于我的花,不是开在王小波和我的“精神家园”里的花。
上个世纪末,我借开会之机,由济南转来青岛。来青岛必去海边。那时从海边直线走回我住的旅馆,要穿过一大片渔村。渔村虽大,却很安静,几乎见不到人。房舍多是青砖平房,都带小院。我在院落之间的小路东张西望慢慢走着。烤地瓜的香味。摊煎饼的香味。月季花,凤仙花,鸡冠花。久违的味,久违的花。我知道,我的心的那层硬壳正在缓缓剥离。又走了一会儿,忽见一堵残缺的青砖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深紫色的、粉红的、淡蓝的、条纹的,薄薄的花朵在阳光下抖出妩媚的光彩,但多少透出几分疲惫,似乎等我等得太久了,累了。我忘情地心疼地看着她们。一股莫名的乡愁从心底缓缓涌起,眼角甚至有些湿润。
命运这东西也真是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是不是牵牛花的关照——回广州不久,青岛一所大学即问我愿不愿意来青岛。于是,1999年初秋我告别广州,北上来到青岛。倏忽十年过去。
我不太清楚乡愁和精神家园是怎样一种关系。在我身上,二者既好像有所区别,又似乎是一个东西。如果说,爸爸不到一立方米的书箱不断扩展它的边框或疆域,最后幻化为我的精神家园,那么精神家园的正中开放的,就是祖母木篱笆上的牵牛花。在这个意义上,乡愁或可说是其他所有精神、所有情感的基石和酵母。由此生发出悲悯、仁慈和爱,生发出文学情思和日常美感。那不仅仅是怀旧,也是一种向往,不仅仅是惆怅,也是一种顽强,不仅仅是感怀,也是一种信仰。而其理性结晶,我以为就是良知。施之于教育,使得我叩问大学的灵魂和教授的操守;施之于文化,使得我懊恼文字的窘境和优雅的消失;施之于社会,使得我质疑镇长的奥迪和娃娃鱼的遭遇;施之于翻译,使得我选择并坚守了村上春树和他的“高墙与鸡蛋”。就此而言,乡愁也是一种力量,一种无形而强韧的力量,而这未尝不是精神家园的力量。
最理想的状态是:那只油漆斑驳的书箱爬满了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而我,就偎在旁边看书……
(摘自《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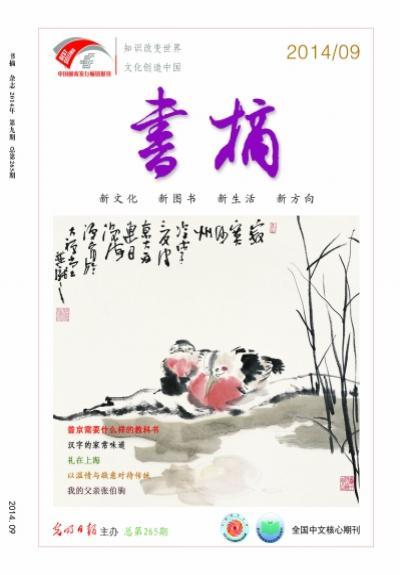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