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24年8月到北京的。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北京市民也常处于不安之中。对刚满20岁的父亲而言,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首要的是解决生活问题,他找了一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来。
到北京前,乔松岩写信把父亲介绍给自己的同学常乃德。常乃德字燕生,山西榆次人,榆次的常家是有名的晋商家族。常乃德于1916年和乔松岩同时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乔松岩在理化部,常乃德在史地部。常乃德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授历史,是教育界很有名望的教育家和学者。常乃德又介绍父亲认识了董鲁安,董鲁安是河北宛平人,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教语文,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著名的现代修辞学家。董鲁安为人乐观,非常潇洒,很有名士风度。父亲到北京,拜见了常、董两位先生后,就去报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没有考上,非常失望。常、董二位想帮父亲找个誊写工作或做家庭教师,以解决生活的困难,也没有找到,董鲁安感叹而幽默地说:“在北京做大事易,找小事难。”这时,恰好梁漱溟先生在曹州办的重华书院(也称曲阜大学预科)招生,常、董二位都劝父亲去报考。
父亲去参加入学考试,结果考了第一名。出乎父亲意料的是,考试完后,梁漱溟亲自到小旅店来看望他这个穷学生。父亲回忆说:“中秋那天晚上,我生着病,一个人在宿舍里,冷冷清清的。先生来看我,拉着我的手说,他一旦认准一件事必需做,是妻子儿女都不顾的。”梁漱溟不仅鼓励父亲克服眼前的困难,而且答应免除他的学杂费,还负担他食宿。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把父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在去曹州之前,中学同学赵吉成给他报名,又参加了朝阳大学的入学考试。父亲到曹州后,梁漱溟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佛教、印度哲学,父亲的志趣在文学和历史,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不想走宋儒理学的道路。这时候,赵吉成来信,告诉父亲已被朝阳大学录取的消息,劝他回北京学习。父亲也想回去,就把想法跟梁漱溟谈了。梁漱溟深为理解,欣然同意,于是他又从曹州回到北京。父亲和梁漱溟的这段师生缘虽然短暂,仅一个多月,但梁漱溟学问的博大精深,为人的宽厚善良,对学生的爱护支持,却在父亲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漱溟从此成为他终身敬重的老师,也是继乔松岩后的第二位恩师。
回到北京后,父亲又过起了穷学生的生活。他有时住在政法大学赵吉成住的大方公寓,有时住在师大同学吴继汉的住处,每天步行到海运仓上学。在朝阳大学的同乡会上,认识了张友渔、侯外庐等人。父亲原想在朝阳大学申请津贴,没有申请到。因为经济困难,大概在校不到一个学期,就辍学了。
北京10月以后,天气渐渐寒冷,父亲的衣、食、住都成了问题。正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有一天,父亲遇到中学同学阎采真(学名耀明,五台胡家庄人)。阎采真多年来一直追随景梅九,做他的助手。景梅九名定成,1882年生,山西安邑城关(今运城市盐湖区)人,是辛亥革命的元老。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在陕西组建同盟会分部。1911年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进行革命宣传,这张报纸在推动辛亥革命起过很大作用。当时人认为《民报》和《国风日报》的作用可抵百万大军。在政治上,景梅九是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景梅九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才华横溢,也是作家、红学家、戏剧家,有“南章(太炎)北景”之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写了《讨袁世凯檄文》,被称为“天下第一檄文”,他还在陕西组织了护国军讨袁。《国风日报》后来被北洋军阀查封,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陕军将领胡景翼,组成国民军,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并电请孙中山进京商讨国家统一大计。北京的政治气氛从北洋军阀的高压下有所松动,这时,《国风日报》复刊,景梅九还职。阎采真告诉父亲,《国风日报》的“学汇”副刊需要一个校对,可以食宿在报社。父亲听了十分高兴,就像久旱逢甘雨。阎采真带父亲去报社求职,景梅九热情地接待了这个穷学生,了解情况后,同意让他担任校对。父亲见了景梅九两次,在父亲的印象中,景梅九对青年人很热情,果然如人们常说的,他确实“热心奖掖后进”,他的学问非常渊博,说一口晋南话却很难懂。父亲在报社任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便于接触文化界人士,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报社父亲认识了同乡山西盂县人高歌,由此也认识了他的哥哥高长虹。高长虹是文学社团狂飙社的创建者。狂飙社是五四运动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社团,狂飙社的前身是“平民艺术团”,1924年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党员高君宇的影响下,由高长虹发起在太原成立的,,最初的成员有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荫雨、高远征,他们要创办一个刊物,宗旨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和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斗争。刊物的名称,高长虹再三考虑,最后选定“狂飙”二字,来源于晋陆云《南征赋》:“狂飙起而妄骇,行云蔼而芊眠。”狂飙就是大风。1924年9月,为了推进狂飙运动,高长虹单枪匹马到北京,其中目的之一,是找景梅九,想依托《国风日报》办《狂飙周刊》,高长虹的父亲是景梅九的好朋友,景梅九对长虹也很器重。所以,到11月,《国风日报》复刊,《狂飙周刊》也就出版了,长虹把他的弟弟高歌从太原叫来负责编辑《狂飙周刊》。父亲在12月到报社,他和高歌年龄相仿,又都是刚从山西来,都爱好文学,很自然就成为好朋友。
高长虹到北京后,狂飙社的队伍迅速壮大,参加的主要有尚钺、向培良、高沐鸿、雷著羽、郑效洵等,父亲也参加了。他和郑效洵年龄最小,是狂飙社里的小弟弟。狂飙社的宗旨依然是要做向“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强者。
在狂飙社成员中,父亲与高长虹的情谊最深,互相以兄弟相称,并且常在一起散步谈心。父亲和高长虹的作品中对此都有记载。
父亲在《读了(长虹周刊)之后》写道:
在1925年1月16日,我同虹哥出西直门外。那时候,我们装上一盒红狮子菸,做野外的旅行。他走着,用脚把田间的土沙无意地一踢,笑的向我说:“假如我们有钱时,《长虹周刊》马上便出来了。”因为有钱便可出周刊。这是个事实,我这么想的。
高长虹在《步月》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想起去年夏天的一夜,同小弟弟坐在河沿的树上,谈论未来的军国大事,我做大将,小弟弟做副将。于是,大将要吃烟了,没有洋火。对面门里出来个小女孩,惊异地看着我们。我们开始说话了:向她讨火。她知道我们也是人,便答说“不敢”,跑回去了。我们在绝望中看见她第二次又跑出来,并且拿了火来,说是偷的。于是大将同副将感谢地笑了。
这样饶有趣味的回忆,生动地说明父亲与高长虹之间的情谊。
由于狂飙社成员都年轻、向往进步与光明,自然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支持。高长虹和鲁迅也有密切的交往。父亲对鲁迅很钦佩,希望能听到先生的教诲。于是,高长虹带他去拜会鲁迅,大概这是1925年初的事。从此,父亲常去鲁迅那里。
父亲和鲁迅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都有记载。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日记》(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25年2月8日:午后,长虹、春台、阎宗临来。
3月9日夜,阎宗临、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二本,赠以《苦征》各一本。
6月16日,长虹、已然来。
9月5日,已然、长虹来。
1926年3月1日,以一法国来信转寄长虹。
7月21日,得已然信,六月二十九日法国发。
8月17日,上午分寄盐谷节山、章锡箴、阎宗临书籍。
《鲁迅日记》中的已然是父亲的笔名,应写作“已燃”。事实上,父亲见鲁迅的次数要比日记里记载的多。父亲是一个很少谈自己的人,他既不宣扬自己的经历和成就,也不谈及自己和“名人”的交往。他从不主动展示自己的光辉,也不借助别人的光辉炫耀自己。这种低调、平实、自信的为人处世的风格,在家里、在社会都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对父亲和鲁迅交往的具体情况,我知道得并不多,他也很少和别的人谈起。父亲的这个特点,在他上世纪50年代初的学生任茂棠的回忆文章《怀念我的老师——阎宗临教授》中也写道:
他从来不宣扬自己,也讨厌别人说奉承他的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生们只耳闻他曾留学法国,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取得过瑞士的文学博士,更不知道他曾任过瑞士伏利堡大学的教授。他曾向学生讲述欧洲文化和中西交通史的知识和问题,但从不提他的研究成果如何如何。如果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不便多谈自己的学历和学问,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他与鲁迅有过密切接触的事是完全可以讲的,他却只是用鲁迅的话教育学生,从不向学生谈他自己和鲁迅的交往。
197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办了一个名为《山花》的铅印刊物,为纪念鲁迅逝世36周年,他们不知从何处听说父亲认识鲁迅,于是向父亲约稿,父亲写了一篇简短的《回忆鲁迅先生》,主要是写1925年初春他去看望鲁迅的情况。当时,鲁迅住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他写道:
我们被接到鲁迅的工作室。房间不大,却很整洁。靠近窗子是床铺,窗外是后院……他的桌子洁净而宽大,不摆书籍与稿件,只有些文具、时钟、烟盘。他经常吸的是普通的哈德门香烟。
鲁迅先生瘦而不高,平头,穿蓝布长褂,皮鞋,衣服很素净。眼光锐利,像常常在战斗。去看他的人,多是青年,很随便,自己找坐处,说话也不拘束。鲁迅常说笑话,自己却不笑。他对青年非常热忱。
父亲对鲁迅住所和相貌的细致观察,表明鲁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和鲁迅的谈话中,父亲问鲁迅,青年应该读什么书?问后,他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后来,鲁迅也曾公开讲过:“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能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脱离。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看来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父亲在这篇回忆文章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感言,表达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意:
我觉着:鲁迅伟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风雨吹荡他,云雾包围他。但是,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洗刷思想的污秽。
鲁迅这些要读外国书的教诲,对父亲出国勤工俭学是有触动的。父亲后来回忆说:他1925年冬辞别鲁迅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先生的影响”,因为“读洋书就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
父亲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太简略了,和鲁迅日记的记载相比就可以看得出来。据《鲁迅日记》,一直到父亲出国后,在一段时间内,还和鲁迅有通信联系。1926年3月1日,鲁迅收到父亲的信,还有给高长虹的信,请鲁迅转交。7月21日,鲁迅收到父亲从法国写的信,8月17日,鲁迅给父亲寄过书。父亲的回忆文章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只写了极简单的经过和主要的思想。我想,除了父亲一贯的不愿多谈自己的处世原则外,也许和后来鲁迅与高长虹的不和有一定关系。因为1926年10月,高长虹以及狂飙社就同鲁迅决裂了,相互攻击和论战,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鲁迅与高长虹论争事件,有关的论著不少,这里就不多说了。好在此时父亲远在欧洲,远离是非之地,并不了解事情详细的过程和是非曲直,在感情上,父亲应当是倾向高长虹一边的,在理智上,也应当不会影响父亲对鲁迅的尊重。
父亲在北京,除了去鲁迅那里,还认识了郁达夫。郁达夫对这个小弟弟,是很亲切的。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有一次说起郁达夫带他去饭馆吃饭,吃完饭,郁达夫脱下鞋来,从鞋底掏出一张钞票付账,并且告他:“钱是最脏的,所以放在鞋里。”
高长虹对父亲的影响是重要的,他把父亲引进了文学领域,使父亲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发展。1942年父亲的小说《大雾》的单行本在桂林出版。
继后在里昂做工三年,受了许多事实的教训,逐渐发现自己没有创作的能力。这并不是自馁,实因一个作家,需要有严肃的生活,渊博的学问,以及颖脱的资质,我既不能具备这些条件,遂决心抛弃了文学,研究历史,不觉已快十三年了。
父亲曾出版和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如:散文集《波动》、《夜烟》,中篇小说《大雾》,文艺理论《文艺杂感》等。后来,他从文学转而从事史学,他的史学论著写得十分灵动优美,一点也不枯燥,这和他早年的文学功底有关,实际上文史是不分家的。
父亲出国之后,1926年4月,高长虹和狂飙社成员移师上海,在上海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版了《狂飙丛书》。1928年4月成立了狂飙出版部,出版过6种丛书35本图书,编辑了5个刊物,出了36期。
高长虹在狂飙社解体后,1929年,东渡日本,大约是在1932年前后,他曾到瑞士寻求父亲帮他治病,父亲也在经济上援助过他。高长虹1937年回国后,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先到武汉,再到重庆,1942年到延安。1946年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区,大约在1954年因病逝世于东北沈阳。
(摘自《阎宗临传》,三晋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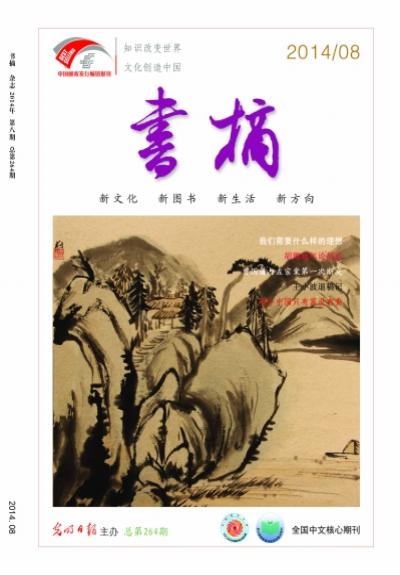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