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中国人称为文殊菩萨)的道场,远自唐代即为中国的佛教圣地。逾千年来,豪门贵族施功德的珍宝已遍布山中庙宇。因此,殿阁不断重修,涂金与油彩闪亮耀目,每年有二到三次香客云集。但在群山外缘,时髦照顾不到的地方,寒素的寺僧们负担不起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或能找到未经触动的遗构。于是,1937年6月,我自北平首途五台山。
从太原驱车约八十英里路到东冶,我们换乘骡车,取僻径进入五台。南台之外去豆村三英里许,我们进入了佛光寺的山门。这座宏伟巨刹建于山麓的高大台基上,门前大天井环立古松二十余株。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极古立辨。但是,它会早于迄今所知最古的建筑吗?
我们怀着兴奋与难耐的猜想,越过訇然开启的巨大山门,步入大殿。殿面阔七楹,昏暗的室内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巨大的佛坛上迎面端坐着巨大的佛陀、普贤和文殊,无数尊者、菩萨和金刚侍立两侧,如同魔幻的神像森林。佛坛最左端坐着一尊真人大小的女像,世俗服饰,在神像群间显得渺小而卑微。据寺僧说,这是邪恶的武后。尽管最近的“翻新”把整个神像群涂上了鲜亮的油彩,它们却无疑是晚唐的作品,一眼就可看出它们极类似敦煌石窟的塑像。
我们分析,如果面前这些塑像是幸存的唐代泥塑,则其头顶的建筑就只可能是唐代原构。显然,殿内任何东西在重建中都会毁于一旦。
次日,我们开始仔细调查整个建筑群。它们均明确无疑地显示出晚唐特征,但那还不是最奇特处。当我们爬进平暗(天花板)上的黑暗空间时,我大为惊讶地发现,屋顶梁架作法仅见于唐代壁画,此前我从未亲睹实物。与后世中国建筑方法相反,全然出乎我的意料。
平暗上的“阁楼”里,上千蝙蝠丛生于脊桁四周,如同厚敷其上的一层鱼子酱,竟至于无法看见上面可能标明的年代。蝙蝠身上寄生的臭虫数以百万计,于木料上大量孳生着。我们立足的平暗上面厚积微尘,也许历几个世纪方积淀至此,其上到处点缀着小小的蝙蝠尸体。我们的口鼻上蒙着厚面罩,几乎透不过气,在一片漆黑与恶臭之间,借手电光进行着测绘和拍摄。几个小时以后,当我们钻出檐下呼吸新鲜空气时,发现无数臭虫钻进了留置平暗上的睡袋及睡袋内的笔记本里。我们也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刻最感快慰。不出所料,队中同人均对身体的苦楚一笑了之。
大殿墙面原本定有壁画为饰,早已不存。至今唯一留存壁画之处是“拱眼壁”, 过梁上斗拱间抹灰的部分。拱眼壁的不同部分,彩画的工艺水准悬殊,年代也明显不同。其中一段画有佛像,后有背光花纹,纪年为公元1122年。旁边一段画有佛和胁侍菩萨,显然年代更早,艺术特点更佳。这一段与敦煌石窟壁画相似处最为惊人。它只会是唐代的。尽管只是一小片墙面,位于不起眼处,据我所知,它却是除敦煌壁画以外,中国本土现存唯一的唐代壁画。
在大殿工作的第三天。我的妻子注意到,在一根梁底有非常微弱的墨迹——它蒙尘很厚,模糊难辨。但是这个发现在我们中间就像电光一闪。我们最乐意在梁上或在旁边的碑石上读到建筑的确切年代。以风格为据判断一处古构的大致年代,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过程。虽手边有令人信服的材料且苦苦研究过,在证据不足时,我们还是不得不谦抑地将建筑的年代假设在二三十年之间,有时斟酌范围竟达半个世纪!此处,高山孤松之间即是伟大的唐代遗构,首次完璧现于世人面前,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特别认识。但是它的年代如何确定?伟大的唐朝自公元618年延续至907年,300年间各门类文化均得以强盛发展。在这300年中间,这座生动的古刹始建于哪一年,这个疑问难道过于好奇了吗?
现在,带有模糊笔迹的梁枋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迫切的答案。但是它们被后世的淡赭色涂层所蔽。我的妻子把头弯成最难受的姿势,急切地从下面各种角度审视着这些梁。费力地试了几次以后,她读出了一些不确切的人名,附带有唐代的冗长官衔。但是最重要的名字位于最右边一根梁上,只能读出一部分:“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她,一位女性,第一个发现这座最珍贵的中国古刹是由一位女性捐建的,这似乎太不可能是个巧合。当时她担心自己的想象力太活跃,读错了那些难辨的字。她离开大殿,到阶前重新查对立在那里的石经幢。她记得曾看见上面有一列带官衔的名字,与梁上写着的那些有点相仿。她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确切的名字。于一长串显贵的名字间,她大喜过望地清晰辨认出了同样的一句:“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
这个经幢的纪年为“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随即我们醒悟,寺僧说是“武后”的那个女人,世俗穿戴、谦卑地坐在坛梢的小塑像,正是功德主宁公遇本人!让功德主在佛像下坐于一隅,这种特殊的表现方法常见于敦煌的宗教绘画中。于此发现庙中的立体塑像取同一布置惯例,这喜悦非同小可。
经年搜求中,这是我们至今所遇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里,我们同时发现了唐代的绘画、唐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塑和唐代的建筑。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更属海内无双。我最重要的发现当是此处,恐怕将来未必能够更见任何同等古迹,更何况四艺合一之处。
离开佛光寺前,向长老道别时我的兴致颇高,应承明年重来时携政府基金以广为修葺。我们取道北麓通代县的路线离开山区;代县的规划十分精彩。我们在那里舒坦地工作了几天。
7月15日,一天劳作之余,我们见到了由太原运抵的成捆报纸,洪水冲溃大路将这些报纸耽搁了几天。我们放松地躺上行军床开始读报:“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已经爆发一个星期了。我们几经波折,设法绕路回到北平。
一个月后,北平沦陷。不久,中国营造学社和许多文化教育机构一样迁往华南。
我曾在华北调研过的多数地方现在都落入了日军手中。比如我最牵怀的唐代遗构所在的豆村,过去在外界并不知名,现在却再三见诸报端,或为日本人进攻五台的基地,或为中国人反攻的目标。我怀疑唐代遗构能否在战后幸免于难。万望我的照片和测绘不会是它目前所遗之唯一记录。
待战争结束,除了寻找更多新资料用于深入研究以外,当另有一项额外的任务,就是重访我们旧日的足迹,看看日军的炮火毁掉了多少无可替代的珍宝。
(摘自《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4月版,定价: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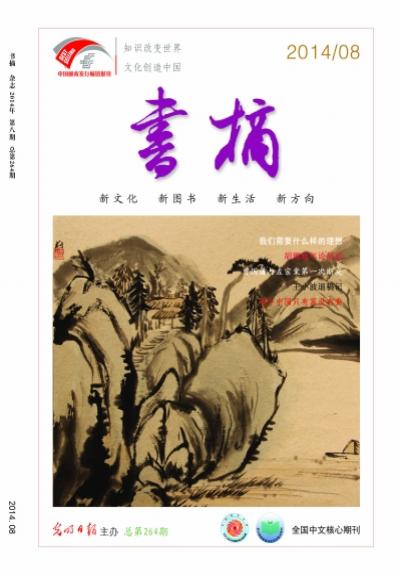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