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凝聚着爱娇的、带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你们看,巴先生的头发怎么白啦?真是不可想象啊!”
我们都跟着笑起来。我说:“你没看见我们都成了老头老太啦!”辛笛笑说:“陈蕴珍(萧珊)嘛,她是不会老的!”靳以穿着他那件由于发胖早已扣不上的黑大衣,指着神采飞扬的女主人笑着说:“瞧萧珊这身打扮,俨然贵妇人气派!”罗荪微笑着,习惯性地低咳着。对了,还有黄裳沉默地靠在椅子上,两手插在裤袋里,炯炯有神的眼光扫着在座的这个那个。巴金用他改不了的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腔了,他哈哈笑着:“陈蕴珍总像个小孩子,真是的!真是的!”
我发现我躺在黑暗中,一片沉滞的黑暗!生者与死者的影子一起掠到我面前又一个个地消逝,微笑的面容,怅惘的眼光,甚至是泪光莹莹……我伸出手来,多想拉住你,我说:“蕴珍,你别走,干嘛那样匆忙?”你却无声地飘然逸去。我的眼睛突然涨满了泪水,这又是个梦!我是个爱做梦的人,但从前很少梦见过已死去的人,除了个别的。但这二十年里,我的朋友们——生者与死者,都在夜间向我走近。
1973年5月,我编造了一个借口,请假到上海去看巴金先生。瑞珏和小林到车站接我,我们在车站附近一家拥挤的小饭店里随便吃了碗汤面,互相交谈了那些年大家的情况,然后我们坐公共汽车到高安路下车,三人默默地走到我原先那样熟悉的大门前,九姐出来迎接我,九姐说巴金先生亲自到菜场找老母鸡去了,为了接待我这个多年不见的“远客”。
巴金先生已是满头白发了,那时他还不到七十岁!我们似乎都在强忍着几次想溢出的泪水,却专门谈些在农场或干校劳动时如何苦中作乐的话题。他时不时地摘下眼镜,擦着眼角溢出的水滴,说是眼睛不好,牙齿也不行了,却又不停地反复说:“我还好!我还好!”
晚上,我睡在九姐同瑞珏的房间里,夜深人静,瑞珏详尽地讲述了这几年你们家的遭遇,她谈到你的病怎样被发现、耽误,和你做手术前后的情景。九姐打开靠墙的箱子,取出一叠照片……
你躺着,紧闭着你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我多想叫你一声:“你为什么不睁开眼,你的老朋友又到你家做客了!”而你却直直地躺着,像电影《哈姆雷特》中淹死的奥菲利娅,你的黑黑的头发全部梳向头顶,拢在一起,铺平在停尸床的上端,仿佛也是水淋淋的。你的表情却是陷在恬静的睡眠之中,全然不顾那站在你身旁,穿着不平整的白衬衫的,你那满面哀戚的“巴先生”!
九姐告诉我,由于你已经被耽误了,做了切腹手术后,发现癌早已扩散,人是更禁不起了,最后也只能带着没有愈合的伤口,包包扎扎,穿着与原来的体形不适合的肥大的一套服装入殓。
这天夜里我不能安眠,我在想着你在最后的六年中所受的折磨和侮辱。你扫街,站在你的“巴先生”身边“陪斗”,你默默地看着那些歪曲事实、文字拙劣的大字报,用身子挡住巴金先生,自己的脸上却被带铜头的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我可怜的朋友,难道我们年轻时向往的生活竟是这样冷酷无情么?好像有一只手在我眼前一张张地翻着你的照片。
第一张是你穿着工装裤俯身在草地上,这是在上海一个有名的公园里。你支起胳膊,一副全然顽皮的样子,可能那时你还在上海爱国女中,在社联的领导下投身于中学生的抗日运动。这张照片究竟在哪年照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这是你的得意之照,因为在你身后远远的草地上,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在那里假寐,他的脸上用他的呢帽遮着阳光,这就是你的巴先生。
第二张——我们穿着长长的夹袍,外面都加了一件短短的毛线马甲。你穿了我的,我穿了你的,只是为了跟袍子的颜色调和,也为了“好玩”。这大概是1939年的秋天,一个下午,到处繁花似锦,我们已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了。
第三张进入了40年代,你穿着矮领子的花布旗袍,梳两根短辫,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清澈纯真,还有你那常被我们赞美的酒窝嵌在散发着青春光彩的面庞上,这是你最喜欢的半身照。那是你的黄金时代。学业、友谊、爱情都在丰收。同学好友们叫你“小三子”,因为上面还有树藏和另一个外号叫“毛儿妈”的女同学。这也就是你后来先用“萧姗子”,后来干脆用“萧珊”为笔名的来历。
抗战后,过了一段不算短的岁月,你终于带着你的小婴儿回上海了,而且孩子的爸爸就是你最崇拜的“巴先生”,你仍然习惯这样叫他,有时也叫他李先生,当着人,你从来没有直呼其名,而他也总是叫你“陈蕴珍”。你们这个家一直是靠巴金先生的稿费为生,你们不想发“国难财”,也不可能加入“劫收大员”的世界,你们的财富只有书,发黄的土纸制成的书!巴金每天开夜车写作,这原是他十年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喜欢在文章中写道:“日也写,夜也写……”如今生活上是热闹起来了,在上海的朋友们常来闲谈,喜欢议论国家大事,嬉笑怒骂之余就逗弄孩子,帮忙搞这样那样。你喜欢这样苦中作乐的生活。第四张可能是在小林三岁生日那天,你们在照相馆拍了家庭照。我收到的是你们母女二人的半身照。你的眼睛眯缝着,却闪着顽皮而又强忍的笑意。看样子,你这个年轻的母亲是满足的。
第五张。现在是50年代了,1956年夏,我们都已是三十几岁的人。我正在准备去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教现代中国文学。我带着三个孩子到你家玩了几次。我们也曾在前面的庭院里照过相;我们俩带着我三个孩子,巴金先生微笑地站在旁边。这时你们已经搬到武康路了,你们喜欢这个幽静的住宅,特别是因为楼下大厅外的凉台下面有一大片草坪。我们坐在凉台的藤椅上,你指着草坪对我说:“我想在那头竖一个架子,装一个白色的长吊椅,配上垫子,再放几只漂亮的靠垫。”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我想起一个美国电影。你出神地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巴先生可以坐在吊椅上看书,摇呀,摇呀……”我大笑,我说:“跟电影一样!不过我可从不喜欢打秋千,我觉得晕!”那时我觉得我们都喜欢用自己的生活趣味装饰自己的家,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自然是“资产阶级”的。
到了60年代,三年灾害之后,你曾寄给我一张穿着黑色旗袍的小照片,是在家里庭院中照的。可能是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你斜站着,抱着双臂,在凝视着什么,还是在想着什么。这时你也有四十岁了,正是中年的边缘上,显得深沉、含蓄、成熟,似乎已经很懂得人生了。
巴金的作品鼓舞了你而写信给你心目中的“英雄”,后来你们一起像朋友一样地在大后方——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度过了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各种各样的旅行滋味。当然你们说这不过是强迫游山逛水……
在昆明一个饭馆里,在一个只有五个人的小宴中我才懂得你们等于订了婚;在贵阳花溪的清苦的“蜜月”;在重庆第一次以“巴太太”的姿态出现在老朋友面前;在成都的待产……你好奇又不安。然后你回到上海,在房子里系着围裙,忙吃忙穿,抱着孩子参加朋友们的高谈阔论,也在哇啦哇啦地嚷着:“天快亮啦!”
是的,天快亮了!萧珊,小三子!你是爱国女中的学生,你懂得热爱我们的祖国!你甘愿抛弃在上海的舒适生活,却到内地去过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艰苦日子,那时你才不过是19岁!你穿着巴先生给你买的黑皮革短大衣,目光四射地、充满好奇地接受生活给你带来的种种考验。
毕竟你是天真的,虽然也从天真走向成熟,这过程是漫长的。我还记得你在结婚之后我们一共有过三次的长夜谈。
最后一次长夜谈,已进入60年代。1960年春节期间,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我在前一年由于所写的两篇儿童文学出了问题,当时批判会议的记录全发表在《雨花》杂志上。我的心情不好,来了还是住在你家。这天夜晚你在二楼大书房里备了一盆烧得旺旺的炭火,我们三人谈到半夜。的确当时我们都不大明白,然而那天夜里你们的安慰和勉励却使我支撑下来,很快地又恢复了自信与乐观。
萧珊,你坐在黑暗中想些什么?你有没有回忆过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昆明大西门外的那一次大胆的夜行?——
你、树藏和我三个人在沈从文先生的家里度过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时间大概是1939年年底,那时我们联大的女生宿舍还在城外农校的一个小楼里。这天可能是除夕,我们在昏黄的煤油灯和红烛的光影摇曳下聊个没完,听着沈先生浓重的湖南口音的笑谈,谈林徽因,谈诗和散文,谈我们这些少女应该怎样珍惜这读书的好时光……我们吃了又谈,谈了又吃,完全忘记我们该赶夜路了,忽然发现已是午夜,这才恋恋不舍地站起来。三姐怎么也不让我们走,怕路上遇见“强盗”。我们却嘻嘻哈哈地满不在乎,我们说:“我们是三个人哩!三个人足可以打一个坏人!”沈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啊哈,三个勇敢的少女!”树藏摇了摇手中的甘蔗:“瞧,我们有这个!”沈先生大笑,三姐不停地说:“不行!不行!”最后他们还是只好端起油灯,送我们走出大门。分手时,三姐还在说:“随便住一夜吧,我们实在不放心哩!”但我们这三个无所畏惧的少女就这样每人挥着一根两三尺长的甘蔗,嘻嘻哈哈地快步向城门走去。
那天夜里,你有点胆怯,紧紧地挽着我,好像我们都在心跳个不停,只有树藏大大咧咧,确实不大在乎。走了一会,她建议我们开始吃甘蔗,于是路上添了我们的撕啃甘蔗皮的声音。我们嚼着吐着,树藏不停地发出“呸!呸!”的声音,我们大笑。你忽然说:“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树藏一边啃着甘蔗,一边满不在乎地说:“打!用甘蔗打!”我们当时想象的坏人无非是美国电影中的蒙面大盗的形象!后来我们终于看见远远的女生宿舍的微弱灯光了,显然大家都松弛了,忽然高声唱起抗日歌曲,忘了疲乏,步子也更快了,当然在我们临近宿舍的大门时,甘蔗也只剩下最后一口!
这是我们三个人唯一的一次在一起的夜行,没有多久,我们各自走进不同的命运,三十多年后你躺在殡仪馆的停尸床上,紧闭着双眼,而树藏成“活着的死人”,睁大着充满愤慨与疑问的眼睛,不认识任何老朋友了,直到1981年2月才永远阖上了双眼,那准备用甘蔗打坏人的天真少女却早已是一场十分十分遥远的梦境了!
你是个好主妇,虽然你不喜欢用“贤惠”这个词汇来形容你,其实我亲眼看见你一心一意地想把你们的家布置得十分舒适而并不追求华丽。50年代你为巴金定制大大的方枕头,你说:“巴先生喜欢大枕头,他可以靠在床上看书,这就舒服多了。”朋友们常常当面笑你娇滴滴的声音和孩子脾气,可是他们都知道你是多么会照顾你的巴先生,而且你总是很听话的。你总怕你落后了,于是坚持了俄语学习,这我一直是佩服你的,因为我怎么也学不下去。你翻译了普希金与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你的译笔是那样地清丽流畅,朋友们常说读你的译作是一种享受,可是你为了“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却心甘情愿地当了无名的编辑,兴致勃勃地到处组稿,看稿也看到夜深,然后又争取下去体验生活,那些年你从未想到该拿几级工资,只想到自己该多做一些对读者有用的事!你怎么可能想到有一天竟会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给你加上巴金打入作协的“坐探”这样恶毒的头衔呢!
你所有的老朋友都在怀念你!每一次在北京或上海我们相聚的时候,总不可避免地谈起你。沈先生和三姐总是惋惜地叹着:“这样一个活泼的人,怎么会走得比我们都早!”在上海我们这些老朋友若是晚间在你们家同聚,就总觉得你当然还是跟我们在一起,坐在我们旁边,睁着你美丽的大眼睛望望这个,望望那个。你不会走开的,小三子!在上海你的家里,在巴先生的面前,我们尽量不提到你,我却仿佛看到你静静地坐在一只空着的沙发上,跟我们一起聊天,吃晚饭,夸奖着九姐炒的“鱼香肉丝”,跟辛笛兄没完没了地开着玩笑,然后看电视,不停地发议论,等我们走后,你陪着你的巴先生,替他拿起手杖,慢慢地扶他上楼,回到你们的卧房……你还在武康路你自己的家里,在楼上陪伴你的“巴先生”,书桌上你在50岁的照片上深情地凝视着他埋头写他的《随想录》,虽然你的笑容却是我从未见过的极其凄凉的笑容!
(摘自《青青者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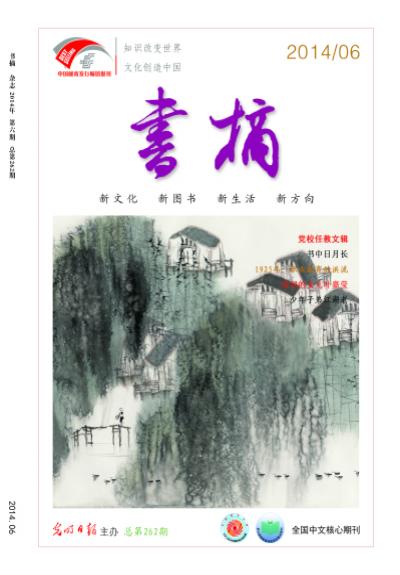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