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乡,都得听父母絮叨:亲戚或街坊,谁死了,谁重病缠身,命不久矣。我常常一脸漠然,心想这与我何干呢。然而事后,尤其是无端想起这些已经冷却与即将冷却的名字,心中总不由一惊。原来他们与这个红尘颠倒的世界的联系,只剩下我们的回忆;原来他们的生命,还不及一个残存的意象那样生动。将一些人和事记录下来,我不奢求借此而流芳,我只想证明,他们曾走过这片土地,走过春天的繁花秋天的冷月……
憨夫子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憨夫子微闭双目,手舞足蹈。他的吟咏时而高亢,时而沉郁。我从梦中惊醒。
憨夫子姓何。不过街坊似乎都忘了他的尊姓。自打我记事,所见诸人,不是称他“憨老师”或“憨夫子”,便直接呼他“老憨”。父亲说,老憨生具异相,双眼白多黑少,五岁才会叫爸妈,人家孩子流口水,那是看见了鱼肉,他流口水,那是看见了书,因此他从小就被街坊称作“老憨”,叫了这么多年,谁还记得他姓什么呢。
憨夫子的事迹,滋养了我们贫乏的童年,熟识他的人,都能说道一二。而且这些事迹,都与他的憨有关。譬如他一边烧锅,一边看书,不仅把饭烧煳了,还将自己的布鞋当柴火塞进了熊熊火中;他给女儿喂红薯稀饭,喂到一半,诗兴大发,便去挥毫泼墨,待诗写好了,回头一看,那半碗红薯,却落入了邻家的狗嘴里,自此女儿再也不让他喂饭。
这些都是寻常事——其实认真说起来,憨夫子绝非什么异人。他的生平,清白如吾乡的手磨豆腐:贫家出身,师范毕业,中学教书,娶妻生女,与世浮沉。他所异于常人之处,一是爱书成痴,二是爱诗成魔。不想这吟风弄月的嗜好,最终殃及他的教师生涯。他教了十五年高中,因爱在课上谈诗词曲赋,为家长所检举,称其不务正业,耽误了学生高考,缘此罪名,被学校从高中部贬到初中部。然而他不知改悔,仍旧给一脸懵懂的初中生讲格律,谈平仄,校长闻后大怒,遂禁止他登台授课,发配到阅览室看门。这在吾县的教育界,同样是一桩谈资。
父亲与憨夫子自小相识,曾有意请他为我发蒙,为奶奶所阻止,说怕传染了他的憨。后来父亲拿我的作文请他指正,他大喜,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我读高中,恰巧是他在高中部的最后时光。他实在不太擅长讲课:一口乡谈,笨拙至极;自说自话,丝毫不顾学生的感受。他最得意讲古诗文,讲廉颇蔺相如,便抱上一摞《史记》;讲杜甫诗歌,便高举《杜诗镜铨》……他在台上顾盼神飞,台下一片窃窃私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他的叹息穿越了那仓皇的三年。
上大学之前,我去他家辞行。时值炎夏,他正伏案读书,奔腾的热浪使他破落的书房愈发逼仄。他老了,瘦骨嶙峋,脖子漫长——后来我读余光中写一个人的瘦,“瘦得像耶稣的胡须”,眼前便浮现黑而瘦的他。他见我来了,十分高兴,二人坐定,却相对无言。
张麻子
青林渡的鱼行老大是个外乡人叫张麻子,大概在1995年前后,搬到南巷,租房恰在我家对面。他有两儿一女,其女彼时虽年幼,却是美人坯子,一双丹凤眼,顾盼神飞,一笑百媚。街坊偶尔取笑他:“张麻子,这丫头是你亲生的么,你这模样,只能生出老母猪。”他从不生气,反而纵声长笑,得意非凡,说他这老闺女,若生在古代,起码可以当贵妃!
其实张麻子五官端正,并不丑陋,只是肤色太黑了,用彼时我们最爱听的单田芳老师的话讲,“面如锅底,黑中透亮”,那两只牛眼瞪起来,直如丧门神。令人好奇的是,他这么黑,怎么会有麻子呢。张麻子酒喝多了,便给我们解感,说他脸上的麻子,不是黑麻子,而是白麻子,算命先生刘瞎子说过,这是富贵之相。我们乐不可支,遂大胆走近他的酒桌,去数他脸上到底有多少白麻子。
除了白麻子,张麻子身上还有一大特色,其左手小指,仅余半截。原来他早年嗜赌,不仅负债累累,还面临家破之虞。在拖儿带女准备回娘家的妻子面前,他立誓戒赌,为表决心,用菜刀斩下了半截手指。他对我们说,现在一见麻将牌九,早已结疤的小指还会隐隐作痛。
我从未见过张麻子下水捕鱼,然而他在鱼行,却是摊位最好、生意最火的鱼贩子。他买鱼卖鱼,从不缺斤短两,处事公道之外,更兼为人热忱。
然而张麻子虽有富贵之相,却无富贵之命。鱼行二十年来太平无事,他只当了半年,便碰上城管部门整顿市容,鱼行首当其冲。协议不成,竟而大打出手,这在一向尚武的吾县,当时只道是寻常。张麻子用秤杆戳伤了一位执法人员的眼睛,再加上他是领头羊,遂因扰乱公共秩序,拘留十天。
十天后,张麻子走出拘留所,迎面扑来了三大噩耗:曾经繁华的鱼行被夷为平地;他打伤的那位城管,病情恶化,转到上海手术,需要他支付巨额费用;生具贵妃相的女儿,因家中忙乱,无人看顾,在十字街口被车轧死,肇事车辆逃逸无踪。
一夜之间,正值壮年的张麻子头发白了大半,覆于黑脸之上,无比残酷。
他像一条被搁浅的鱼,却来不及悲伤,强打精神,一家一家登门借钱,以筹医药费。从我家借了一千,父亲深知他为人,未打欠条。
不久,张麻子一家忽然消失,据说是深夜迁徙,谁也不知去向。借钱给他的债主纷纷怒骂,就连一向老实的父亲,都痛恨自己看错了人。
2001年,临近除夕的一天,父亲早起开门,看见张麻子的长子站在漫天冰雪之中,一身风尘,赶忙请他进屋,他不肯,拿出一千元,说替他父亲还债;一条烟,孝敬我奶奶,权作利息。一问才知,原来他一家夜奔,都去了上海打工,张麻子夫妇捡垃圾,两个儿子在工厂搬运,前不久,张麻子重蹈爱女的命运,遭遇车祸,死前叮嘱儿子,务必将债务偿清,否则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当天,南巷的街坊都拿回了欠款,那是张麻子的卖命钱。
童亮
火车和酒,像两颗温柔的钉子,楔入了我与童亮的友情。
绿皮火车的行旅,是我今生最不愿触及的记忆。王晓渔兄说“火车是文学的敌人”,诚哉斯言。大学四年,我乘火车,奔驰逾万里,亲历与见闻种种,彻底击碎了我对苦难的抒情。有一回从汉口到重庆,我只买到站票,竟一路站了将近20小时,其间,我屡屡生出一种想法,不把自己当人,而视作货物,随地一扔了事,然而我终究没有勇气,放弃人之为人的脆弱尊严。
大一寒假返乡,我的火车噩梦才刚刚开始。那一节车厢,近一半是西政的同学,上车伊始,众人吆五喝六,谈笑风生;列车开到安康,闷罐一般的车厢渐渐陷入沉寂,我收起手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伸了个懒腰,发现斜对面有一双眼睛,在灯火明灭之间,粲粲若星,仿佛在坚持什么。他见我起身,冲我一笑,寒光一闪,他的牙齿整齐而雪白。
我记得他叫童亮,此前见过一次。这厮油头粉面,唇红齿白,皖北人大多质朴而沉毅,童亮置身其中,相当异类,像一个常年流连于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并不为我们这些乡土的草根所喜。
此刻我们是无法入眠的难友,便顾不了旧时的成见。我招呼他走到车厢的尽头,装模作样点了两根烟(其实我俩都不会抽烟),漫谈开来,冬夜在窗外飞驰,偶有冷气渗入,令人头脑凛冽。这一谈才知,我们的成长、读书历程竟如此近似,遂越说越投机,有时相视而笑,奠逆于心,顿生知己之慨。
后来才听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我与童亮自此订交。我们都认为,对方可以生死相托。
此后便是喝酒。青春有多长,酒就有多芬芳,我们的醉意就有多激扬。有一回我俩喝醉了,我送他回寝(12舍),他执意回送,二人相搀,一路摇晃,走到我的寝室(2舍),然后我再送他,他再送我……第二天,室友说,昨晚你至少回来了五次。我摸了摸疼痛欲裂的脑袋,忽然想起,说好我请客,却是他买单。
大三那年,我和姚一斗寄居于歌乐山中的一间地下室,黄卷青灯,闭门读书。每个月,童亮都会提诗仙太白上山。一斗不爱喝酒,我和童亮便将酒菜打包,行至山间,席地而坐,一觞一咏,飘飘然若在世外。
酒酣之际,童亮讲述他的家世。其父是一家中学的副校长,平生谨小慎微,奉公守法,有一年忽被举报贪污,有司调查,虽还他清白,其间却大吃苦头,而且从此断绝了转正的前程,他终究意难平,遂令儿子学法律,主正义。童亮的兴趣,本在所史和考古,格于父命,只得违逆志向。大学这些年,他埋头苦学,却沦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律虚无主义者。他认为,这样的体制,个体并不能改变什么,与其投入,不如疏离。
歌乐山上,他与我相约:毕业之后,决不入公门,不向体制妥协。我们背负诺言,从此天各一方。我一直混迹于媒体,他则浪迹天涯,在深圳当编辑,在苏州做法务,后来回到安徽,竟干起了白酒销售代理。有一年我途经合肥,他从舒城赶来,高举一瓶散装白酒,说兄弟这次让你尝个鲜。那晚我只喝了三两,胸腔便如火烧,醺醺之中爬上火车,一觉睡到杭州。翌日收到他的短信,原来这玩意叫酒母,最是凶猛不过。
2008年的一天深夜,他来电,说正坐在长江厂边上,想起老朋友、老同学,想起当年与我一道纵酒狂歌,意气慷慨,“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那是他此生最快意的时光。他语音低沉,唉声叹气,我顿觉不妙,遂拿酒母一事激他,说上次不够尽兴,年底我回老家, 一醉方休。
再见他,是我奶奶的丧礼,他来吊孝。晚上喝酒,相顾却是一脸凄然。我不知他伤心什么,直到他起身,连敬我三杯,一脸愧意:他拗不过家人的意愿,只能回乡,参加公务员考试,前不久考入了司法局。他说自己背叛了青春的誓言,他说那晚在长江码头,万念俱灰,决意自杀,他说……
他的眼泪落入酒盅,渐渐弥散,消逝,不复可见,就像我们一同飞扬与蹉跎的青春。
(摘自《少年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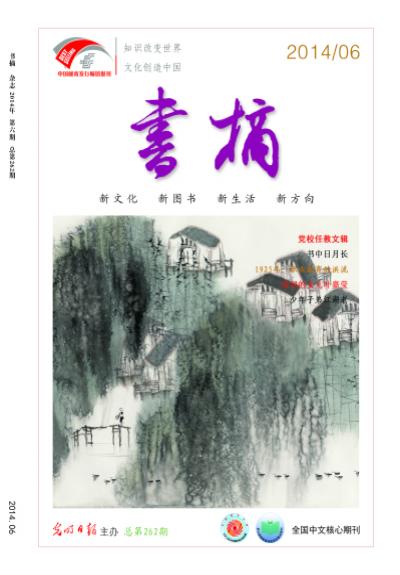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