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货币化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
中国人以前有亲情、家庭、血缘的关系,但是现在没有了。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中国成为了很大的消费市场,大家很愿意坐在一起谈买车、买房子,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CBD上班的很多女孩子,可以为了买一个名牌包吃几个月的方便面?我个人觉得对物质需求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标志作用,名牌包也好,车子、房子也好,这些都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一种身份认同,是一个巨大的身份认同的危机。过去60年,中国分成相对鲜明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一个人的身份是通过阶级的符号,通过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赋予的东西决定的。那个阶段你所有的身份是非常稳固的,而且那种稳固是非常残酷地强加给你的。1978年在有新的交易产生后,人们可以用金钱获得新的身份标志,获取阶级的成分,家庭的出身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用金钱作为社会新的润滑剂,在初期有巨大的解放作用,比如,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住酒店不需要再开介绍信了。用金钱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这种自由感至少持续了二三十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过去所有看起来坚固的政治约束都已经丧失了。但同时,金钱带来了新的问题。现在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经济舞台上,身份不鲜明了,一个人的教育、出身等都不重要,唯一可以证明自身价值的是银行卡里有多少钱。
社会的货币化看起来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但不能忽视的是,所有自由分为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货币化当然会获得外在自由,但内在自由属于另一个范畴。很多情况下在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整个社会内在自由的消失,这与金钱是没有关系的。当前所有人从身份上看起来都有极大的自由,但同时这个极大的自由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独特性消失了。独特性没有了,人只能通过积累更多的100块钱来证明自己的独特性。
中国迫切需要思维观念的变革
中国体制特性非常奇怪,我们的集权主义是恒定运动的结构,比如小说《芙蓉镇》中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搞不搞新的运动了”,它是不断运动的东西,不断运动意味着所有东西是不坚固的,不管是金钱还是权力。所有人在高速流动环境下成长,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不确定的。所有财富和权力都不能维持太多代,很快被洗刷,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在一种不稳定的系统里。当所有人都在不稳定的系统里,这个社会会变成永远临时性的社会。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房产是不是能坚持70年,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三年之后的事情做打算。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卡夫卡写的《洞穴》,一只小老鼠在找到一点粮食后非常焦虑,它不知道这些粮食该放在哪里。它不断把粮食从这个坑转向另一个坑,它一生为粮食的安全寻找一个去处。我认为这种深刻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感是构成中国人精神世界最主要的东西,这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永远不会有余钱存在。
我同样认为传统家庭是功利性的家庭,在中国,这是非常漫长的家庭传统,像对小孩子讲“你要有出息”,这个“息”是利息。这个漫长的功利传统(包括家族的传统)是应对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的保护伞。中国人始终是某种工具性的产品,过去是家族的工具。这个东西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变得非常严重,造成整个中国社会内在的塌陷,一个巨大的塌陷。这个塌陷是经过狂热革命运动,再加上金钱的侵蚀,它们共同带来了整个中国人精神状态内在价值的巨大缺陷。这个新的塌陷使整个社会所有其他逻辑都不再起作用,只有金钱和权力的逻辑在起作用。
这种功利的逻辑导致了金钱至上的恶果。过去十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这么喜欢谈钱,而且是这么大规模地喜欢谈钱,金钱无孔不入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血管里。我在小区里散步,遇到一对六七十岁的老夫妇,他们会非常轻松地谈论“这个房子才五百万元,那个房子才六百万元”。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自觉地把金钱作为生活中衡量的工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过去十年里,大家根本不谈其他的逻辑关系。
从根本上来讲,这也同时意味着人彻底沦为工具了,前十年是政治的工具,现在是政治加金钱的工具。80后的小孩,90后的小孩,他们有比我们70后小孩更大的被物质所困扰的压力,他们已经饿不着了,但是那种本身对物质的焦虑压倒了一切。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解决,金融系统的建构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这样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整个思维观念上的变革,这才是最迫切的问题。
社会不应该是二元的。在金融体制上,批评社会货币化并不代表要进入非货币时代。我们的社会应该有多种语言存在,货币是一种交易的语言,一种经济的语言。经济的、交易的语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存在着对这类语言过于担心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权力的语言和金钱的语言里面蕴含着巨大的交易性。这使我们生活得特别不高兴,或者大家觉得不容易,因为交易形态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我们在里面只听到物质的语言、权力的语言,我们听不到道德的语言,也听不到美的语言,更听不到文化的语言。我始终认为,正是因为这些语言的缺失、这些纬度的缺失才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钱渗透量比集权更强大。经过集权之后的金钱会是巨大的腐蚀剂,这个腐蚀剂会进入毛细血管。
我最近在重新读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的文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捷克跟我们中国20世纪80年代一样,中间出现了断层。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政府用物质收买整个捷克社会,人们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买小车,去度假,政府靠这些收买整个捷克社会。捷克人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热情,人和人互助的热情,变成70年代每个人的冷冰冰,知识分子要不然流亡,要不然也是很卑微的角色。这种情况下,社会有消费的狂热,但是思想上又是非常巨大的寂静,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和有良知的人会怎么做?人和人如何联合起来面对这个冷漠的东西,在后集权的社会里,政治和权力无孔不入地进入到我们社会里,我们妥协,我们下意识地回应了谎言,从而完成体制运转的过程。正是因为这种合谋,造成这个社会继续运转。我们整个时代,包括我们谈论政治、谈论各种问题。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搭便车的心态。我拒绝付出代价,只能等到潮流发生改变,我才加入其中。这种搭便车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只能在这个烂泥潭上继续打转。那一刻成为律师、成为一个商人或是成为在课堂上讲实话的老师,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反抗过程。
直面生活的痛苦,真心地理解世界
现在很多人喜欢讨论幸福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新型文化的象征,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很盛行。当时的美国人喜欢练瑜伽,去印度寻访,谈个人内心的解放,彼此谈论是否感到幸福。当时整个美国环境受挫,20世纪60年代高亢的理想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巨大的挫伤,美国人在越南失败,苏联开始多元扩张,日本开始崛起,美国人对外丧失了自信心,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内心。因为大部分人很难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揭自己的伤疤是很痛苦的,他们会拿很多小花样掩盖自己的痛苦。
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的技术,包括微博和互联网提供了非常自恋的手段,人们会关注自己现在是不是增加了1000个粉丝,这一条微博有多少人转了,这背后是整个精神被掏空的标志。
人什么时候最幸福?我认为人失去自我的时候最幸福。为什么革命让人欣喜若狂?那是因为在人群中感受不到自我,那一刻没有自我,人觉得是最幸福的。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人可以选择做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追问自己心中黑暗和光明并存的地方,可以揭露自己的伤疤,这是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我觉得这个过程会让人重新认识自我。现在的人可能非常倦怠,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才会不断地追问关于幸福的问题,而如果放弃自恋文化的特征,真心地理解世界,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人不需要刻意地寻找痛苦,而应该不回避生活的痛苦,我们现在的时代是鼓励所有人回避生活的痛苦。这是一个不断按下快捷键的时代,是涂一层糖纸的时代,小心翼翼地问道:你看我幸福吗?坐在咖啡馆里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无法直面生活的象征。
投资知识将给社会带来持久的变化
我完全不懂投资,但是我有两件事很想做:第一,我跟朋友们开了一家很小的书店,我特别希望能在中国很多城市,不管大城市还是中型城市都有那么一家书店,可以提供自由的阅读空间和讨论空间;第二,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基金用来鼓励全世界的年轻人写书、拍纪录片和拍照片等,以不同的形式发现世界。这几年我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差异,包括对自己的认知差异,以及中国现实对世界的影响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感。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在影响世界不同的地区,我们对这些影响后果(包括对中国在世界中真正的位置,以及别人对中国的感观,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是什么)一无所知,中国像一个盲眼巨人和感觉迟钝的巨人。过去中国人老说西方人像公牛闯进瓷器店,现在中国就是这头公牛,我们无意中毁坏了很多东西,自己茫然不知,这种无知会带来最大的伤害。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去世界各个地方看看,看毛里求斯发生了什么事情,看非洲人是怎样生活的。只有巨大的知识工程,才能给社会带来持久的变化。
(摘自《阅读的版图》,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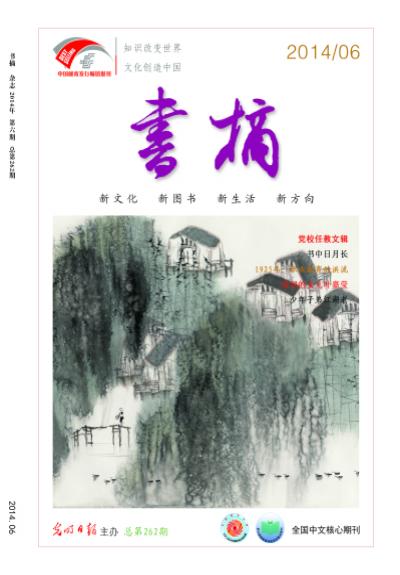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