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出生后,我就开始改口叫他“爷爷”。他跟我当了四十四年的父子,前二十六年我叫他老爸,后十八年我都叫他爷爷,因为爷爷是他最爱听到的一种称呼。
我虽然算早婚生子,但德儿出生时,爷爷已经六十二岁,他们当了十八年的爷孙。隔代的爷孙情,比我跟他或我跟德儿的父子情,更亲也更浓。
我从小一直以为我父母只生了六个小孩,好多年后才听我母亲说,我还有个应该排行老二的哥哥。他出生在抗战结束后,但因为罹患肺炎而早夭。我那个早夭哥哥的离开,好像也带走了我父亲的部分生命。他虽然还有六个子女,但他的父亲角色却始终很淡也很远,他跟我们兄弟姐妹中间好像总隔着一层难以言说的什么东西。一直要到德儿来到世间,才又唤起了他早已遗忘了三十多年的角色记忆,他是以爷爷的身份在扮演父亲的角色,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更清楚了:“你们六个小的时候,你爸从来没替你们把屎把尿过,但他对孙子却什么事都做,比他对自己的孩子还更像个父亲。”
德儿在小学毕业前的十二年,他们爷孙俩几乎是须臾不离、亦步亦趋。社区里,爷爷每天推着婴儿车散步,小校门前,爷爷每天等孙子放学后,牵着他的手穿过大街小巷一路玩回家,沿途熟识的店家看到他们都会打招呼:“老爷爷又接孙子放学啊!”听到这样的招呼,木讷的爷爷也会笑着叫应:“是啊,是啊。”
爷爷不但是他孙子的保姆,也是他的保护神。任何人只要对他孙子大小声,轻者被爷爷怒目以瞪,重者必遭爷爷厉声叱骂,连我有时候想要履行一下当父亲的权责,也常因他护孙心切而弃权投降。
有一年德儿在学校玩爬单杠,不小心跌下来摔破下巴,爷爷把血流不止的孙子送到医院后,立刻打电话回南部给我母亲,“你爸在电话上哭得不像话,一直怪自己没把孙子照顾好”,我老妈每次描述这通电话时,都不忘加个批判性的脚注:“来台湾几十年,我没看你爸哭过,你哥小时候调皮捣蛋常常受伤,但也没看他伤心成那个样子。只有在你另外那个哥哥走的那天,我看你爸哭过。”
德儿出生的那天,我从医院打电话给父亲:“老爸,你当爷爷了!”一个月后,他只带了一个行军袋,里面塞了一床棉被和几件衣服,搭火车到台中住进我租的一个透天厝里,开始扮演他一生最快乐的一个角色:爷爷。但他这个角色只扮演了十八年,太短了。
最后的夏天
有朋友推荐我去看张作骥拍的《爸……你好吗?》,我摇摇头苦笑:“大概不会去看吧。”“为什么?”“不敢看。”
真的是不敢看。因为怕在戏院里丢人现眼,又重演看《海角七号》时,电影尚未散场就趁黑落荒而逃那样的惨剧。
一把年纪后这几年,全身器官老化的速度虽与年龄成正比,唯独泪腺却像永远的尹雪艳,岁月不曾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而且愈老愈发达,稍不留神它就会自动运转,连阅尽世事的大脑都来不及管控。
新竹创下高温那天晚上,我在闷热得像蒸笼的房里读陈寅恪的诗,“暮年一晤非容易,成作生离死别看”,越读越燥越闷,闷到受不了终于弃书开电视想换个情绪,哪知道开机就是公视播的《山上的理发师》,还没看几分钟,剧情还没搞清楚,泪腺就开始蠢蠢欲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几个月前看《入殓师》影碟,看到本木雅弘拿剃刀替他电影中死去的父亲,一刀一刀伴随着一滴一滴眼泪,刮去满脸的胡茬时,我就已经尝过崩溃的滋味。我从本木雅弘模糊的眼睛看到了另一张满是胡茬的脸。
我父亲一生拘谨,而且愈老愈拘谨,完全不像个饱尽沧桑的老人。他生病住院时,年轻的护士要带他如厕,他腼腆地拒绝了,一直等到我去看他时,他才忍不住开口,走出洗手间时还会尴尬地对我说声“谢谢”。
有时候我看他满脸胡茬,问他:“怎么胡子都不刮呢?”他总是叹口气:“有什么好刮的?”但我拿电胡刀替他刮胡子时,他脸上又露出那种腼腆的表情,动也不动地等我刮完后摸着他的脸,笑他:“你看,又像个老帅哥了吧!”他也是一声“谢谢”,更不要讲我隔几个礼拜替他剪手指甲,脚趾甲时,他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又多么的不自在了。
他离开前那个夏天,我回南部家里看他,陪他坐在屋外的藤椅上聊天。南部天气又闷又热又黏,黏到连风都吹不动,他还是一件麻纱汗衫,一把蒲扇,安静地靠在椅背上,听我絮絮叨叨东拉西扯,只有听到关于他孙子的话题时,他才偶尔插个话,牵出一抹一闪即逝的微笑。看我讲得满头大汗,他拿蒲扇指了指屋里:“你进去吹电扇吧!”
那天替他刮完胡子剪完指甲后,抱了抱他跟他说:“我回台北了。”他点了下头:“天热,就别回来了。”坐在几万英尺高空的机舱里吹着冷气,想他可能还躺在屋外的藤椅上, 想着我才抚摸的那张满是胡茬的脸,蠢蠢欲动的泪腺终于又失控了。
那是我跟父亲相处的最后一个夏天,一个又闷又热又黏的夏天。
最后的眼神
从火葬场捧着他的骨灰坛一路到灵骨塔安放后,我跪在冰冷的磨石地上,凝视着他那张邮票般大小的黑白照片,久久不愿起身离去:终于,到了阴阳两隔的时刻了吗?
那个时刻,我曾经想象过好多年,三更半夜担惊受怕过好多年,也思想准备过好多年,但从那大清晨接到那通电话后,我却让时间冻结,不肯承认,那个时刻果真来了。
那天早上母亲下楼,看见他还睡在床上,侧着身右手掌压在头下,他一向习惯的睡姿。母亲叫他:“老头子起床啦!”未应,推他,也未应,才发觉她十七岁在战火中下嫁的那个人,已经在睡梦中悄悄离开了她。
她和我父亲牵手在桂林,分手在高雄,五十载岁月,几万里长路,多少次生离;对他们那代人来说,死亡,其实并不陌生,两次战争,他们见证了太多死亡,死神也曾像敌人一样一路紧紧追在他们的背后。但每次想起那个当年骑在枣红色军马上的年轻英俊军官,这次真的撒手离她而去时,母亲总是感叹又感叹:“老头子让了我一辈子,早知道他这么早就走,就该对他好一点!”
母亲的感叹何尝不是我的感叹。父亲三十六岁时生我,八十岁离开我,四十载都成肠断史;有几年只要脑海里浮现关于他的种种,我就毫不迟疑立刻转念,害怕自己一打开闸门,就再也挡不住记忆洪流汹然轰然的侵袭。
过去一年,我从父亲在安徽出生的小镇写起,写他的故事,写他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以及为人爷爷的那段历史;就像在拼图一样,我把散落一地的拼图零片,安徽的、桂林的、贵州的、上海的、高雄的、台北的,一片一块地拼贴组合,尝试去拼出我父亲的图像,那个图像中有他经历过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跟他相关的各式各样人物。
但我愈写才愈发觉,我找到的拼图零片,其实比我找不到、早已因遗忘而遗失的零片,少了不知多少倍;再加上我又是个拙劣的拼图者,以至于父后十四年,我至今依然未能完成父亲的拼图。
当然,有些拼图零片,我是刻意选择性地遗漏:我在他入殓时见他的最后一眼,我执铭旌走在棺木后送他到火葬场的那段路程,他的肉体被烧成骨烧成灰装进骨灰坛的那一刹那……我虽然几次想将这些记忆的零片化成文宁,但却几度怯懦迟疑而缩手。
我父亲只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比许多平凡人更平凡百倍千倍的平凡人,他自己如是观,别人也那样看,我当他的儿子,竟然也懵懂浑噩了四十四年,误以为他既无高深学识又没显赫经历,他的一生当然平凡至极,他的故事也当然贫乏至极。
但我忘了,彻彻底底忘了,父亲,每个人的父亲,都是不平凡的。在父亲这个名词的前面,平凡或者贫乏这样的形容词,根本都是不该存在的赘词。
到今天,我只要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它就是父亲这个名词的定义,也是我印象中父亲的模样:我读高中时,每逢下雨天,“到了下午雨还没停的迹象,他一定会穿上雨衣,骑着他那辆笨重漆黑的飞利浦牌脚踏车,一路骑到我学校,到我教室那栋红砖大楼边的大树下静静等着”,“等下午某堂课下课铃响后,我下楼走到大树下,从他手上接过一个折叠成四四方方用油布包着的小包裹(油布里包的是一件雨衣),然后再看着他骑上脚踏车,缓缓骑出校园大门”。
我父亲的一生,他当父亲的那个角色,以及八十年岁月中他当过的每一种角色,其实,都尽在那个下雨天的画面中,直到这一刻,我似乎还能感觉到,他缓缓骑出校园大门时,回头再看我一眼的那个眼神。
那是父亲的眼神。
(摘自《我叫他,爷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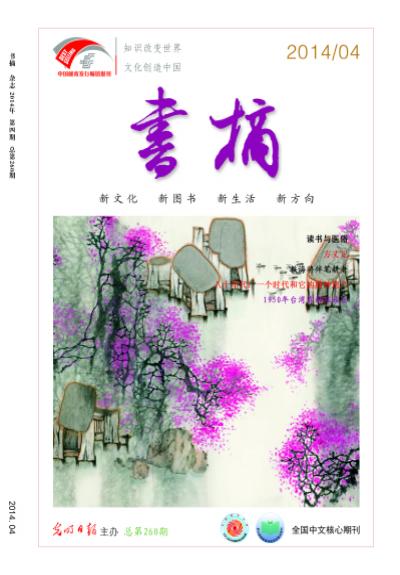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