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过去的八十年代并未真的过时——它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库,其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仍可凭依。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它的光荣源于八十年代的梦想,它的梦想也能唤醒八十年代的光荣。
卢跃刚:新闻媒体作为“公器”始于八十年代
《新周刊》:能否先谈谈八十年代中国新闻界总的思想特征与精神状态?
卢跃刚:八十年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这股社会思潮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八十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主题词是“启蒙社会”、“推进改革”,意识形态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编辑、记者相当自觉地反省假、大、空宣传对社会对国家对人心的危害,相对独立地进行新闻判断,并逐渐向“新闻职业化”、“新闻本位化”转型,以推动社会进步。
《新周刊》:当时有一些全国反响的重大报道凸显了传媒在引发、推动中国社会思潮方面的作用,请你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卢跃刚: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都不为过。应该说,八十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八十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做出的反应。
《新周刊》:你对八十年代全国各地新闻传媒自身的发展有何认识?
卢跃刚:我首先要说说《读书》。《读书》是我的启蒙老师,读了26年,即使《读书》已经办得很糟糕了,我还是期期买,哪怕是看看题目就扔。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底层生活的青年读到《读书无禁区》这样的文章,浑身在燃烧!看的遍数多了,我几乎能把李洪林这篇文章给背下来。我的书桌上唯一一件艺术品,便是《读书》创刊号原大木刻,上面刻有《读书》创刊号封面和目录。一本读书刊物,与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实在是罕见。后来,出版家办《读书》的时代结束后,《读书》编辑方针丧失了“公共性”,实在遗憾。“长江读书奖”甚至闹出了丑闻,诱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知识分子的公开分化。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报》非常值得研究。我是1986年调进《中国青年报》的。当时按照发行量和影响力算,有“中央七大报”之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从报道的内容、文体创新、思想敏锐、启蒙立场考察,《中国青年报》无疑都是处于先锋的地位。这家党报不论资排辈,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鼓励成名成家,鼓励名利双收,所以有一个让人缅怀不已的业务民主空气。八十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文学的影响力绝不逊于新闻,甚至超过了新闻。除了早期的《今天》,还有《人民文学》《中国》。如果《中国》不垮,我不会去《中国青年报》。文学刊物在八十年代社会传播学意义上的研究,目前还没有看到。
钟叔河:出古人的书,为今人开路
钟叔河的普通话不好,但谈吐斩截,情绪饱满,中气也很足。“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人一生下来就判了死刑’,只是个缓期长短的问题。”这话从钟叔河那里说出来,显得意味深长。
钟叔河1931年出生,解放后在报社工作过几年,1957年被划成“右派”,拉板车熬活,“文革”期间又蹲了10年监狱,正经的工作时间只有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然而,他用10年时间就奠定了中国出版界先行者的形象。钟叔河身上,有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气象,他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周作人文集,重编《曾国藩全集》,都是在出版界开新风的手笔。
1979年“改正”时,钟叔河已年近五十。深感时不我待的钟叔河,马上开始着手“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钟叔河的“帽子”是《湖南日报》摘掉的,但“改正”后他要求去出版社:“进出版社就是为了编‘走向世界丛书’。”为什么出这套书?钟叔河在《与之言集》中说得很明白:“书虽然算古籍,读者却是新人。整理出版古书,应该引导读者向前看,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
为了编“走向世界”,钟叔河翻阅了两百多种笔记,打算出100种。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钟叔河以前就读过,但没有正式出版过的版本,他得到处跑着找资料。
开始,钟叔河只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手里也没有“团队”,主要的工作都是一个人来。审稿、校对等编辑出版中的“额定”事项已足够繁重,他还要给丛书的每一本书撰写前言,每篇都是长文,最长的有三万多字,最短的也有8000字,写一篇大概要一个星期。但这并没有影响“走向世界”的出版速度。他介绍说,当时一个月左右出一本。
在北京看到“走向世界”后,钱锺书对时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的董秀玉说,编这个书的人如果到了北京,他想见见面。1984年1月,钟叔河到了北京,由董秀玉带着去见钱锺书。钱锺书对钟叔河青眼有加,不仅因为钟叔河的编书之功,还因为他十分欣赏“走向世界”的那些前言。钱锺书告诉钟叔河,这些前言可以结集出书,并主动承诺为书作序。这本书就是《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
到岳麓书社后,钟叔河又干了两件事:整理出版周作人和曾国藩的书。这两个人,一个是“汉奸”,一个是“汉奸刽子手”,他们的著作一直没人敢碰。
钟叔河很喜欢周作人的作品,三十出头的时候,他给周作人写过信。周作人不仅回了信,还把与钟叔河通信一事写进了日记里。钟叔河回忆说:“周作人当时的处境比我好得多,连海外的邮件都可以收。因为‘文革’开始前,周扬、胡乔木,甚至毛泽东都对他比较照顾。我当时是‘贱民’,干苦力,要不是当时年轻,很难活下去。”能收到周作人的回信,对钟叔河来说,是很让人振奋的。
对钟叔河来说,编“走向世界”是“借古喻今”,出周作人的书是“士酬知己”。尽管周围的压力很大,还被人指为“偏爱汉奸”,钟叔河还是坚持要做。钟叔河说:“那些反对出版周作人和曾国藩的人,并不是恨‘汉奸’,而是怕惹上麻烦,影响自己做官。”
1985年,他先出了一本《知堂书话》(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书),还准备编一套周作人的文集,但又担心动作太大了,整个事情被禁掉。他从钱锺书那里获悉,胡乔木很喜欢周作人,于是寄了本《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过去,并附信说想编一部《知堂文化论集》。很快,钟叔河收到回信:“谢谢你寄书,祝你的《知堂文化论集》获得成功。”就这样,周作人这个禁区终于算打破了。
编《曾国藩全集》是钟叔河的又一跨越雷池之举。1983年,李一氓召钟叔河到北京开会,钟叔河在会上说要出曾国藩的书。国家出版规划倒是将这个项目列进去了,但只准备把原有的《曾文正公全集》影印出版。钟叔河提到:“原来那套书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编的,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了不少不客气的话,都给删了。”
钟叔河搜罗了一堆资料,在会场上条陈原版的讹漏,坚持要做新版。由于喜欢“走向世界”,李一氓对他印象很不错。钟叔河回忆说:“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李一氓专门坐到了我旁边,当时有很多人找他谈审批立项的事,李一氓把其他人支开了。我就想办法说服他。”通过会上会下的努力,新版《曾国藩全集》终于列入了国家出版规划。书出版不久,就有媒体说这套书“引爆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
对于当下的出版状况,钟叔河直言“不看好”。他说:“从自由度上讲,比八十年代进步了,但是我们的人不行了。”他说,现在的人肯定是越来越聪明的,但是,“没有理念了”。“我们那代人还是有追求的。在劳改队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以后还能‘改正’,更没想过自己还能回来拿起笔杆子,但我们都没有放弃探索。我当时就是要出周作人,大不了我这个总编辑不当了嘛!”
钟叔河的总编辑果然没当太久,1989年之后就提前退休了。倒不是因为周作人,而是他得罪了不少活人,他说:“我有总编辑的权力,你不能随便往岳麓书社里面安排人,只要水平不够,你是部长的亲戚也不行。”
退下来后,钟叔河反倒一身轻松,编自己想编的书,写写想写的文章。钟叔河自陈一向不爱走动,而且历来不爱吃吃喝喝,所以很少出门。老伴去世后,起居有保姆照顾,女儿每天过来跟他吃饭,但不住在一起。钟叔河有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他说:“这是最好的病。”“估计我会死得很快,不会老拖着。”
钟叔河希望这辈子不但对得起人,也要求自己对得起自己。“人还是要有点儿性格,想说的话我还是要说,太世故了不好,那样等死有什么意思?”
林汝为:那时候拍戏,什么劲都使上了
林汝为已经81岁了,平时鲜少在公众前露脸,但她一天也没闲着。她刚刚从山东采风回来:“正在写一个剧本,名叫《八活正传》,想讲讲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农民致富的故事。”她手头刚刚完成的另一个剧本名叫《别样青春》,似乎赶上了这两年影视圈最流行的“青春”大潮,但她讲的是自己的故事,“在抗战根据地长大的孩子们的青春,对你们这代人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她依然非常关心电视:“我现在看电视剧,只要看一两集,就知道这个人是在认真拍还是在胡闹,一眼就能看出来。”
28年前,从电影演员转行到电视剧导演的她第一次把老舍小说《四世同堂》搬上荧屏,成为中国内地首部长篇电视剧。作为拓荒者,林汝为回忆起八十年代来,怀念的是那时候单纯的氛围:“那时候拍戏真是要了大家的命了,什么劲都使上了。”
1981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林汝为调回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做导演。“当时中心里有电影厂调来的人,也有电影学院刚毕业的人,都算是有经验的人,但是拍点什么呢?大家对电视剧这个形式感到很陌生。”抱着一种“试着来吧”的心情,林汝为把老舍的《四世同堂》反复看了七八遍:“我们家老老少少都很迷这部小说,以至于家里书都不够,还得去新华书店再买一套。正巧市委宣传部给了一个指示:要拍有北京特色的题材。我就想拍这一部试一试,它太适合当时的中国人了。”
技术条件简陋,拍《四世同堂》只用了一台机器。在演员挑选上:“非常慎重,不能说谁有兴趣就让谁拍,不管是再好的朋友,他想加入这个组,也得先看他能不能完成老舍的角色,且要非常精彩,不能走了调了。”
林汝为念念不忘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的李维康。“老舍在小说中特别写了,韵梅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不能让婆家挑出一个‘不’字的媳妇儿。当时有人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这个事儿,还特地找到我们家,想要演这个角色,这使我觉得,我必须特别准确选择角色,不然就把老舍糟蹋了。”在林汝为的观念里,如果不是懂得很多做人的教养,演不了韵梅这个角色,而懂礼数的演员,最好是上京剧界找。“我去中国京剧院见了一次李维康,没说话,她正要上台,脸上全是油彩。”后来林汝为找到自己在京剧院的朋友:“你得帮我一忙,你请吃饭行不行?我得瞅清楚这个女演员。”虽说是饭局,但林汝为把这当成了一次面试:“连坐的位置都煞费心思,李维康坐哪儿,我就坐在她对面。担心她见了生人不爱说话,又让找了几个她的朋友一起。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地说一些家务事,在家里面做饭这些事情——要演韵梅,不会剥葱可不行。”
为了拍好《四世同堂》,林汝为带着剧组主创拜访了很多老舍生前的朋友,听他们讲老舍的工作状态,待人处世的态度:“慢慢我们都觉得老舍先生像是自己的父亲,这是一种单纯的情感,完全不同于今天把某名人当成自己亲戚的那种功利心。”林汝为还常常去见老舍夫人胡絜青:“有一天,她从八宝山火葬场请了十几位工人来跟我见面,听他们讲旧社会的时候是怎么处理死者的。头一次见他们的时候,我心里乱蹦,为什么呢?我看到这些人的眼睛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他们看人的时候,是非常认真地看着你,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人的眼睛为什么这样亮呢?跟他们聊天以后,我才知道因为他们有很多跟死者亲属接触的经验,所以他们看人的时候,都是非常深沉的。”
八十年代的单纯环境,是今天所不能比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演一个戏多少钱,有什么呢?有补助费,一天一块五,得自己带饭。有些演员不是每天都有戏,他们的待遇是每天八毛。我们家没什么钱,我从来没拿过酬金,那时候拍戏,收入就只是工资。”
《四世同堂》播出后,反响之强烈超乎想象。但林汝为并没有看见这种情况:“我头一天晚上在机房把片子做完,交给制片,第二天早上5点到机场,就出国了。”直到一年后,林汝为回到北京,制片主任交给她厚厚一叠报纸和杂志。“我这才知道这戏有多火。”
(摘自《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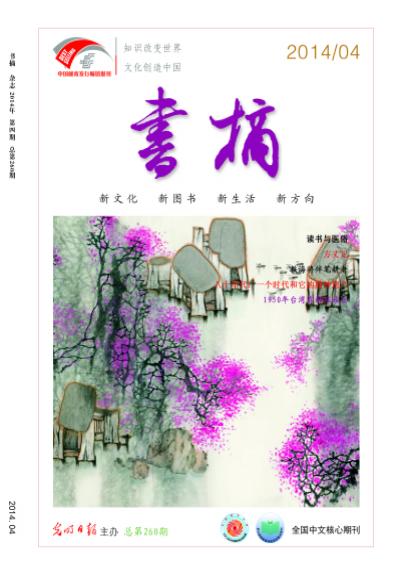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