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种宽泛的比喻中,古典世界要么被比喻成童年,要么被比喻成老年,而现代世界总是一个青年的形象。童年和老年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自足的,它们的丰盈来源于自身,而青年的同义词是发展和变化,是不断地依赖于他者,攫取或给予,创造或毁坏。现代世界里充满了争吵和运动,而古典世界则是恒久安详的。
在《红楼梦魇》的自序里,张爱玲谈到自小对《红楼梦》和《金瓶梅》的迷恋,她说,“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非常震动,因为不曾有这样的体验。或许可以安慰自己说,这样类似泉源一般的书至今还没有遇见,就像恋爱失败的人安慰自己说那个最好的人还没有出现,但这样的安慰其实是虚妄,因为假如存在这样的书和人,也一定是从少年时的初心里一点点长成的,而非从外面找到或撞见。说到底,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虽然有点惶恐,像一个没有信念的人,但也只好这样。
52岁的维特根斯坦说:“像个骑自行车的人,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着踏板向前。”一个没有信念的人,在其最好的意义上,也就好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生活是成问题的,所以会有那么多不停在寻找解决生活问题的人,“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是乱世的问题,有些凄惶和严峻,因为关乎身家性命;“天下方太平,荡子何所之”,则是盛世的问题,有些迷惘和不务正业,但同样也是性命攸关,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随时会倒下。
至于现世是什么样子呢,我也不清楚。有两位我很敬重的学者,他们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交集,前几年分别出了两本书,书名的意象却惊人地相似,一本叫做《何枝可依》,一本叫《拣尽寒枝》。“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卜算子》常被说成是东坡贬居时写给某个女子的情诗,这种解释,就好比把《短歌行》解释成曹操的招贤令,都似乎明明白白端出了个答案,却从来不去想这答案对己身有无作用。而所谓诗无达诂,也不纯粹就是读者反应的胜利,因为一首好诗在后世寻找和唤起的,那些具体时空里不息的生命激荡,终归有其相似的涟漪。
《何枝可依》和《拣尽寒枝》都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只是读书札记,看起来都是东鳞西爪,忽今忽古,无所归属。在《何枝可依》的自序里,作者最后说:“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不仅回不到孔夫子和孙中山的时代,同样也回不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代。路在哪里?我很茫然。一个时代已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而《拣尽寒枝》的作者在前记里也说道:“无论读本科还是念研究生时,我都不大清楚什么书真正值得去细读,即便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的书值得读,也不知道怎么读……老实说,我一直在不断自个儿摸索什么书值得读以及如何读——而且始终带着一个心愿:想要清楚知道,因现代性而支离破碎的中国学术思想最终在哪里落脚……种种经验和教训,余温犹存。”
我很喜欢这样坦诚的表达。生活都是成问题的,杰出的人也不例外。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正确生活着的人不把问题体验为悲哀,所以,环绕他生活的是一轮明亮的光晕,而不是可疑的背景”。他们并不急于把问题变为答案;相反,那些问题照亮了他们脚下的道路,并慢慢地,消失在身后。
(摘自《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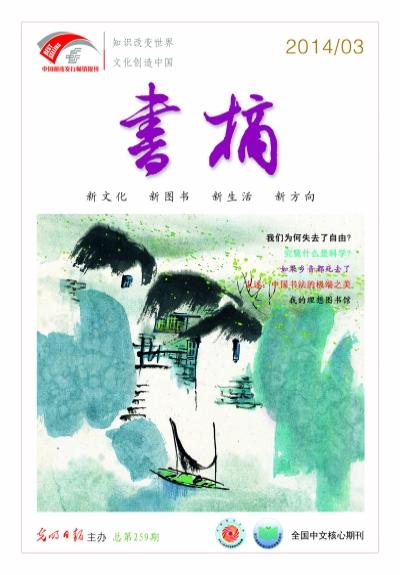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