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辅导员是王岐山
1964年秋,我考上了北京第三十五中学。从三十五中走出来的如今最有名的大约就是王岐山了,当今的中国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还是我初二时的辅导员。
新学年开学的第一课,就是讲语文课中第一篇文章《梁生宝买稻种》,里面有个人物叫“任老四”。讲到“任老四”这一段时,老师提问了我,也刚好这个班只有我一个姓任的。于是“任老四”就在同学们相互都还陌生、彼此叫不出名字的时候,成了我的外号。如今仍和我保持联系的许多同学也还亲切地称呼我为“老四”,这让一些圈外人误以为我是在家里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
五年级之后,同学们为了省下公交车费,常结伴步行回家。那时我们住校,通常会在星期日晚归校时,拿到父母给的两三毛钱公交费。当时的公交车是按四分、七分、一毛、一毛五的标准,分站计价的。
五六站路程的车费一般在一毛之内,为了省下这一毛钱,我们会长途跋涉,步行回家,沿着城墙外的外护城河(由木樨地向南的那条河),经市府大楼取道木樨地,然后沿铁路向北到三里河。
那是段自由欢乐的时光,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一路上,或打打闹闹,或跑跑跳跳的。夏天采着草中的小花,撩拨着河中的清水,秋天抓着不再活跃的蚂蚱,品尝着红的、紫的叫不上名称的野果。从菜市口到三里河或军博,对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那时的北京城还没有现在四通八达的马路,没有高楼大厦。城外尽是破旧的平房区、荒野和正在建设中的各种工地,我们还要从一条每天都有很多火车通过的铁路跨过。
上初一时班上的辅导员是姚明伟,姚依林的大儿子,高三后他去了越南学习,中间由蒋小泉接手过一段时间。再接下来就是王岐山了,当时他上高二,他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辅导员,从在校学习到上山下乡,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至今他还会偶尔在半夜打来电话,我们经常一聊就聊很久。
初中的辅导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大哥哥,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导师,但却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阅历帮助我们独立思考。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岐山找我谈话,让我写申请,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这一步之差,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
不知道今天的中学,是否还有这种高年级学生到低年级学生班中当辅导员的制度。但对于初中生而言,有了哥哥或姐姐式的帮助比只有师生之间关系的教导要有用得多,遗憾的是我们连初二都没毕业,中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在延安插队
毛主席一挥手,一声令下,结束了所有中学生们的学业,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移民活动。上山下乡,“到广大的农村去”成为所有人完成中学学业之后的唯一出路。我是1969年1月9日出发的,和一个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班里的同学分在了不同的村子,我住的是个离延安最近的村子。
整个村庄有十几户人家,村里给我们准备的窑洞是队里的仓库翻修的,一口整窑,旁边有一个占据半窑的炕,窗户正对着两米之外羊圈的门。隔壁就是两个空窑洞,养着队里的几十只山羊。窑洞一进门是两口大缸:一口缸中是村里为我们准备的过冬菜,用盐腌的蔓菁,一种类似于萝卜的当地菜;另一口是水缸,村民们都要从沟边的井里挑水,存放在大缸里,缸里的水要用白矾净化沉淀,否则会从水缸里跳出蛤蟆来,几天就要淘一次缸,否则缸底就沉了厚厚的一层泥,往缸里续水时会将整缸的水搅浑。再往前走是一块石板搭成的案台,是放碗筷、调料和切菜的地方,有个圆圆的菜墩子。紧接着就是灶台,能放两口锅的火灶,烟道在炕下盘绕,窑洞的底部边上有个垂直的烟道,一直通到山顶上,冬天这就是唯一的取暖设施了。
灶火既要解决做饭、吃水问题,同时要让余热成为暖气。而夏天做饭就要到外面去另起炉灶了。洞的底部靠墙的位置又局部向里挖出了个平台,这里就成了储存室、大衣柜。炕桌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吃饭外,写信也全靠它了。村民点的是一个碗状的煤油灯,而队里给我们准备的是那种有灯罩不怕风吹的马灯,也比一般的油灯要亮些,还可以方便地放在车上或挂在窑壁上。我们来的时候带了蜡烛,原本以为多余,现在却当成了宝贝,不到关键时刻舍不得拿出来用,通常是在大家都睡了,而某人还想单独看书或写家信时才拿出来用。就这样,共约20平方米的地方住了七个大小伙子,虽拥挤但也其乐融融。
学生下乡第一年的粮食是计划供给的,第二年的口粮就要靠自己赚工分了。最初队里给同学们定工分是一天6分,加个早工能多一分到二分。每个窑洞中都有一个单线的小喇叭,公社的广播站会用这个小喇叭来传达上级的指示。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小广播就开始播放《东方红》,于是我们就开始“早请示”。村里百姓集中在村头的场子上,面对着一堵有着毛主席像的矮墙,高举着红宝书喊着“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随后就上太阳出来之前的早工。后来我们会了一些技术活,于是分工有了差别,我和两个同学最高评到了8.5分,早工也涨到了1.5分,于是一天下来能挣到10个工分了,一个完整工的分值。而当时村里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一盒火柴钱。晚上下工,大家还会在队长的带领下到主席像前“晚汇报”,这之后才能各回各家。有时队里还会按上面的要求轮流由张三、李四来安排晚上的学习,如读几天前的《人民日报》社论,阶级斗争在农村这个山沟沟里也丝毫不能松懈。
除了精神食粮外,我们首先还要解决基本生活中的吃喝。山里没有炒菜的油,连酱油类的调料都要到十几里外的下坪去买。附近几个村里只有下坪一个供销点供应给我们的毛粮,还要拉到这里来加工,如高粱去皮,小麦磨面,小米退壳等。烟、酒这些都是奢侈品了,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等于好几天的工分。
这里供应的油是麻油,一种大麻子产的油。当地农民都会在自留地上种大麻子,收下来熬油,存着过年或有客人来时用,平时都用的是动物油,如猪油、羊油等,记得村里曾给我们准备了一挂羊油。记得一次一个同学自己在家做饭,偷偷跑到老乡家买了十几个鸡蛋,自己在家煎鸡蛋吃,一铲子羊油,煎一个鸡蛋,一连吃了十几个,等我们回来了,羊油少了一大块,这同学也捂着肚子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一个人闯关东
从延安回京之后,我又去了莫力达瓦,来到东北部大草原,领略北国的风光。
一个小村只有一条路和路两侧的十几栋房屋,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但却生产了吃不完的粮食,还有人均不少于三头的牛群、羊群等,这里与延安真有天壤之别,让我这从山沟里来的知青大开眼界。
对比延安和东北,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延安用无数鲜血培育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承载无数人的希望,如今又要用几代人的贫穷分担本就无力抚养的大量人口,让这片有着光荣传统和巨大贡献的土地继续承受着不堪重负的压力。但东北这块地肥沃得可以让许多人不但能吃饱肚子,还能养牛、养马、养羊,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逃荒者、开拓者和战争的残留人群。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资源配置合理性”这个名词,但我们能深深感受到土地资源的差别与人口生存环境的差别让本就不应再增加大量人口的土地承担更多知识青年的生活重担,而东北这个本可以养活更多人口的土地却被忽视了。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完成了秋收,剩的就是场上的活儿了,如去皮收豆、玉米脱粒。满目看到的都是丰收的景象,一个村生产的粮食几乎比我在延安一个公社的收成都多。
秋收之后农村人多是农闲了,东北叫“猫冬”,但这里却还有许多的农副业。一是收割一人高的牧草卖给军队当马粮。二是上山砍柴。这里有大量的原始森林,木柴是主要燃料,一冬天要准备一年的干柴。割草我没赶上,但学会了砍柴。
说是上山砍柴,但斧头是干零活的,主要靠锯子。两个人一起上山,选择那些不成材的松树,从根上锯,差不多要断时,在另一侧用斧子砍个缺口再用力一推,树就倒了。冬天砍柴,树木冻了之后是脆的,砍起来很容易。再用锯子和斧头清理了枝杈之后就可以装车了。一牛车的木头拉回来后,要锯成一尺半左右的一段段圆木,再用斧头劈成瓣子。这个活也要在冬天树木中的水分都冻住时干,一斧子下去自然就裂开了,如果在树木不干的夏天,这个活就要费力气多了。
再将劈好的木头瓣子一排横一排竖地交叉垒成堆,慢慢将湿柴风干,这样烧时屋里就不会冒烟了。通常每家每户都会在冬天堆上几垛这种木头瓣子,像存粮食一样地存上一大堆的干柴。过了冬天就没时间再去忙这些闲活儿了,也没有冬天那么容易干了。
这里冬藏的菜中,既有萝卜、白菜、土豆,也有许多风干的豆角和叶类干菜。主食则以小麦、玉米、大豆为主。冬天懒得做面食,我们就炖上一大锅玉米子和豆渣子混合饭,可以连吃好几顿或好几天。那时的饭量都很大,每个人都用中个的洗脸盆当饭碗,一次至少要吃半脸盆的饭。
在延安时跟老乡们学会了卷烟抽,老乡们说这是为了解乏。东北几乎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包括老人都会卷烟抽。而这里抽烟则大多是为了防止蚊子与小虫子咬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殊环境,同样也就造就了一套各自的生活方式。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似乎是与世隔绝的。也许这里本就是一些土匪、氓流和逃荒者生存的地方,因此“文革”并没有对这里造成太多的影响。我们这群学生中,大多是“黑帮”子女,但并没有因此而被歧视。老乡们也没有刻意“再教育”,甚至没有人关心你的家庭、你的过去。反而是一群学生们在不断研究着《资本论》,关心着国家大事,偷听着各种广播,讨论着政治局势。也许此刻他们的父母都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反而是当地那些只知道自己的世界如何好的老乡们给了他们更多的关怀与温暖。
(摘自《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58.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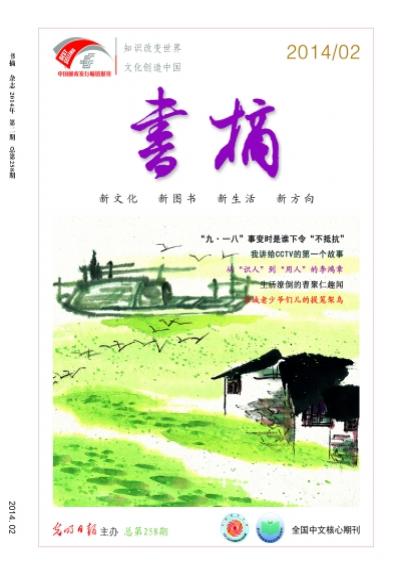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