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最近网上流行一个段子: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令人莞尔之余,又多少有些凄凉。一则消息,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一位老人和三个孙子、孙女围坐餐桌吃饭,因为孩子们频频低头玩手机,老人生气,摔了眼前的一个盘子,扭头回房。三个年轻人傻眼,只好轮流进屋劝慰,才最终平息了老爷爷的怒气。
其实手机只是割裂真实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媒介,早在手机普及之前,便已出现“交流之无奈”的端倪。十年前我上大学时,第一波互联网浪潮风头正劲,同宿舍四个男生各守着一台电脑,看新闻,玩游戏,搞网恋,最终发展成四个人背靠背坐着,却用QQ聊天的习惯。
技术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带来经济的增长、政治的变革和文化的转型外,恐怕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对人与人之间交流方式的冲击。互联网和手机,让面对面不再成为必需,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提高了沟通的效率。现在与我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有上海的,有成都的,有广州的,有港澳台的,也有欧洲和美国的。我和他们大多素未谋面,仅凭电子邮件和MSN沟通,就能迅速完成工作。而自从有了微博之后,我也和学界、业界的很多同行有了不少交流,大家在网上互相转发、点评、调侃,却也不必见面,甚至根本不会见面。
但这种高效、快捷的交流方式,也产生了问题:它在本质上,是将社交礼仪从交流中剥离出去的一种方式。换言之,我可以同时与很多人打交道,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不必遵守任何必需的仪式。交流似乎变得更纯粹,却也更走向去深度、无意义的道路。我不必洗澡更衣,不必梳妆打扮,不必挤地铁到很远的地方和对方见面,也不必拥抱、握手、拍肩膀。剩下的,只有最直白的“干货”。可是,这样的交流,难免走向廉价和浅薄。难道不是吗?我们只在有直接需求的时候,才会去用这种最方便的方式与人联系,追求的,要么是利益,要么是即刻的快感。交流结束,就真的结束,不会留下什么值得玩味的东西。
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仪式。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文化的传承和运转,主要依靠仪式来发挥作用。婚礼的仪式,让婚姻的意义作为一种为众人见证和法律保护的契约而得到强化;葬礼的仪式,让死亡变得更加肃穆,同时给逝者生前的至亲好友一个适宜的时机去合理地表达他们的悲伤。在远古社会,在祭坛前宰杀牲口并向本民族信仰的神祇祷告,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仪式,即使到了千万年后的现代,它也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延续着(如家庭里供奉的佛龛和祖先牌位等)。如果按照“最有效”的原则来看,这些统统是毫无用处的繁文缛节。但这些东西让这个世界更稳定、更亲切,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更笃定。
得承认,我对新技术始终持有怀疑态度。这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时常在我脑海中与“荒凉”、“冷漠”联系在一起。西方的一些社会运动家发明了一个词,叫“懒汉行动主义”,说的是大家似乎都很活跃,转发、评论、短信、QQ,仿佛鼠标一点,自己就亲自参与了社会的变革,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可实际情况是,这种看似高效的“伪交流”,除了满足交流者本人的一些快餐式的需求外,从长远来看,对这世界的改变微乎其微。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丢掉手机”的民间运动。在我国,也有一些还不太成气候的民间团体用各种方式鼓励人们离开网络,走上街头,和真实生活里的真实的人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实应该是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距离。也许每一个沉迷于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世界里的人都在琢磨如何“做些改变”,但真正的改变,却需要很多的勇气和极大的毅力。
“小镇青年”的快乐生活
寒假,我回东北老家小住了半个月,见到了几个久违的表弟,讶异地发现他们竟都已“长大”。有的上了大学,有的毕业进入外企工作,有的马上面临高考。这班男孩子从小就在我的“带领”下成长,如今我倒成了其中个子最矮的一个,真有“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意味。
久居外地的经历已经使我难以融入他们的日常对话,他们对我的态度也由儿时的亲昵变作礼貌与敬畏。他们就是京沪穗的白领们时而艳羡不已、时而不以为然的“小镇青年”。相比京沪穗,小镇依旧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电视依旧是青年们最常接触的媒体,尽管他们观看的节目与父辈们有很大不同。而大城市居民须臾不可离的互联网,在小镇仍主要是一种娱乐工具。另外,相比大城市,小镇社会的契约关系比较淡薄,而亲情的纽带则远为强烈。姊妹兄弟是日常交往最多的人,血缘关系被视为一种近乎神圣、难以打破的社交基础,这也令从大城市归来的我颇有些疏离感。
当然,大城市与小镇的差别是无法在寥寥数语中描摹清楚的。我想传递的,无外是一个久别小镇、重新归来的原小镇青年的零星感悟。总体的感觉是,尽管我比我的同辈见识多得多、懂得多得多,却似乎远没他们快乐。我的一个表弟,小我5岁,现在是某汽车生产企业的技师,工作辛苦,薪水却并不高,但他显然比我更热爱自己的工作。一年前,他认识了一个长得不很漂亮、能力也不出众的女孩,今年就要结婚,明年计划生子。他的收入,即使在长春这样的城市,也只能算是中等,但他似乎毫无沮丧情绪,而始终活得健康、乐观。用他的话说,多赚多花,少赚少花,生活总是能过下去的。
此外,我还见了个老同学。当年他成绩优异,也考到大城市的名校,却在毕业后选择回家,进了本地的银行。听到我已经没有半点家乡口音的普通话,他有点惊讶地问了一句:“你这么说话不累吗?”我本想解释自己不是故意这样说话,而是已经习惯了这样说话,但转念一想,解释清楚了似乎也没太大意义。吃饭的时候,他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妻子让他在回家的路上买些菜,另一个是妈妈问他周末是否回家吃饺子。他笑着哼哈应付,挂断电话,并对我说:“女人就是麻烦。”可天知道那一刻我有多么嫉妒他。
其实,比起大城市来,小镇的生活依旧是不大好过的,尤其是长春这样“衰落”中的老工业城市。过高的失业率、普遍较低的收入、严苛的气候以及狭窄的视野,令小镇青年的生活并不轻松。但相比京沪穗,小镇的文化是有机的、富有人情味的。情感的因素使原本艰难的环境变成了一种可被很多人共享的生活经验。邻里之间彼此熟识,每个周末都有人来串门,大家聊天和交流的话题包括热门影视剧、赵本山的小品、本地的二人转选秀节目以及坊间传播的流言蜚语。尽管从功利的角度看,小镇的绝大部分日常言谈均属“无效传播”,但其对于小镇青年快乐而充实的生活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
城市化和现代化对有机文化的破坏,已有很多人做出过反思。但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福利的同时,却总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每年的春运,就是大城市与小镇之间的一次文化对接,接口虽遍布锯齿,却让两个世界里的青年能像照镜子一样看见另一个版本的自己。小镇青年的快乐生活,成了京沪穗的忙碌白领们将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心灵的教材。
每个人都需要集体记忆
柯达公司濒临破产,不过是全球性金融风暴中一个平淡无奇的个案。但对我来说,却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故。在我的家里,有个考上大学时从老家带来的旅行箱,里面仍静静躺着几个 ISO100和ISO400的柯达胶卷,前者外壳是暗绿色的,后者是嫩黄色的。那些始终未见天日,也许永远不得感光的胶片就隐藏在薄薄的金属包装里,不知陪我走过多少城市、过了多少年。
当然,我对柯达胶卷的感情并不只因为大学学过摄影那么简单。我的母亲曾是整个长春市最优秀的胶片冲印师之一,彼时并没有多少人掌握这门既需要丰富光学、色彩与化学知识,又须操作复杂机器的手艺。整个童年,柯达胶卷是我生活中最常见的小物件,我用废弃的胶卷壳和万能胶手工制作过坦克车,还拿到学校的艺术节展览。在我考上大学后两三年,传统照片摄影迅速衰落,数码相机取而代之,让母亲吃了半辈子饭的高端技术,一夜之间失去市场,一个会简单操作电脑的中学生,就能替代她。像所有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黯然隐退的人一样,母亲和她的同事无奈地退出了历史潮流。只是,直到现在,我家的各个角落里仍能零星找见用过没用过的胶卷,供我们缅怀过去的日子。
如今,集体记忆已是个非常时髦的词。在北京、上海等时髦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胡同和弄堂里,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国货商店”,店主仿照老国营商店模式经营,售卖白瓷茶缸、回力球鞋、蜂花洗发水、百雀羚护手霜和永久自行车,年轻人趋之若鹜,尽管对他们来说这些老国货背后的故事往往过于陌生和遥远。
这样看来,集体记忆似乎与年龄没有必然的关系。并不是老年人才怀旧,八零后、九零后也有类似的需求。原因何在?我偶尔会和学生聊起这个话题,问他们为何要去追逐一些不属于这个年代的、古老的记忆。得到的答案有很多,但归结起来,无外两点:一是他们大多在互联网环境中长大,缺少标示自身的共同生活体验;二是现时的社会环境中缺乏可以供一个群体共同尊奉的理念或信仰。于是,伪装成“老物件”的商品“乘虚而入”,扮演了集体记忆承载者的角色。
所以说,人人都需要集体记忆,并不必然意味着过去必然比现在美好,而是因为现时的社会变得零散、孤孑、不再“有机”。每个人都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想方设法避免着与他人发生文化或情感的交集。在社会和私生活之间,缺乏一道具有凝聚力的黏合剂,那就是“社区”。
所以,在我看来,为每一代人营造共同的生活经验,建构有机的、自然的集体记忆,应该是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样是文化商品,也有真诚与不真诚的分别。看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黄土地》和《芙蓉镇》,90年代的《活着》和《霸王别姬》,与今天的那些票房动辄几亿的大片,为人们带来的文化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其间的分别,与投资的多寡、票房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有时我想,也许我对柯达胶卷的感情主要源于其真实而真诚地记录了我的生活,像一种仪式;而今天的数码技术让影像泛滥到无可复加的地步,照相不再具有独特性。
建构集体记忆,其实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工程。它要求我们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内心,聆听灵魂深处的需求。
(摘自《最繁华处最惊心:一个青年学者的文化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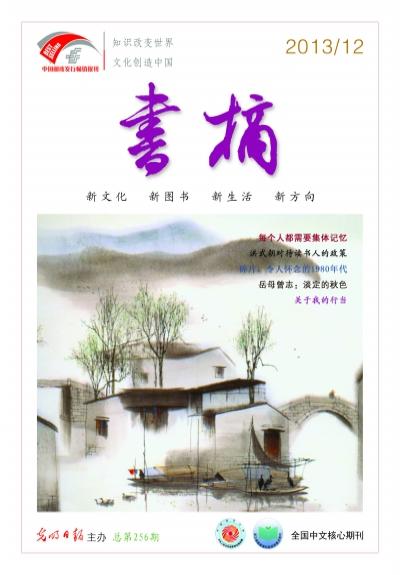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