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十分重视身上的佩饰,不仅用以美化自身外形,而且借以标志身份等级。佩饰都系在革带上然后连于大带。常见的佩饰有玉、珠、刀、帨等。
玉是最重要的佩饰。《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又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一走动佩玉即发出叮咚的响声,是因为所佩不只一玉。
玉本是一种贵重的装饰品,为贵族豪富所专有,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却把佩戴玉石附会上一种神秘的道德色彩。《礼记·聘义》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似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绌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三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玉的这种人为色彩并没有被着重表现,每凡说到佩玉,都在借以烘托人物的高贵或环境的华美。
容刀也是一种佩饰。《诗经·大雅·公刘》:“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但《释名》不以为是加了装饰的刀:“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无刃,备仪容而已。”大概刘熙是据汉代礼仪解释的。在上古,人们佩带刀剑,既是装饰,也用以自卫。《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警卫人员)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因此荆轲要刺秦王,只能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而秦王侍医夏无且只能以药囊打荆轲,其他人员看着荆轲追秦王都毫无办法。朝廷既有此禁令,要佩刀剑以为饰,便只好做刘熙所说的容刀。
古人还喜欢在身上佩带香袋,里面放香草香料,类似后代荷包的样子。香袋古称容臭。《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后来则称香囊,而且不限于佩带。《谢玄传》:“玄少好佩紫罗香囊,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取,即焚之。”杜甫《又示宗武》:“试吟青玉案,莫带紫罗囊。”用的正是谢玄的典故。古代也有称香袋的。《洛阳伽蓝记》卷五:“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
佩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是各个时代风尚的组成部分。各个时代花样不断翻新,总的说来,它的作用也和服装一样,主要是为了美观和标志地位。其中,有些还依稀保留着人类原始社会生活状况和习俗的痕迹。
酒
我国酿酒的历史很久远,可以说是与种植生产同步的。据说殷朝人特别喜欢喝酒,纣王就曾“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据说殷即因此而灭亡。《尚书》中的《酒诰》,就是周公姬旦告诫殷的遗民要以纣为鉴,不要沉湎于酒的。现代出土的殷代酒器极多,说明当时饮酒的风气的确很盛。其实喝酒并不是殷人独有的嗜好。例如在《诗经》里就有很多地方提到酒: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豳风·七月》)
有酒湑我,无酒酤我。(《小雅·伐木》)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鹿鸣》)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日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小雅·宾之初筵》)
酒同样是周朝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写晋、齐两国国君行投壶之礼,晋之大夫荀吴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齐侯说:“有酒如渑,有肉如陵。”这说明他们何尝不希望有酒池肉林。历史上曾经专门谴责殷人沉湎于酒,其实是不公平的。
古代的文士中有很多贪杯豪饮的人,“不胜杯杓”者寥寥。他们不但喝酒,而且写酒、歌颂酒,好像酒以及有关酒的题材,真的能够浇其胸中块垒、启其神妙文思,酒几乎成了古代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
古代作品中所描述的喝酒情况,有的很吓人。例如樊哙在鸿门宴上立饮斗卮酒,而且表示还能再喝;唐代的王绩号称斗酒博士:他能每天喝一斗酒;宋代的曹翰酒量更大,喝了好几斗酒后仍然十分清醒。与这些人相比,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过景阳冈之前一饮十八碗,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其实古人之所以能喝这么多酒,奥秘在于古代的酒并不是烈性的。
古代的酒一般都是黍、秫煮烂后加上酒母酿成的,成酒的过程很短,而且没有经过蒸馏,其所含酒精量远远不能跟“老窖”、“陈酿”、“二锅头”比。陶潜《和郭主簿》之一:“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杜甫《羌村三首》:“赖知禾黍熟,已觉糟床注。”“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这些诗句,不但告诉了我们造酒的原料,而且还说明酒是诗人或农民自酿自饮的。
烈性酒在我国出现得较晚,至早不过南宋。淡酒也有浓烈程度的不同。酿造一宿即成的叫酤,也叫醴,其味甜。现在的糯米甜酒、醪糟即与醴相似,不同的是原料,今之醪糟系用黏稻,古代则不一定。历时较长、经多次酿制加工的酒叫酎。 比醪、酎更烈的酒叫醲、醇。
酒酿成时汁与渣滓混在一起,是混浊的,若经过过滤,除去渣滓,就清澈了,所以古人常说浊酒、清酒。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杜甫《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显然,浊酒是较低级的酒。
古代的酒也有糯米做的,当糟滓未经滤出时,即泛出白色,因而浊酒又称白酒。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陇西行》:“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现在上海人喝的白酒就还是古之浊酒,而在北方,白酒早已指烈性的烧酒了。
在古书中我们还可以见到酒变酸的记载,这在喝惯了烧酒的人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其实道理很简单:酒中杂质多,糖分多,放久了自然会变酸。《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但是因为家里养的狗太凶,没有人敢来光顾,因而“酒酸不售”。
最迟到唐代,酒的品种就很多了。王翰《凉州曲》中“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名句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了,而有些酒则只是在诗文中保留其名,而其酿制方法早已失传,甚至这些酒的味道、颜色等等特色也已无法考证。
陈设和起居
南北朝以前没有桌、椅、凳,而是坐在地上。坐时在地上铺张席子,所以说“席地而坐”。睡觉也在席子上面,所以又有“寝不安席”、“择席之病”的说法。稍讲究一点的,坐时在大席子上再铺一张小席,谓之重席。
古代室内设几。几为长方形,不高,类似现在北方的炕桌或小茶几。但作用却与炕桌等不同,主要是为坐时凭倚以稍休息。
古代室内有床,但与现代的床不同,较矮,较小,主要是供人坐的。从东汉末年起出现了一种“胡床”,大约是北方游牧民族为迁徙方便而创制的,中原地区在民族交往中引进,因为跟中原所习用的床有同有异,所以加胡字以示区别。胡床的床面系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可以折起,类似今天的马扎,所以又称绳床、校椅。因为胡床轻巧便于搬动,所以常常移至室外使用。后来的木质交椅、今之折叠椅、凳,即由胡床发展而来。古书上还常提到榻。榻跟床差不多,可坐,可卧。
我们曾经多次谈到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坐的姿势又是怎样的呢?
古人坐时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现在韩国、日本还保留着这种坐法。因膝盖着地,所以管宁的木榻“当膝处皆穿”。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长跪,又叫跽。这是将要站起身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
古人还有一种“不规矩”的坐法,叫箕踞,或单称箕或踞。其姿势为两腿平伸,上身与腿成直角,形似簸箕。有他人在而箕踞,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
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因为奥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
乘车的礼俗
上古乘车是站着的。《礼记·曲礼上》:“妇人不立乘。”可见男子一般都立乘。乘车的位置是舆的前部、轼木之后。御车者把辔汇总分握在两手中。六辔合在一手还要四马协力疾奔,辔虽不再“如组”,但仍要极高的技术。
赶马的竹杖叫策,皮条的叫鞭。古人十分重视驭马的技术。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设有“御”这一科。《左传》记述战争,总要交待交战双方主将的御手是谁和是怎样选定的。这在以车为交通、作战的主要工具,而路面、车体的条件都还较原始的时代,是极必要的。
古人对御车有一整套严格的要求,这还不包括上车、执辔、站立的姿势等。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是人们在狩猎、作战、旅行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要领,目的是为保证车的速度、安全和效率。古代的统治者还从驭马的方法中,悟出了对人民的统治术。例如《吕氏春秋·审分览·审分》:“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韩诗外传》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又《孔丛子》卷二:“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这些比喻,体现的都是儒家以礼治民的思想,虽然反对只以酷烈的刑罚进行统治,但把民比作马牛,却是与其他治民学说无别的。
古代乘车,一般是一车三人。三人的位次是:尊者在左,御者在中,车右在右。如果车中尊者是国君或主帅,则居于当中,御者在左。
(摘自《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版》,中华书局2013年4月版,定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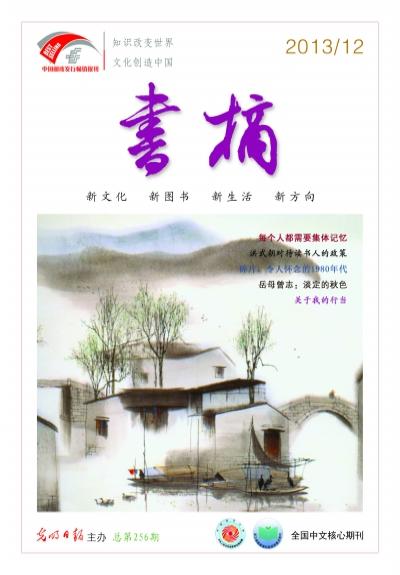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