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于光远先生走了……
回想起来,自2006年春收到于老给我的那封电邮之后,便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了。
在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已有不止一位像于老这样的我所敬重的老作者,随着自然规律渐渐远去……期间,惦念和伤感不时会在我的心中交替着。
而在这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也时常想起于老,想起那封电邮,但碍于工作和生活的颠簸,也是为了不打扰他的生活,一直没有主动与他联系。现在想来,终究还是很有些遗憾。
于老是《文汇读书周报》(以下简称“周报”)的老作者。如今我循着那封电邮,翻阅2005年的报纸:
2月11日,编发于老的书评《读〈上海巨商黄楚九〉》。文中透露,“我本姓郁,我的家族是上海土著。我的祖父的祖父弟兄俩,鸦片战争以前就从今天的上海郊区乡下到了上海城里经商。兄长成了上海首富,是名副其实的上海巨商。弟弟也就是我的祖父的祖父,给他的哥哥打工。我的祖父的祖父的哥哥富了两代人,黄楚九和胡雪岩都只富了一代。”我想起于老当时曾在电话中对我说,他想再写些与上海有关的往事。
8月,于老致信周报:
我正在写《我的治学方法一百条》文稿,其中有一篇《当敬一事师一理师》,现在寄给你们,你们看看是否可以发表。另外,我又写了一篇《关于读〈论语〉的一点感想》,它可以看作是给《文汇读书周报》的读者提出的一个问题,请他们思考。它并不是什么论文,什么成熟的想法,我倒是很愿意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给我一个反馈。
9月2日,周报将于老信中提到的两篇文章以“于光远治学随感(二则)”为题刊出,同时刊登了于老的来信。在《关于读〈论语〉的一点感想》中,于老对周报有个“定位”,至今看来仍然值得玩味——他说:“你们这家报纸是以读书为任务的。”
10月,于老“一口气看完了”周报刊载的《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后,致信编辑部说:文章“写得非常之好……劳你们代我向两位(作者)表示感谢与祝贺”,并随信“投寄一篇旧稿《勤学好思的胡耀邦》给你们……我想这个题目对你们的报纸比较合适”。由此可见周报作者与编者之间的某种“默契”。
11月2日,《勤学好思的胡耀邦》见报;同月25日,周报获得独家授权,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付印之际,破天荒地以5个整版率先刊发了该书第一章《永远的沉默》及作者满妹撰写的《后记》。
上述于老给我的那封电邮,便与这一长篇书摘有关:
昨天仔细地阅读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
我把你们2005年11月25日第1083号的报纸加以对比,发现你们独家首发的长文,有独立的价值。而北京出版社出的书有它的缺点,比如你们的报纸的第二版有胡耀邦给我的那首《渔家傲》,多少透露了些批判胡耀邦生活会的消息。而在北京出版社出的书就一个影子都没有。因此我建议《文汇读书周报》能否把你们刊物上的这五个版的内容单独出版。能够公开最好,否则内部印一下也就能留下一个历史记录。因此,本月11日就想和你联系,今天早上打电话,你又外出。一想不如用书面的形式,同你商量。你们看怎么样?有什么要我做的事情,尽管向我提出。
电邮写于4月12日,也是有些料峭的春天。回复前,我找出那期报纸,重读了于老电邮中提到的那段与《渔家傲》相关的文字:
……
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我常想,父亲这一代人,可能是由于年轻时生活环境恶劣和长期紧张的工作,很多人虽然活了一辈子,却只会工作,不会生活。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转移注意力的小块文章,如获至宝,回家和父亲闲聊时说:你几年前建议离退休干部休息后,写写回忆录、练练书法或绘画,还可以学点儿养生之道。没想到这些居然和报纸上科普文章宣传的观点很接近,只是科普文章中介绍的内容更广泛一点儿。看到父亲还在听,我就装着随意地接着说,报纸上讲了四点:发泄;倾诉;换环境,如外出一段时间;或学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像什么写诗啦,绘画啦。
不知道父亲是否受了这篇短文的影响,有段时间他竟学着做起诗词来。父亲曾写了一首词《戏赠(于)光远同志 调寄渔家傲》,幽默诙谐地调侃了教条主义: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
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牵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
浊酒一杯信天游。
回想编发此稿时读到这首《渔家傲》,我看到的也是“幽默诙谐”;而据于老电邮,这首词的内涵显然不止于此。既然不止于“幽默诙谐”,付印时再作“微调”也该是“合乎常理”的。
于老的想法我能理解,但一则周报以五个整版破例刊发已实属不易,再则当时我的岗位也已变动,不再主持工作。于是我回复说“目前看来很难实施”,并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岗位变动情况……想来于老接此邮件或有失望,但终究还是明白的。
也因此,胡耀邦的这首《渔家傲》便成了我的“心结”,我也开始关注起这首词来。
今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4周年之际,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了周瑞金和邓伟志怀念胡耀邦的两篇文章,其中邓伟志的文章标题即出自这首《渔家傲》:“你骑马来我牵牛”。文中写道:“1988年底,我有幸在于光远同志家中看到耀邦同志写的《戏赠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的手迹……耀邦同志这首词是戏中有戏,戏中有不戏。是的,‘你骑马来我牵牛’,牵牛的与骑马的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
6月,《书摘》杂志刊出于老的《告别胡耀邦》,其中一段文字终于让我明白于老为何特别看重这首词的原因了。
又过了一个月,胡德平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有胡耀邦用毛笔写的几个字:“德平或安黎转于光远同志。只有一张纸,别无他文。如于不在家,可暂不送。八日于天津。”信未封口,抽出来一看,上面写的原来是一首词,前面写了“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
词意一看也就明白。他对有些事情有牢骚,不过讲得还比较含蓄。他既然是戏赠给我,我也就不去深究这首词的含意,不去琢磨他写这首词时心里想的都是哪些事,那时他有哪些甜酸苦涩又怎样牵着牛和那些骑着高头大马的人争自由了。我信奉“喜喜哲学”,我希望耀邦在当时的处境下尽可能过得快乐些。看到他写的这首词有一定程度的游戏之意,我想他写时的心情总还是可以的,也就放心了不少。
至此,我终于弄清了这首词的来龙去脉,明白了这首词的“戏中有戏,戏中有不戏”。
读到于老的《告别胡耀邦》后,我又找出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当年拿到书,因为经手编发了其中的第一章,因此是直接从第二章读起的。此番重读,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于老电邮中所说的“一个影子都没有”的那段文字,一字不拉地印在我手上的那本书中……莫非是于老将书与报纸对比时疏忽了?莫非于老读到的不是我手上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
我很想找机会向于老询问,但一耽搁,于老竟已走了……
此刻我重读2005年约请于老为周报20周年撰写的题词:“能对社会进步起积极作用的思想和知识的传播以书为媒,而书本身又需要介绍推荐。尽心为书之媒的周报深受读者喜爱,过去这样,今后也一定这样。”感觉自己真该再做些什么了……
2013年10月7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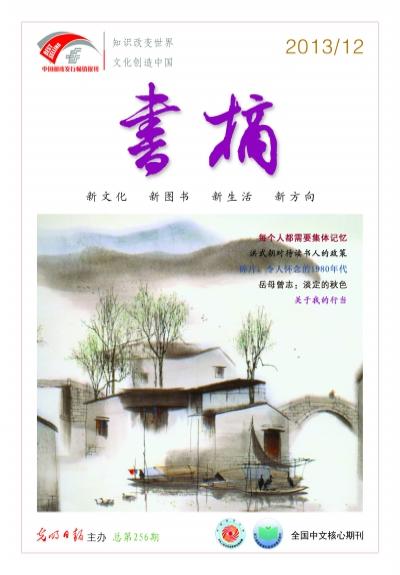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