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家里院里养什么花种什么草,似乎都有讲究,都有雅俗之分,这里说说我在这方面的一些亲闻亲历。
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祖母让我到花店买些草花籽。记得买回的有串红、喇叭花、牵牛花、鸡冠花、蝴蝶花、孔雀花、三色堇、百日红等等。回家后在北房东廊前,由祖母指挥,我挖了几条垄,埋下去,浇上水,似乎没多少日子,就长出一片姹紫嫣红。我和祖母都很高兴,祖父却不高兴了,说:“刨了!”问为什么,说:“太俗!”问种什么,祖父说:“芭蕉!我跟元方说了,从他那儿移。”
元方姓赵,蒙古人,清末大学士、军机大臣荣庆之后。他是银行家、藏书家,祖父的好友之一。他家住西城翠花街,宅子横跨两条胡同,非常大,宅有园林之胜。果然没过多少日子,芭蕉就来了。高高壮壮的树干,硕硕大大的叶子,黄黄绿绿的颜色,带来一派南国风光。夏夜听雨打芭蕉,清寂幽远,与李清照词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境界很相似。
赵元方又送了祖父两只荷花缸,一大一小,大的直径一米左右,整块大青石雕凿而成,缸身遍布花卉图案,由三个重重的石墩架着。荷花粉嫩娇艳,绿叶托着,有一种雍容典雅的姿态。秋雨入池,夜涨无声,李商隐“巴山夜雨涨秋池”约略近之。
能散发香气的花,祖父最喜欢的是南方的米兰。深绿色的叶丛中,点缀着米粒般大小的金黄色小花,香气幽深淡远。而且米兰有个特点,越是近前闻,越闻不见。有点儿距离,就有幽香暗来。仿佛它在教人不要心浮气躁地乱闻,而是气定神闲的安坐等待。其次是北方的茉莉。万绿丛中白花似雪,花朵饱满,花香馥郁。放进茶叶筒,香气永远不散。再就是金银花。金银花是蔓生植物,盛开时十分壮丽,满架绿叶之间,黄白两色花朵重重叠叠,香气随着晚风一阵又一阵飘出,满院子都是它的味道。而最可怕的是一种名叫“夜来香”的“香”,每当它夜间开始“工作”,就得赶快关窗闭门。因为那是一股强烈的带辛辣气的“怪香”,刺人口鼻,让人喘不上气。不知是谁种的,后来赶快刨了。
月季和昙花也为祖父所爱。祖父养月季,很注重品种,所种的月季颜色有红、黑、橙黄、蓝紫、绿白等等,外边很少见。但昙花更少见。家里有一盆昙花,但不是祖父养的,是别人送的。送来时,上边一共有四十九朵,估计就在当晚开放。祖父大喜,还请前院的街坊们来一同观看。昙花开放总在晚上九十点后,夜深人静之时,而且它倏忽而开,瞬间即落,所以几十年从不熬夜的祖父,也破天荒地看完了昙花从开放到凋落的全过程。昙花一现确实值得欣赏,紫色包衣打开后,白色大花徐徐绽放,又缓缓凋谢,整个过程庄严而肃穆。那种静静来悄悄去的从容气度,令人浮想联翩。尤其我家这盆有四十九朵之多,你开我落,此起彼伏,宛如一个盛大壮丽的舞台。
家里有两盆麦冬草,放在北屋正中廊下的台阶两侧,架在两个花墩上。麦冬草的形状和松枝类似,不过它是青绿色或翠绿色,结出的果实酷似一粒粒鲜艳的红豆。我曾问祖父,这是否就是他教我唐诗中“红豆生南国”中的红豆。祖父说,不是,但很像。
入秋以后,自然就是菊花。家里的菊花大概有十几盆,颜色有黄、白、紫、橙、粉、绿、墨等,且形态各异,没有重样儿。每逢这时,祖父总三天两头请朋友们来家赏菊饮酒吃螃蟹。但每逢这时,祖父却不喝他平时必喝的白酒,而是与客人们一齐喝烫得热热的黄酒。我还记得家里那时有两套喝黄酒用的杯子,每套12个,装在很漂亮的长方形盒子里。每个酒盅外边有一个四方形水注,为了往里注热水把酒盅烫热。酒盅上印着松树、梅花鹿、僧人等彩色图案,我曾想拿走两个当玩具,大人没给。
入冬以后,花草凋零,但是有两样祖父培养的花卉恰在此时开放。首先是腊梅,这是看去一棵枝干虬曲的老树,每到年底,就开出满树娇小的黄色花朵,散发出阵阵香气,极其清幽。每当这时,祖父总招呼家人都来欣赏。腊梅花开春前,多在瑞雪飘飘之时,故古人有踏雪寻梅之说。
若说“岁寒三友”松竹梅,家里靠西墙倒是种着竹子,先是密密麻麻一长排,再后来变成重重叠叠一大片。黄昏斜照,夜空月辉,每每将竹影映射得万般迷离,如至幻境。
松树都种在墓地周围,不能种家里。好在家里有两个盆景松树,算是凑成了“岁寒三友”。
其次是水仙。水仙似乎被文人们称为“案头清供”。最好的产地是福建漳州,祖父的学生们每年都会送几头来。我小时候,水仙没长成时,我觉得它像一头蒜,长成后,我看它又像两棵葱。所以我不明白祖父为什么要用一个非常漂亮的以后才懂得是雍正胭脂水色水盂把它供到书案上,且不时对人赞赏它。
我觉得在祖父看来,凡是那些好活好养好摆弄的花草,都俗。他尤其不喜欢石榴树。可北京的胡同院落里,种石榴树很普遍。我也曾想种棵石榴,祖父不同意。问原因,说:“俗。”怎么俗?说,“颜色不正。”顺着祖父的想法,我发现石榴的颜色果然不正,它说红不红,说黄不黄,还有点怯。这也许就是祖父和他的朋友们评花时所说“颜色不正”或“花色太乱”的原因。
祖母对花草则采实用的态度。在祖母看来,指甲草,可以染指甲;白凤仙,可以治脚气;茉莉,可以泡茶;荷叶,可以熬粥;金银花,可以泡水喝,去上焦火等等。祖母也会美化,比如祖母嫌葡萄架满架绿叶太单调,便沿架种了爬蔓的鸟萝,开出的粉红色小花很娇媚,但又被祖父认为俗。
我那时还小,只干两件事,一件是卖力气当“花匠”,刨沟浇水搬盆运土;另一件是玩耍。院子里真是聚集着无数生命:葡萄架下,马蜂;池边,蜻蜓;花间,蝴蝶;树上,腻虫。夜间还有萤火虫。对那些五彩缤纷的花朵,我也有自己的喜好。记忆最深的是麦冬草前边的地上,有一簇荷包牡丹。开放时,浓浓的绿叶之间悬挂着一个个荷包似的纷色花朵,与电影中看来的女孩子送给男孩子定情的荷包一般无二。尤其那种粉嫩嫩娇滴滴的颜色,非常令人喜爱。 听说是多年前祖母种下的。祖父又说它俗,但我力争保留,终于免去它的灭顶之灾。与祖父相反,我虽不讨厌名贵花木,却也深爱一般花草,甚至野草野花。这样的野花野草,家里墙跟下,旮旯里就有两种,二月兰和狗尾草。
二月兰是紫白色的野花,狗尾草是黄绿色的野草。它们不怕热不怕冷,不怕雨不怕风,不怕日照少,不怕土壤差。有土就能长,有缝就能钻。但它们花色寻常草色一般,又太多太普遍,就不受人重视。每年秋去冬来,我把那些只能在温室里越冬的花木往屋里搬时,又为留在院里怕冷的花草“穿靴戴帽”时,它们只是远远地望着。但它们在冬日漫天的风雪咆哮声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有人说,这俩,一个穷命,一个贱命。我却觉得它们像一对不离不弃的伴侣,意气昂扬的穷小子和穷姑娘。从某种意义上说,穷困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城市园林可能不把它们当回事,可你进到山野,漫山遍野的二月兰如海,坡顶崖下的狗尾草如浪,你也许就会感到美丽未必强大,强大才真正美丽。因而,我喜欢所有花草,因为它们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就像一现的昙花,生于恬淡,死于安宁;就像狗尾草二月兰,执著坚定,永不屈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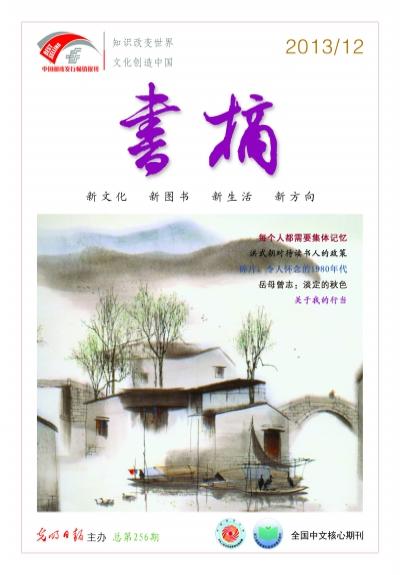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