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狗咬人”频发,近日甚至有藏獒咬死女童……淋漓的鲜血中,我总会不由地想起来那条斑马线,想起那条闲庭信步的狗。
那是条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是我从单位回家下了公交车必要经过的。照理应该是行人优先的,且线的左侧路面上还有醒目的车辆减速标识,但车轮总是熟视无睹地呼啸而来,甚至喇叭声声辗过斑马线,扬长而去……
行人早就习惯了“一看二慢三通过”,知道在车轮面前,即便有法律法规保障,所谓的“行人优先”其实也是近乎虚拟的。血的事实告诉行人,被撞的事天天都有发生,更有被撞之后“为免后患”而被车轮活生生地反复辗死,甚或被车主“激情”的乱刀捅死的……法律固然可以主持公道,却不能复活生命,于是面对远远呼啸而来的车轮,行人只能站在斑马线一侧静静地等待——珍爱生命,让车轮优先通过。
一天黄昏,我看见一只小狗从等待的人丛中脱颖而出,沿着斑马线向对面走去,不紧不慢,让人想起“胜似闲庭信步”……但,呼啸而来的车轮在斑马线前戛然而止了。
那一刻,等待的行人(包括狗的主人)和呼啸而来的车主,无数双目光齐刷刷地尾随着闲庭信步的小狗……四周出奇地安静。
直到小狗走完斑马线,车轮滚滚而去,我随着行人开始通过斑马线时,才猛然发现,那条闲庭信步的狗,就在那一刻,改变了我对狗的偏见。
我不喜欢狗,很有些根深蒂固,大概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每每听到狗叫,总会想起他那句“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仿佛天下的狗都是赵家的,虽然我清楚地知道那绝不可能——即便是狗,也不能随便姓赵的。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的心中,“狗”确实不过是“赵家的狗”的简称。这里不妨引1995年7月1日撰写的《想到了狗》以证:
前夜,睡梦中忽被邻家的一阵狗叫惊醒,或者是恰好醒来便听到了那阵狂吠,总之就此再也没有睡着。睁眼看着黑漆漆的墙,于是想到了狗,狗叫,“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记忆中,狗除了看门、狩猎等功用外,在文化的层面上多半缺乏褒义的成分,诸如为虎作伥的走狗,无需哀其不幸的丧家狗,摇尾乞怜的哈巴狗,史有前例的狗崽子,等等。而中国成语则更是将狗贬得几乎一无是处,倘若狐群狗党、鸡鸣狗盗等还算不上是“狗身攻击”的话,那么一一数落狗头(军师)、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犬牙(鹰爪)、(狼心)狗肺、狗尾(续貂),甚至连狗皮(膏药)、狗屁(不通)之类也不放过,则可谓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描摹狗了。或有人认为不然,并举出“犬马之心”为证。其实那狗(马之)心终究不过是奴才之心,“封建”之后的人是断不该以“狗心”为褒义的。
然而,即便如此,狗如今还是风光了起来。黄昏遛狗正在成为都市一景。应运而生的狗市、狗食、狗书等等狗文化,简直让人觉得“狗眼看人”已经过时,当提防的倒是自己千万不要“人眼看狗”,因为这些被遛的狗本身多半与它们的大户主子一样,也是很有些身价的,尤其是那些拥有像汽车牌照一样难得的“户口”的狗们。
遛狗,狗仗人势—人仗狗势的六足散步。
也许,这话说得太刻薄了点,因为养狗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更不只是为了遛狗。虽然谁也不愿承认自己喜欢做奴才,但这世上毕竟总还有人需要奴才。孤家寡人的寂寞导致杯弓蛇影的恐惧,倘若拥有唯命是从的奴才(其实并不难找),那心里便可少许多寂寞恐惧,而狗实在不失为最最奴才的,或者说最最奴才的便也是最最狗的。
于是这都市里便多了许多的狗。它们外出遛达,灵敏的嗅觉几乎可把每个过往行人的体味辨析。或有遇上不快意的,便会本能地狂吠几声(向主子请示汇报),甚或朝目标直扑而去——据报道,仅上海、广州去年被狗咬伤的人便高达六万之众——平均每十分钟伤人一个。
狗很风光,狗患却也因此而生。因为狗“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狗之咬人正如狗改不了吃屎一样,因此要消除狗患,除了痛打之外别无办法——期待主子来烹走狗,那得以更多的人被狗咬为代价,且多半只是种虚妄,所以鲁迅先生断然不予狗以“费厄泼赖”,认为“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睁眼看着黑漆漆的墙,在不时的狗叫中一路想来,墙依旧还是黑漆漆的,于是感觉夏天的夜竟比白昼还长。
但那条闲庭信步的狗却让我对狗刮目相看,甚至不免有些敬重起来狗来。但继而又有些悲哀——正是那条狗,让行人,继而让人觉得“活着,还真不如一条狗”。这实在是很悲哀的。虽然我坚信“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但目睹车轮对狗的生命的尊重远甚于对人的生命的无视,终究是让人难以承受的。
感觉“活着,还真不如一条狗”,的确让人悲哀;但,是人,终究还是不愿像狗一样活着的,所以只能静静地在斑马线一侧等待,同时保持作为人的自由思想。
于是我写下上面这篇文章,以记录这段不如狗的生活的思想。
2013年7月1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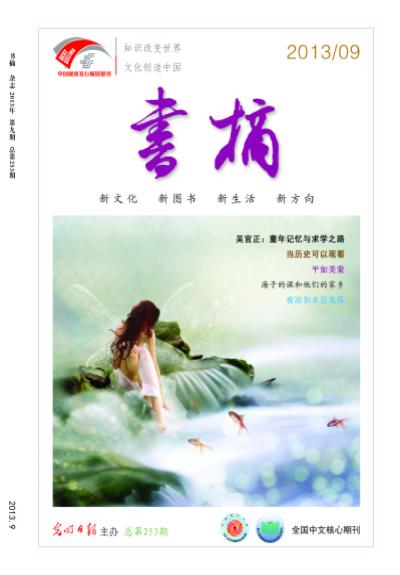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