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几个十年?更不可能有几个几十年。所以几十年后一个人总要回头看看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而这“走”,无论是波澜壮阔还是波澜起伏抑或是波澜不惊,都由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推动。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出于环境,对此我深有体会。回想过去,两种生活环境,对我影响最大。
一个环境是我十五岁到东北成为知识青年后。知青生活人们已耳熟能详,不必多说。但我要说的是我对其产生深刻印像的一位知青,他叫王家骥,哈尔滨人,比我大四五岁。他身材细高,容貌清秀,气质偏文。他从不打架,却能服众。喜欢看书,但不迂腐。爱好文艺,又不轻浮。说话不多,也不大爱笑,但要说,虽只三言两语,却能说到点子上,就有智谋。所以那些以打架骂人好勇斗狠为时尚的知青们,对他都很崇敬。我对他这种不怒而威的风度非常佩服。
我生在书香之家,对知青生活环境自然很不适应。一不会打架,二不会劳动,三不会家务,所以很“狼狈”。知青们也会起外号,送我一个“落难少爷”,挺风趣,也挺贴切。而他,却在我这“落难之时”,和我成了朋友。原因也简单,他喜欢看书,而书不多。我来东北时带了不少,他常向我借。我也愿意借他。他不像有些人还回来时书已成烂纸,或者干脆不还,更有些人拿去上了厕所,并由此铅中毒进了卫生所。他还回来的书总是干干净净,有时还给包个皮儿。我对历史和文学知道得较多,他常问我这方面的知识。他则有时给我讲些为人处世的经验,我常常听不大懂,他就说,没关系,慢慢就懂了。他认为我单纯幼稚,但常又反过来说,这样好,使我心里很迷惑。
我们认识一年多后,连里出了件大事,要说这事的发现者还是我。那时我跟马车,天天要饮马。有天到井边打水饮马,马死活不喝。后来发现水有味儿,疑心水里掉什么东西了。最后发觉水里泡着个死人,正是失踪多日连里的一个当地职工。连里知青们一听喝了好几天泡死人的水,一个个翻肠倒肚,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心想喝就喝了呗,人这辈子什么事赶不上啊!这时难题出来了,谁下井把尸体捞上来?平常这些仿佛打架不要命的人,这时纷纷往后退,没一个敢下井。这时王家骥自告奋勇下了井,把尸首捞了上来。这事当时“勇冠全连”,因为捞上来后发现这人脑袋被利斧劈开,面目狰狞。再一调查,原来是几个当地人挟私报复,一个晚上用斧子把他砍死后扔到了井里。
我和王家骥后来聊到这事时,我问:“你不害怕?”他说:“他活着时我都没怕过他,他死了我还怕?”我说:“这哪一样啊!死人多恐怖。” “再恐怖他也不会动了,你怎么摆布他怎么是。”他又笑笑说,“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我还要问,但他好像不大愿意继续这个话题,说:“以后你会明白。”
他曾对我说,从你那个家庭环境转换到现在这个环境,差距太大。但要适应现在也不难,关键是自己对自己得有个狠劲儿,不能怨天尤人。你有这个潜质,我看好你。
他说得对,从北京到东北,对我来说,生活环境天壤之别。我幼时家住一独立四合院,生活印象是:一、院子大,遍植花木,几无隙地;二、房子多,图书更多,处处皆书;三、人口少,祖父母、父母、我和妹妹,三代六口人。院子里整日寂无声息,我也没什么玩伴儿,除了看书,经常是一个人自己在院里玩。
所以我对鲁迅先生的百草园深有体会,对他幼年从百草园中所得到的乐趣更是感同身受。春天的杏花,夏天的马缨花,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一年四季装点着庭院。春夏之交,天空中蜻蜓、蝴蝶、蜜蜂、马蜂甚至还有牛蜂飞来飞去,它们透明的翅膀,摇曳的身姿和直上蓝天的背影,承载了我儿时许多遥远梦想。地上更是一个充满认知乐趣的园地。蚂蚁们跑来跑去,身上背着“如山”的米粒儿。土鳖们在墙角忙这忙那,蚯蚓们躲在花盆里,听说它们即使断成几节也照样生存。即将化蝶的大青虫软软地趴在树下,两只小猫一左一右,好奇地注视着它,不时用爪子拨弄一下。树上蝉鸣一片,却不妨臭大姐在树跟旁睡觉。毛毛虫在树上蹓跶,也无碍与它为邻的小小腻虫。还记得有回在院子中间的甬路上发现一条蚯蚓般的虫子,它正朝对面的土地花丛中爬去。可能它也觉得阳光暴晒一马平川的石头甬路将自己暴露无遗,内心恐惧,于是拼命扭动着身体,急急忙忙朝草深处爬去,让人心生怜悯。葡萄架下,马蜂安家;墙角旮旯,蜗牛倒挂。家里一只白猫,最爱扑蝶。虽然总看见它摩拳擦掌东奔西跑上窜下跳,可就没见它逮到过一只,反而总是见它失望地望着蝴蝶在它面前逗引似地越飞越高,冉冉而去。不过它倒敬业,“拿耗子”。但捕了后不吃,叼了直奔北屋祖母床下往上扔,弄得祖母床板“咚咚”响。玩死了,也不管了,跑出去玩儿了,害得我去把死耗子掏出来扔掉。难忘的是房檐下一窝出生不久的小燕子。大燕子一走,它们就拼命叫。有回我弄了个高凳,上去看看。小燕子虽然还睁不开眼,但也许感到气味不对,纷纷将头调转向里,屁股高高地撅向窝外,紧紧地挤成一团。等长大了,大燕子带它们学飞。大燕子一只在前,一只在后,四只小燕子居中。小燕子飞得依里歪斜,看着总像要掉下来。累了,它们就抓着院里晒衣物的铁丝休息。一段时间后,小燕子们终于学好了,于是全家一齐冲上高远的蓝天。
在这样环境长大的我,一旦进入“文化革命”那个抄家打人暴力血腥的时代,真是惊呆了。紧接着“登天”,即上山;“入地”,即下乡,更让人措手不及,“狼狈”也就很正常了。但是艰苦环境却真是锻炼人,尤其是王家骥下井捞尸后,我对他的话想了很多。人死了有什么可怕?活人难道就不可怕?我读过的书比他多,难道我就不能比他更勇敢?更成熟?
考验不久就来了。一天我们一群知青跟车拉沙子。开车的是个女司机,上海人,素以速度“疯狂”著称。果然半道儿上,她把一过路女青年给撞了。车停下来,得有人把女青年抱进驾驶室,好送医院。可车上这些平时爱打架刀子皮带不离手的知青,一见那女青年血拉呼嚓的样子,你推我,我推你,没人敢下去。后来我下了车,抱她进了驾驶室。女青年双目紧闭,身上到处是血,嘴唇一大口子,血顺着嘴,甚至从耳朵里往外流。我把背心撕了,学着电影里的样子给她包扎。安置好她后,我从医院里出来,遍身血污。回到连队,连里的人见我就问:“就你这文人,还会跟人打架哪?”
还有一回,我跟马车,途经一片草甸子。那时刚发过大水,有些坟被水冲开,白森森的死人骸骨随处可见。我让老板停了车,下去捡了个骷髅回来。我一路瞧着骷髅,心想人生就这么简单?生前欲望无数,死后一具枯骨,还不分贵贱。一路胡思乱想,居然无师自通地“通”了庄子的生死观。回到连队,拿进宿舍,本想让大家看看,没想到一宿舍人乱跑乱嚷,让我赶紧扔了。我于是到树林里挖坑把它埋了,还起了个小土堆。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王家骥,他少有的大笑,说这就是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原因。
岁月匆匆,半年以后,他上调到师部。我返城之前,去找过他,未遇。不久他来连队看我,我又出去了。从此断了联系。
回到北京,我又过上了庭院生活。但看到那些熟悉的几乎未变的景象,感觉却同从前大不一样。少时我只感到花草树木虫鱼飞鸟的外在形貌,眼下却想得很多、很远。明白了古人为什么说察一叶而知春秋,观滴水而知沧海。对我而言,这一叶和滴水的感觉就是,一、生活无限美好;二、生命没有高下;三、仁爱之心始自弱小;四、感恩天地敬谢自然。又有时,当思潮回溯到遥远的北方,陷入冥想中,便会觉得,严酷生活会使人内心变得强大,这强大的体现就是:你既不会打碎别人的脑袋,也不惧怕任何被打碎的脑袋。因此,我将永远怀抱梦想,从容走自己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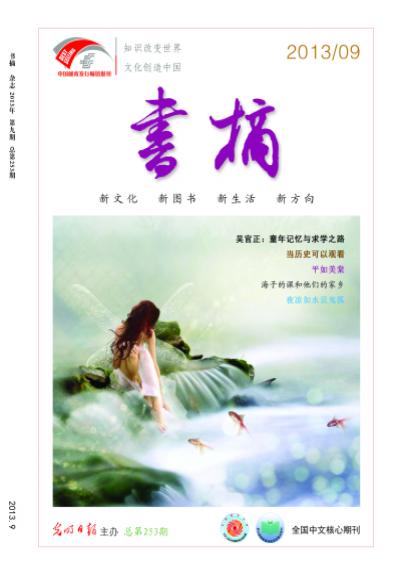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