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培养正见的正途不是听同一种人从同一个角度重复说同一种话,而是听不同的声音、冷僻的声音、遥远的声音。在这本书里,一个美国少年,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看我们习以为常的北京、中国。
我的曾祖父说过:
做选择时最重要的是勇气、同理心和责任心。
我曾从某本书上读到过这么一则运动规律,就是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影响之后发生的事情——球一旦动起来,跟着便会发生一系列预期的且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抛球、击球、发球完成后,后面可选择采取的动作就很有限了,而且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要不是在北京待的那一年,我一定会驳斥这条所谓的“运动规律”太过宿命论,而且是漏洞百出的。但是,经过那一年,我不再这么肯定了。有时,我最多愿意承认这条规律是基本正确的。
临时的家
穿过海关来到机场大厅,四处找寻着那个衣着得体的长发年轻中国女子,我父亲说她会举着一块写着我名字的牌子。维多利亚·毛是贵州省电视台的电视主播。她最近刚和她的艺术家男友到北京发展,但是还没能在电视台里找到电视记者的工作。我爸在去北京的某次旅行中面试过她,并认为她就是照顾我的合适人选。
这个苗条的年轻女子的确举着块写有我名字的告示牌走来了,却和我爸描述的并不一样,她留着一头短短的、黑色夹浅咖啡色的头发,身着紧身黑色牛仔裤,一件混色毛衣,穿一双橘棕相间的胶面网球鞋。她那时正举着一个粉色手机在耳边,所以把告示牌夹在了腋下,她伸出手来向我介绍自己。她说,她正给司机打电话,让他把车开进来。
于是我们就上了那辆据说是刘家的车,而刘家,就是我父亲为我安排暂住的那户人家。
我们在一系列建筑群中缓慢地穿行,包括一片被污染的河浜、一个小公园,最终便驶入了一扇在好几幢高楼下的大门。两个武装保安在入口处让我们停下。维多利亚向他们说明,我们是为了拜访刘家而来。我们等着其中一个保安打好电话,他朝我们招手,示意可以通过。
我下车见到了刘夫人。她穿着一袭海军蓝的宽松长裤和一件白色女装。她说着一口极流利的英语并且精力充沛。她带着我们到电梯前,告诉我们他们家在二十一楼。她还说我一定非常劳累困顿,需要休息。她快速地向维多利亚和我展示了一下他们宽敞的公寓,刘夫人解释说,他们买下了三套公寓并且全部打通了。客厅被刷成全白,里面零零散散地放置着一些中式家具和传统艺术品。在主卧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西式卫星电视,有一间屋子的正中央还有一只巨大的浴盆,浴盆是纯白色的,装饰金色天鹅造型的水龙头。对此我感到非常惊异。当维多利亚赞美起这房间的美轮美奂时,刘夫人笑着微微点头附议。我可以从维多利亚的沉默中觉出,她准是被这富丽堂皇的公寓给惊傻了。她从未预想过这一切是如此这般的奢侈,比如那个在房间正中精雕细琢的浴盆。
刘夫人带我们来到饭厅,呼唤一名保姆给我们上茶。她分发给大家一小碗用玻璃纸包好的坚果。眼前的小碗和细致的包装让我意识到,我可不能再像万圣节时带着我的两个小弟弟,玩“招待还是捣蛋”时表现的那样。在出发到中国的前几天,我帮着他俩从网上订购了罗马武士的道具服。我啜了一小口茶,发现茶是绿色的,并且带有甘草汁一样的味道。刘夫人对我的表情不禁捧腹,随即递了一小碗糖包给我。我拿了四包。
刘夫人对我们解释说出于安全原因,以后我必须待在公寓里,等维多利亚来,才可外出。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任何情形都不得独自外出。
“那样就太危险了。”她说。
她还说他们自己也仅有一把公寓钥匙,由他们的贴身保镖掌管。这把钥匙从来不离开这栋屋子,除非是他们举家出门度假,会由刘先生带着它。“他们很容易做出复制品,”她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一把钥匙的原因。”
后来我待在北京的那些个日子里,从来也没能真正分清是否有危险存在,抑或只是他们的恐惧和妄想偏执造成的错觉。我也从未听闻有关绑架或者抢劫的新闻发生,当然我无法确定那究竟是没有发生,还是没被报道出来。
刘夫人随后对维多利亚说,我们可以借用他们四个司机中的其中一个。吴师傅会腾出空来送我早上上学,下午打网球。她说她和我爸已经达成共识,这些规矩无论如何不可以被更改。
当刘夫人需要找什么人或者办什么事的话,她就会拍拍手掌,然后一个保姆就会立即出现。我们喝完茶后,她便让她的孩子们出来见我们。大卫只有十岁,莉莉七岁。大卫跑到我们面前,举着一个任天堂NDS在面前,仿佛在操纵方向盘。刘夫人笑起来,“大卫去哪儿都不能没有他的任天堂。”我问大卫是否喜欢打网球。他耸耸肩。“那英式足球怎么样,我是说,足球。”我边想着他是否习惯于英式英语,边改口问道。“大卫太爱玩电子游戏了,我正想着你可以带他多运动运动。”刘夫人边说边去看由保姆陪着的莉莉。莉莉穿着一袭银色和粉色的公主裙套装,维多利亚弯下腰对她说“你好”,但莉莉却躲了起来。刘夫人企图让莉莉说话,但她只是把小脸更深地埋进了保姆的裙褶里。好一会儿才从保姆的制服后,伸出一只小手有气无力地挥动了几下。
刘夫人带着我回到厨房,表示如果家里没有人,依然希望我能自己随意拿取。她还带我参观了几个保姆住的屋子。“你可以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帮你做事。”刘夫人说。
刘夫人最后带我去我的房间。那是一个狭长的类似公寓楼员工区域的地方,有着窄窄的高窗,看出去是一个小小的、乱糟糟的公园。我对刘夫人说我并不希望占用任何一个女佣的屋子。她连连说道,不不,这个绝对是客卧。我并不非常相信她的话,但是我也做不了什么。谢过她之后,我便开始拆开我那粗呢布包,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我的网球包,以备网球队第二天的试练。我脱下鞋,躺到床上,对自己暗暗保证说,几分钟后我就起床刷牙,上床睡觉。除了几个短小的盹儿,我几乎二十四小时没合过眼了。
游览故宫
刘先生为我和爸爸组织了一个小旅行团游览故宫。但因为爸爸周一要在纽约开一个会,必须周日下午飞回美国。他告诉我可以和维多利亚一起去。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维多利亚建议先去喝一杯咖啡。
“去哪儿?”
“跟我走。”她笑笑,走进了一个广场,那里挤满了等待大巴的游客。在拐角的墙根下有一座小屋子,装修成了星巴克店铺。那屋子分明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古典样式。我诧异地看着,“星巴克?星巴克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维多利亚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点了点头,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和一块月饼——一种小巧的圆形蛋糕,吃上去像杏仁软糖和海绵蛋糕的混合体。维多利亚要了一杯拿铁。我一边看着咖啡师摆弄咖啡机,一边重复了刚才的问题:“星巴克怎么开到这里来了?”
“刚开张。”
“不不,我是说他们怎么能允许这种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表进到古典的紫禁城里来的?”
“哦,这很好理解,”她说,“他们邀请星巴克的,因为需要赚取资金来修缮故宫。”
“但这不是当年的古建筑吗?”
“对啊,”维多利亚说,“故宫是明清两朝皇宫。”
她明显没有对星巴克出现在故宫感到有什么困扰,她觉得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侵犯,不如说是一种解决资金问题的有效办法。维多利亚指着房子边一块蓝底镶着红色边框的牌子,她指着两排三行字的指示。第一排是写的:乾清门。我不认识第二排字,和中文比起来更像是阿拉伯文。维多利亚在我问出问题之前就回答了我,那牌子上写的是汉语和满语: “乾清门”。
“你认识满语?”
“一丁点,我的爸爸是满人,我的母亲是汉人。”
“所以你是满汉混血?”
“对,不过我户口本上写的是汉族。”
我读到过关于汉朝的资料,那是一个持续了四百多年的王朝,跨越了公元元年前后。在汉朝期间,中国的疆域、财力和国力都与当时欧洲的罗马帝国相当。
我不知道身为汉族意味着什么,似乎可以说是一个涵盖各种不同人群的泛泛之词。可能它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它作为大多数人血脉的源头,代表着中国文明的一个巅峰。我爸爸总是说,当你想要了解中国的时候,他说当前最重要的前二十条问题都是如何保持国内和平稳定。每当要分析中国的时候,永远要记得这一点。中国就像一艘巨大的战舰,没办法轻易地改变航向。不管做什么都要放慢速度,三思而后行。因为几乎没有可以犯错误的余地。
我们沿着故宫城墙来到了东门。一辆茶色车窗的SUV正咆哮着停下来。刘先生下车了,一边打着电话,身边还陪着一名叫程先生的人。刘先生刚刚得知我爸爸不能来,尽管他显得很慷慨,但我看得出他被什么事情惹得不开心了,也许是因为爸爸临时取消行程所致。显然他组织这次小旅游是想和我爸爸套套近乎。
我们登上SUV,宫门也为我们打开了。开过一条护城河,维多利亚向我解释说我们这是在皇帝和妃子们的住所。程先生找到了一位在故宫工作的人,他带着我们走过一堵足有20尺高的墙,没有窗户。我们走过一连串被铁链锁住的巨大木门。走了大概有四个街区那么远,然后拐上了一条比刚刚窄一半的小巷子。又走了200英尺,我们停在了一道门前面。程先生从一串巨大的铁钥匙里翻找出一把,打开了大门,让我们跨过木门槛进去。
围墙里是一座凋零的宫殿,杂草丛生,坏掉的长椅被扔在两棵老树周围,好像刚刚有一场飓风从这里刮过。他带领我们走到宫殿门前,这座宫殿曾经上过红色、黄色、蓝色和金色的漆,如今都已经销蚀得差不多了。油漆大块大块地剥落下来,一块六英寸大的檐口倒在地上。宫门没有上锁,但他花了一番力气才把它打开来。
他和刘先生说了几句中文,维多利亚翻译给我听,“已经很久没有人到这里来了。”他用身子几下把门撞开,里面没有灯。所有的东西上面都盖了一层灰尘,好像这栋建筑一直矗立在火山灰里一样。一尊灰蒙蒙的佛像和六尊罗汉在入口面对着我们。我问刘先生上次有人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他耸耸肩问我们的导游。导游说可能自从溥仪1924年搬走以后就没有人来过。
离大门五六尺开外的东西就很难看清楚了。家具都堆在屋内,除了门口这一块以外里面连转身的空间都很小。这让人感觉是有什么灾难发生,人们都仓皇逃走。我们越往里走就越有一股沉香的味道,我感觉像是呼吸着那些逃走的人留下的尘埃。大约一百年前,这座宫殿曾住有上千个人,每一个都因为其在国家机器里的职务而受到各种行为自由的限制。现在宫殿荒废了。我还记得博伟(作者在北京时候的网球队同学之一)把历史比喻成一个还没有痊愈的伤口。好像在他的文化里,感伤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中国人总是接受现实并向前看。我猜他们也没有从感情上抹除历史留下的痕迹,只是去习惯它。
导游带着我们继续走,穿过门的一个小院子,曾经是某个妃子的寝宫。屋前有一棵树,维多利亚在那儿跪着拾种子。她和我解释说这是神树的种子,你要是把它种起来就会交好运。导游也跪了下来:“这是菩提树,佛陀就是在菩提树下圆寂的。”
导游把满满一把种子装进口袋,然后起身向刘先生和维多利亚说,他想带我们去一个不对外人开放的地方。于是我们跟着他走上了另一条小巷子。这些宫墙都太高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宫中是怎么能不迷路的。到处看上去都差不多,也没有路牌可以指明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沿着巷子走了有一个足球场的距离,然后看着导游将钥匙插进一把巨大的锁。我惊异,他总是一下就能找到正确的钥匙。他推开门,示意我们先进。这是一栋矗立在一片巨大空地上的小楼,草坪被精心打理过,植物简单而优美。
我们走进屋子,房间里只有几样简洁的中式家具,沿着墙有一排玻璃柜子展示着一些陶器。大卫和维多利亚赞叹着它们,导游双手抱在胸前,站在屋子中央。然后我们来到一间侧室,看上去像是餐厅。家具一样简洁,只有一张圆桌和八张椅子。刘先生看到这些家具的时候显得很兴奋,“这样配对的明代桌椅已经很难找到了。”
程先生带着我们到另一间房间,那里展示了各个朝代的一些瓷器。导游逐一向我们介绍,它们都比较简洁,和西方的器皿不同。导游说,每一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御窑。皇帝驾崩的时候,窑就会被毁掉。每一个皇帝都有自己喜好的风格和工艺。某一任皇帝喜欢青釉,另一任则喜欢薄胎,还有皇帝喜欢细致的花纹。导游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上去像是铜质的碗,一个像是珐琅的,以及一只纯金的。
我们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刘先生停下来对我说:“紫禁城无穷无尽。”
逛潘家园
维多利亚说她能带我去一个贩卖战争旧货的市场。
“我们应该在六点之前到那里。”维多利亚说。
“六点,早上吗?”
“最好的东西只在早上摆出来,等到九点的时候所有好玩意儿都被拣走了。游客们等到下午才来。”我猜她比较习惯使用她的第二语言,但是维多利亚在每件事上都表现得很笃定,她讲英语的时候也无比自然。维多利亚提到了一家叫潘家园的大型集市。她告诉我,北京城规模最大而且最古老的大型集市就是那儿了。它就在东三环边上,离刘家的公寓不算很远,但我们到那里仍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即使是早上六点,北京都会堵车的。这个大型集市被成排成列的摊位覆盖着,显得非常大。除了给我弟弟找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东西以外,我告诉维多利亚我想给我妈妈带点东西。
“你妈妈喜欢什么东西呢?”
“我真的不知道。”
“衣服吗,还是珠宝?”
“也许是一个小盘子,或者一只碗。反正是一些小东西。”
“那我们到集市边缘逛逛。在那里我们会找到很多很棒的东西。农民从乡下带来一些东西兜售。”
此时,外面的天还是黑的。维多利亚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手电筒。“这里走。”她说。她领我走到出口附近,瓷器,陶器,皮革,牛铃铛,硬皮钱包,甚至还有老旧的木质洗衣板,这些杂七杂八的收藏品都被随意地摆放在几片又脏又破、不规整的布上。
“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假的,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东西。”
维多利亚用她的手电筒照着路。大多数小贩都蹲着,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他们就马上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些不值钱的廉价小饰品,然后告诉我们“真的真的很物超所值”。维多利亚赶走了他们。维多利亚把她的手电筒指向其中一块洗衣板上,一块长方形的木头上面有磨损了的花纹。“郭的父母过来这里,买了二十四块洗衣板回去收藏。一位美国收藏家花了大价钱才买下它们。”
维多利亚在一个货摊前停下来,摊子上摆着一套形状不同,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圆形的小碟子。上面画着深粉色的牡丹和亮绿色的叶子,摆放在一个破旧的天鹅绒盒子里。当我蹲下来的时候,摊主递给维多利亚一只绘成同样风格的笔筒。这跟以前我妈妈用来做花瓶的那只简直一模一样,所以我朝维多利亚点了点头。这个小贩明白了我要选择这只笔筒,但是他很不好说话。最后我用二百块人民币,折合美元大概三十元买下了这只笔筒。维多利亚觉得这太贵了,但是我对我买下的东西很满意。“下次的话,就先走开。你说不定可以花七十块买下它。”
我们顺着一排又一排的小摊走下去。有其他的顾客也开着手电筒在逛。这看起来好像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消失了的部落在地上遗留下来的踪迹。看完一排又一排的小摊贩卖的物品之后,终于,有不寻常的物品映入了我的眼帘。“别表现得很感兴趣,”维多利亚用英语跟我说,“你看到那个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了吗?”当她向毯子后面闪了一下她的手电筒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跟篮球差不多大小的东西。
跟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饰品和陶器瓷器的碎片摆在一起的,是一个一面有红星的绿色头盔,还有一副很大的望远镜。“这些是正规的望远镜。”我对维多利亚说。蹲在毯子后面的男人站起来,然后把它们递给我——镜片是红色的,很沉。我想知道这些望远镜曾经被用来观察过什么。外面天还是很黑,没法试看它们好用不好用。我又把它们递回去。他看见我一直在看那顶头盔,就拿起来塞给我。“你喜欢吧,便宜点给你。”我把那顶头盔放在手里摆弄。它很沉,但是看起来像是真家伙。他说:“看一看。”然后就自己用手比画了一下戴上它的样子。头盔上面有遮光板,我往上推了一下然后举到头顶戴在头上。我知道如果我把它买回去送给我的小弟弟,他会把我当英雄看待的。我把它摘下来,还给那个男人。维多利亚站到了我的前面。
“这个多少钱?”
“三百块。”
“太贵了!一百块!”
“这个真的是军用头盔,两百块!”
“一百五十块!”
“不可能!”
“那好吧,我们走了。”
“好吧!好吧!一百五就一百五!”
我问他这个是不是他的。他说是,后来又说不是。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答案。就算是他的又怎样呢?总之现在它已经易主,一个美国来的少年将会带回家送给他的小弟弟——同行的年轻女人把价格整整压了二十美金。
他把头盔装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扯住我的衬衫,示意我等一下。他抬起一个大纸箱,然后兴冲冲地在里面找,直到找到他想找的东西。他拿出一个红色绳子扎住的小硬纸板盒子,花了好大的工夫才把绳结解开。盒子里面是四枚勋章。我亲自检查其中的一枚。红色的那块,缎带很脏,皱皱巴巴,斑斑点点,勋章的光泽早已不再。
我问他,“这是你的吗?”
“是的,这是我父亲的。”
我接受了他给出的第一个价格。我觉得一个男人沦落到要贩卖他父亲在战争中获得的勋章的地步,那么他一定是处境困窘,如果这时我讲价的话看起来会很不道德的。当我们走开后,维多利亚告诉我,我多花了三倍的价钱。
我不喜欢这么计较。这个人远比我拥有的钱少,为了勉强度日无所不做。维多利亚对待这次讲价就好像是一场游戏,然而对于那个小贩,也许这会使生活变得艰辛。这让你开始思索金钱对于你的真正意义。如果你花三倍价钱买了一样东西,这对你真的有什么吗?但是这对这个男人真的有什么,如果一整天都没有人来买东西,这或许会帮到他。维多利亚听了哈哈大笑,“你真是有一颗柔软的心,这是好的,可是这是奢侈品我们消费不起。”
维多利亚带着我进入了更深邃的小巷。里面的小商贩显然和那些沿街躲在自己毛毯下的农民们不同。这些商贩无一例外地都在经营着一个杂乱无章,被各种冒牌货充斥的小店。他们都是职业高手,深谙其中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讨价还价规则。他们还分享好几种技巧,以便更好地出售自己的东西。首先,他们比起其他人,都会说一口不错的英语。其次,他们会投其所好,只挑你想听的说。任何疑问在这里,都变成了肯定的回答。比如,“这是真金的吗?”“绝对纯金。”“这个是古董吗?”“年代非常久远。”“这个还能用吗?”“可好用了。”他们往往假装成顾客,在自家摊位前挑挑拣拣,直到你过去东看西看,然后他们便伺机给你建议,买这买那。他们还往往会把价格设得很高,这样一来就可以在讨价还价中佯装降掉很多价,但最终还能以自己想好的价格成交。
我们在一家卖鞋子的小摊前面停了下来。维多利亚在给她的男友找一双GUCCI的网球鞋。维多利亚说一百块,那个男人说不行。她打手势示意我走开。他马上降低了价格卖到八十块。维多利亚说一百块两双。他递给她两双GUCCI网球鞋,她递给他一百块。
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到达入口处。在等吴师傅的时候,我看见有三个小男孩在一起玩耍。我推测他们的父母是在集市卖东西的。这三个我猜大概有八九岁的小男孩在玩不同版本的石头剪子布。他们面对面站着,然后一边蹦跳一边喊出“石头,剪子,布”三个词来,向下晃动他们的拳头。他们在一个不是很规则的圈里手舞足蹈,我看了几分钟。我问维多利亚这些小孩子为什么不在学校里上课。维多利亚说这些孩子可能是从乡村或者其他城市移居北京来找工作的人的孩子,没有拿到暂住证,可能没有送他们的小孩子去上学,维多利亚说在这待几年以后,这些务工人员有可能带着他们攒的钱回他们的村庄去。一个商店老板对小男孩们吼着什么,然后他们大笑着跑开了。
我给吴师傅看那顶头盔跟勋章。他把他的手伸出来翻看那顶头盔。“非常少见,成为一名飞行员非常难,要通过很多很多的测试。只有少部分人才能通过。最优秀的人才。”他钦佩地点点头。我给他看那些勋章。他解释说这是旧时中国国民党军队对勇者的嘉奖。他拿着那块勋章,小心翼翼地翻来弄去。他抬了几次头,然后用汉语说了些什么,我不是很能理解。我问维多利亚吴师傅说了什么。“他说,‘保管好这些东西,它们沾满勇气。’”
(摘自《美丽的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定价: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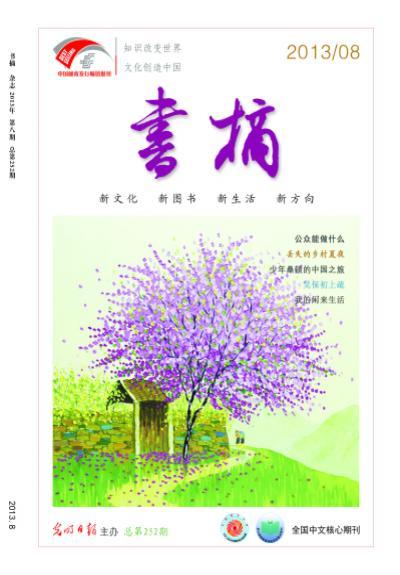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