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你在中国以写作为业,以分析、批评社会为职责,期待赢得对应的声誉与影响,你必定无法逃避韩寒带来的“影响的焦虑”。过去几年中,在一个日益破碎化的公共空间里,只有他的声音能打破种种壁垒,达致每个人耳边。他还以一种最漫不经心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写作者渴望的所有世俗赞赏——既赢得青春期读者,又是“全球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种焦虑不激发你,反而令人困惑。你会承认他的机智、俏皮,他的某种程度上的诚实与反叛,但决不会因为他的写作能力、思考深度、对世界的敏感、对责任的承担做出赞赏,在这些领域,他即使不是平庸不堪,也乏善可陈。与此同时,你的耳边充斥着对他的不遗余力的称赞,把他推向了思想领袖、时代英雄的高度,甚至你一向敬佩的、见多识广的朋友、标榜责任感的媒体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他们半赞叹半悲哀地说,“全中国大学教授的影响力也比不上韩寒”,只要这个赛车手一直写下去,就会写成这个时代的鲁迅。
在很多时代,都有流行一时的人物,他们似乎攫住了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占据了所有的注意力,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还记得乔治·奥威尔曾说起诗人豪斯曼。对于生活在1910至1925年的英国青年人来说,他影响甚巨。但不到几年,他们就发现昔日英雄的诗歌空洞、充斥着廉价的情感。不是豪斯曼的内在品质,而是当时英国社会的流行情绪造就了他。他符合那个时代反城市、爱乡村,亵渎神圣、反抗习俗的嘲讽情绪。如果豪斯曼的例证太遥远与生疏,汪国真是另一个例证。很少有人还记得,二十年前的他是多么风靡,他那些甜蜜蜜的小诗抚慰了遭遇重大时代挫败之后的青年人的心,新一代人忘记了艾青、北岛的传统,相信他理应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韩寒也被新的时代浪潮推到舆论的中心,这股趋势因为互联网,因为一个新型大众社会的出现,因为中国崛起的辽阔背景更为汹涌。他简单的内在价值,被迅速地扩大,最终获得了错位的意义。
因为人们谈论得太多了,我开始回避关于他的一切话题,这其中一定蕴涵了某种反感,此刻的中国有这么多重要的议题等待探讨,媒体与公众却孜孜不倦地把宝贵的注意力与热忱都给予这个青年人的一举一动、一篇博客文章,还认定自己是在谈论思想、批评社会弊端。这其中也该有某种愤愤不平,严肃的知识分子声音被遮蔽了,它不仅远离权力,又被大众遗忘。
在观看台湾的竞选时,我透过报纸知道了韩寒的三篇有关自由、民主、革命的博客文章,再度在中国引发了热烈讨论。我记得自己当时的不屑与失望,这样的命题本应由一些更富经验与思考的头脑提出,然后激起深入与广泛的讨论。我几乎可以想象韩寒引发的讨论方式,它必然是表态式的混乱。他的思考与风格适合于简单问题,是非已定,只需要他加上嘲讽的包装。而对于复杂问题,这毫不起作用。他的反智风格,更无法应对这种具有历史内涵的问题。
回到北京后,我发现这场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并被导向了新的方向。因为麦田、方舟子的加入,自由、民主、革命没人谈论了,人们正在分成两个队列,在韩寒是否存在代笔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我不上微博,没能直接感受这场时时刷新的争论的热烈程度。但在饭桌上、在聚会上、在随手翻开的报纸上,人们总在谈这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春节时一次家庭聚会中,一群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在热烈地争论韩寒,热烈地表态。这真是荒诞的一刻,他们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生,在思想激荡的八十年代成长,有的还在体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而在九十年代要么从商、要么回到学院,都自认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也都以自由派自居。他们的兴奋点也令我诧异。一位相信,不管韩寒是否有代笔,都应该把他放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看,他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韩寒代表进步、自由的声音,我们不能让这个声音受到攻击。第二位则完全沉醉于韩寒的影响力,她反复强调的是,该如何利用这影响力来教育新一代青年人,她的口吻像极了二十年代国共两党的“争夺青年”。而最为理性的一位把话题引回到三篇文章,她觉得韩寒太轻佻了,不够尊重前人的付出,也忽略了很多学理的因素。
这个下午的聚会,像是这场公共讨论的缩影,也象征它真正的悲哀所在。一个下午的时光,以大家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我们原本可以进行一场真正的谈话,陈述自己对各自领域的看法,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最近读到的新书,或是又看到哪种新理念。但我们把时间毫不吝惜地扔进了对一个并不复杂的青年人的无穷猜测与分析,引证不同人最新发布的博客,像是对一根早没有味道的甘蔗嚼了又嚼。
我相信,类似这样的下午,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群中发生着。我在其中最直接的感受是,每个人都受到规模与数量的诱惑,甚至被它压垮了。
门户网站、视频、微博,我们正目睹与感受着如此众多的人突然参与到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意见所形成的巨大浪潮,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它当然意味着巨大的进步。它鼓励了个人自由,也给予人们某种联结感,他们都曾因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被长久压抑。在很多事件上,它也形成新的压力,冲击了封闭的政治结构,促使迟缓的官僚系统做出改变。
但同时,它也正在凝结成令人不安的力量。将近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种舆论已经造就了一个亢奋、烦躁的公共空间,而且呈现日渐堕落的趋势。公共讨论的内涵消失殆尽,只剩下人们分成两个立场的表态,谁也没兴趣倾听对方,至于中间的声音,则再也听不到了,到处弥漫的是情绪性的释放,而非理性的分析。且不说围绕韩寒的争吵,其他更极端性的言论,从郎咸平、宋鸿兵到孔庆东,反而大获全胜。中国社会的舆论空间似乎已堕入了恶性循环——思想的浅薄与语言的粗鄙,彼此交替,而因为严肃思考与情感的缺席,庸俗文化则大行其道。
那么在此刻的中国呢?我仍相信,重新凝聚知识分子的共识并捍卫其内在价值是关键所在。过去十年,除去传统的制度限制,市场化与信息革命也促成了知识分子团体的瓦解与边缘化,很多人选择了自我放弃。
对于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既不能沉溺其中,也不能仅仅去批评它是闹剧。你可以切断微博与网络,却不可能隔离现实的生活。
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公共生活。一个社会最糟糕的状态不是它已经身陷粗俗,而是它沉湎其中,放弃从中摆脱出来的努力。重建的重任只能交给那些智力与情感上的真正精英之士,他们既抵制政治与市场权力的诱惑,也回避大众的诱惑。他们有着内在的价值观,提供社会的方向感,刺激你的庸常状态,提供新观念,在一片噪音中提供清晰、富有审美意义的声音,追寻更高的标准。
(摘自《时代的稻草人》,群言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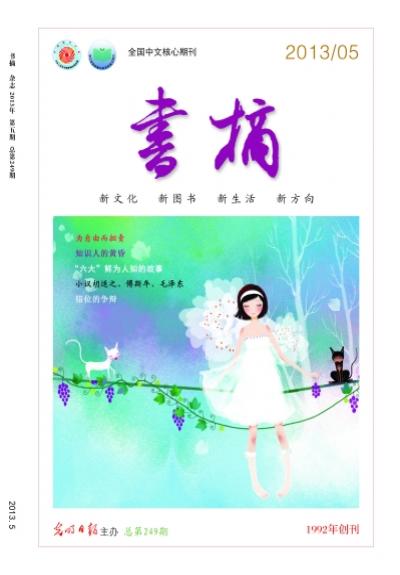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