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清晨,曙色微明,鸟儿在林木间低语,以神秘的节律和鸣,你是否觉得它们是在和伴侣谈论花呢?人类对花的爱恋想必伴随着爱情诗的诞生。花固有的甘美,沉静的芬芳,还有什么比它更能让人想到清新未染的灵魂展露呢?原始人向他的情人献上第一个花环,由此超越了兽性。他克服了粗野的本能,进而为人;他意识到了无用之物的微妙之用,于是进入了艺术之域。
欢乐抑或悲伤,花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饮食,歌舞,谈情说爱,都有花的陪伴。我们结婚、受洗,花都在我们身旁,就连死亡也离不了花。我们伴随百合礼拜,于莲花中冥想。我们带着玫瑰和菊花的徽记战斗。我们已经尝试用花语传情。没有花我们将如何生活?没有花朵存在的世界让人惊悚。病人的床头没有送去的鲜花,何来安慰?黑暗中疲倦的灵魂,哪有一线喜悦的光明?她们恬静的温柔恢复了我们对宇宙衰微的信念,恰如美丽的孩子专注的凝视唤醒了我们失去的希望。我们在尘土之下沉睡的时候,是花在我们的墓畔悲伤地流连。
令人悲哀的是,尽管花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并没有完全克服兽性。剥下羊皮我们的狼性会露出牙齿。有句俗语说,人10岁的时候是动物,30岁是失败者,40岁是骗子,50岁是罪犯。也许人成为罪犯是因为他永远没有摆脱动物本能。对我们来说,除了饥饿什么都不真实,除了我们的欲望什么都不神圣。圣殿在我们眼里一个接一个坍塌,但唯有一个神龛永存,在那里我们焚香膜拜至高的偶像——我们自己。我们的神何其伟大,金钱就是他的先知!我们掠夺自然为了向他供奉。我们自诩征服了物质,却忘掉物质也奴役了我们。以教养和风雅为名,我们什么恶行做不出来!
告诉我,温柔的花朵,星星的泪滴,向歌唱露珠和阳光的蜜蜂点头致意的时候,可曾想到等待你的可怕的厄运?趁你还在夏日的微风中,尽情地梦想,摇曳,嬉戏吧,明天一只冷酷的手会扼住你的咽喉。你会被折断,被一瓣一瓣地掰碎,与你安静的家园生生离别。那只手也许就属于一位路过的漂亮姑娘。她会说,多美的花呀,而此时,她的手指上正沾着你的鲜血。告诉我,难道这就是仁爱吗?也许这就是你的命运,囚于一位你认识的无情的女士的发辫,或者插在一位绅士的扣眼内——如果你是人,他决不敢正视你的脸。也许你会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容器中,只有些许的浊水稍微缓解你难止的干渴,而这干渴预示着你生命的退潮。
花儿啊,如果你生长在天皇的国度,你也许会在某个时候遇到一个拿着剪刀和小锯的可怕人物,他把自己称为花道大师。他宣称自己有医生的权利,所以你会本能地憎恨他,因为医生总是延长病人的痛苦。他会把你切断,拧弯、扭曲成他所认为适宜、而你从未设想过的奇形怪状。他会像正骨大夫一样扭曲你的肌肉,让你的骨头脱臼,会用通红的炭来灼烧你,为你止血;他会用铁丝插进你的身体,增强你的循环。他会让你喝盐、醋、明矾,有时候还有稀硫酸。如果你昏迷过去,他会给你的脚下浇开水。他会自吹自擂,因为他的治疗,你的生命比原来延长了两个星期甚至更长。难道你不觉得被摘下的那一刻就香销玉殒更好吗?你的前世究竟犯了什么罪,让你今天遭受这样的刑罚?
在西方社会,对花的奢靡浪费甚至比东方插花大师们对花的处理办法更让人震惊。在欧美,为了装饰舞厅和宴会的餐桌,今天采来明日就丢弃的鲜花不可胜数。如果把这些花朵串在一起,那可以环绕大陆做一个巨大的花环。相形于这种对生命莫大的漫不经心,东方插花大师的过失就不值一提了。至少,他尊重俭朴的自然之道,深思熟虑后选择自己的牺牲品,而且对花的遗骸报以敬意。而在西方,花的展示似乎是炫耀财富的一部分——出于一时豪兴的结果。豪奢的宴会结束后,这些花的下落在哪儿呢?没有比看到萎谢的鲜花被冷漠地扔到垃圾堆更让人惋惜的了。
为什么生得如此美丽的鲜花会如此不幸呢?昆虫有蜇人的刺,最温顺的兽类被追逐得走投无路时也会反击,长有华羽可以用来装点帽子的鸟能飞翔以逃避猎手,身覆大家垂涎的毛皮的野兽,会在你走近时隐遁。唉,除了蝴蝶这种有翅膀的花以外,所有的花在破坏者面前都无能为力。如果它们在垂死的创痛中惨叫,也不会到达我们无情的耳朵。我们总是残忍对待那些默默地爱我们,为我们服务的朋友,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因这冷酷而被最好的朋友抛弃。你难道没有注意到野花一年比一年稀少?也许它们中的智者告诉它们等到人们更有人性时才回来。也许它们移居到天堂去了。
培育花草树木的人理应得到赞赏。莳弄盆栽的人远比拿剪刀的人有人性。观察他们为水和日光操心,和寄生虫作战,因霜冻而犯愁,为迟迟不萌芽忧虑,为叶片泛出光泽而狂喜,是件赏心乐事。在东方,花卉栽培的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诗人们对心仪植物的痴恋,常被记载于故事和诗歌中。在唐宋,随着制陶业的发展,精美的插花容器出现了,它们不是一般的花瓶,而近似光彩夺目的宫殿。每一种花都由不同的人照料,并用柔软的兔毛刷子刷洗植物的叶子。有本书中写道,牡丹应由盛装的美女洗沐,腊梅则应为清瘦的僧人所浴。日本最为家喻户晓的一出能乐叫《盆景树》,写于足利时代,讲的是一个贫寒的武士,在冰冻的夜晚,因为没有足够的薪柴取暖来招待一位游僧,竟劈了自己心爱的植物。直到今天,这出剧目仍能赢得东京观众的眼泪。
养护华奢的花需要特别留心,唐玄宗为了惊走飞鸟,下令把小金铃挂在御花园的树枝上。春天他带着自己的宫廷乐师出游,演奏柔和的音乐取悦花朵。我们国家的亚瑟王传奇中的主人公源义经,曾写过一个奇妙的牌子,这块牌子仍然保留在我国的一个寺庙里。这是一个告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一株珍奇的梅树,引人注目的是它带有战争年代残忍的幽默。告示在描述梅花之美后说:“伐一枝断一指。”
但即使是把花种植在花钵里,我们也有自私的嫌疑。为什么要让植物远离原生的环境,在陌生的地方盛开呢?这难道不像把鸟关进笼子,强迫它唱歌交尾一样吗?有谁体谅兰花的心情呢?它们在你的温室中为人工的热气所窒息,无望地渴望能一览南方故土的天空。
理想的爱花者是那些在花的故土拜访花的人。像陶渊明,他坐在破旧的竹篱前与野菊交谈;或者像林和靖,黄昏时分漫步在西湖边的梅林,沉迷于梅花神秘的芳香。
但我们不能如此过度感伤。我们应该少放纵情感,多壮阔胸怀。老子说:“天地不仁。”弘法大师说:“生生生生暗生始,死死死死冥死终。”举目所向,毁灭无所不在。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皆然。唯有变化才是永恒——为什么只能乐生不能乐死呢?生与死表里一体,如梵天的夜与昼。
花决不似人间的懦夫,有些花为死而自豪——日本的樱花就是如此,当它们任风自由飘落之时。不管是谁,当他伫立在吉野或岚山满天飞舞的花雪前,一定会懂得这个道理。在那一瞬间,樱花像宝石镶嵌的云朵盘旋着,在水晶般的溪流上飞舞着,然后随着欢笑的水流奔向远方。它们仿佛在说:再见了,春天!我们正步入永恒。
(摘自《茶之书·“萃”的构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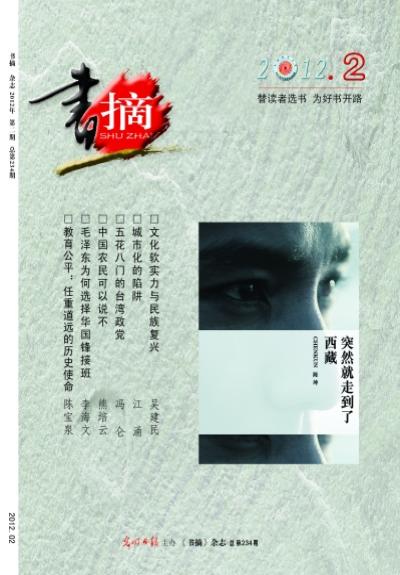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