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不敢奢望,总是有一种忧伤。这还不仅是对一种“文化所化之人”或者文化“托命之人”的人物的忧伤,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忧伤……
年初,搬到了圆明园东门外,与清华荷清苑只隔一条马路,于是常去清华园走走:走过了以朱自清《荷塘月色》一文著称的荷塘及自清亭,记得第一次读其名篇时,我还是一个“文革”时期的中学生,那时还不知道平淡的好处而竟对此文大失所望;也走过了早期写诗并埋于故纸堆、后期则以激烈著称、与政治发生关涉而竟遭暗杀的闻一多的纪念碑亭,还有同样早年埋于故纸堆、后来也和政治发生关涉,始则高位,后却自杀的吴晗的纪念碑亭。
这些纪念碑亭多是新修的、相当醒目,也标注在了清华校园的地图上。但我知道我的踯躅其实是暗暗地想寻找一块朴素的旧碑。这块旧碑以前虽然也拜访过,现在却一时不易找到,又不想问人,只在内心默默地希望着碰上。终于在一个薄暮时分,就在一块热闹地段后面的僻静处,又发现了它——清华于1928年6月初在王国维自沉一周年忌日(一说1929)所立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写,林志钧书丹,马衡纂额,梁思成设计。结尾斑驳的几句是:“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悼念追思王国维的诗文不止一篇,而是写过三次。他先在1927年6月写有七律挽诗一首,开头两句是“敢讲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继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并在“挽词序”中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而在之后的1934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又写道:“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陈寅恪这三次所写的数篇悼念追思王国维的文字既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又可说是夫子自道。而在这些文字中,都透出一种深深的忧伤。
在陈寅恪那里,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一种忧思,还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在他于欧美访学的时候,他就谈到过今后士人将无去处,不如尽早觅一职业谋生,甚至不妨经商。然而,他回国还是赶上了最后一段优待士人的平和时光,尽管他在西方多年,并不在意拿回一个“博士”学位,但还是被清华聘请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当时的清华国学院不仅有一种深厚的研学风气,也还有一种精神。据其时在读的蓝孟博回忆:“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又“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然而,在这精神的深处,的确又总还有一种隐隐的、排遣不掉的忧伤,尤其在几位导师那里。清华国学院其实仅持续了五六年,其盛期更短,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感人一幕。那感人的绝不止是精湛的学识,而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一种燃烧的东西,哪怕只是深处一点精神的爝焰,却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精魂。而这爝焰又有深厚的文化学术的包裹,不会是很快燃尽的“一腔热情”。
陈寅恪认为王氏所忧伤悴死的超越精神“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是的,这还不仅是对一种“文化所化之人”或者文化“托命之人”的人物的忧伤,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忧伤;这不仅是对一种即将衰落的文化的忧伤,而是对整个文化精神的忧伤。更有进者,我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夜在橄榄园的情景,可以感到一种信仰精神的忧伤;在康德所说“有思想的人感到忧伤”中,可以看到一种理性精神的忧伤。
一千六百多年之后,帕斯卡尔深切地感受到了耶稣在橄榄园中的忧伤,他似乎听见耶稣在对他说话:“我在自己的忧伤中思念着你。”他于此写道:“耶稣将会忧伤,一直到世界的终了。”
问题还在于:他们为什么忧伤?
(摘自《大家手笔》,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2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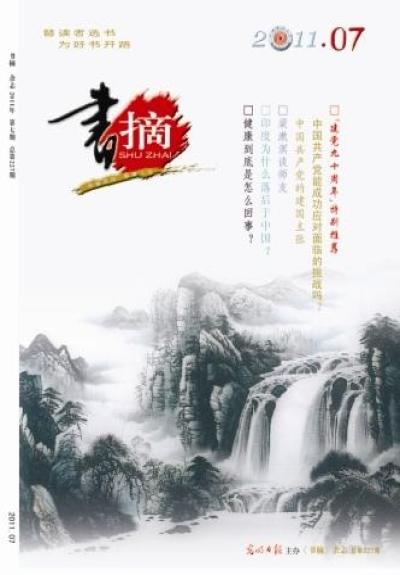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