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恐怕难以想象,若干年前的某些时期,在我们国家任何有关人性的讨论,都是一个禁忌。不要说正面讨论人性话题了,就连拐弯抹角的“文学是人学”这样的文章,都要被冠之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遭受全国范围之内的大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人们,没有一些关于人性的看法,但主要是阶级论的人性论。那就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坏的,他们的人性也是坏的,而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他们是好的,其人性也是好的。好便是绝对的好,坏便是绝对的坏。谁要是说工人阶级或者贫下中农也有缺点,那是很难的;而谁要是说资产阶级其个人也有优点,这个人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这样的区分显然过于粗疏,今天的人们已经发展出更多的智慧,不再拿这些东西当作圭臬。但是,曾经有过的那么一个印象深刻的时期,它所产生及延续的思想影响,却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的。我将在我们环境中发生主导作用的人性知识,称做一个“高版本”的人性论。所谓“高”,就是对于人性拥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和估计,有的时候甚至过高,而对于人性中所具备的缺陷、沉沦等各种有限性,缺少必要的自觉意识。
将一个阶级加以神话,与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神话气氛是互相影响的。在那种气氛之下的人们,习惯运用一种人间奇迹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现实和未来及看待人们自己。毛泽东有诗句云:“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好家伙,六亿人口(除去一小撮坏人,一般来说你我都在内)都成了如同古代圣君尧皇帝和舜皇帝一般。所有伟大光芒最后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被当做“神”一般,他所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去世的时候令许多人大吃一惊,觉得既然红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他就不会撒手人寰。我小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二
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东西?事到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够将诸如此类的事情,仅仅理解为历史的偏离,而应该从中找出某些能够理解的线索。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台湾的思想史学者张灏先生,曾经就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在人性方面的不同立场做过深入研究,他提出了“幽暗意识”这个重要概念。他发现基督教文化是以人性的沉沦为出发点,因而着眼于生命的救赎;而儒家思想则是以“成德”的需要为基点,导致对人性做正面的肯定。当然这不等于说,儒家思想一味地乐观,对于生命的缺陷全无感受和警惕,但是总的来说,儒家的主流主要是对人性幽暗的一面作“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而基督教则采取“正面的透视与直接的彰显”。
2004年我在中国香港科技大学访问了张灏先生。他向我解释“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的区别如下:
“忧患意识”是感觉到周围世界出了严重问题,危机四伏,从而产生一种忧惧与警觉感。因此,忧患意识认为人的忧患,人世的阴暗主要来自外界,而人的内心却是我们得救的资源。发挥人的内在“心力”,可以克服外在的困难,消弭忧患。“幽暗意识”不一样。它提醒我们要结合人性、人心内部的缺陷来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就着人性作一个彻底的反思。很多看起来是外部的灾难,正是由人本身、人性中的缺陷、堕落所造成。人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格,但归根结蒂,那是有限的。与之相反,人的堕落却可以是无限的。对于人性中幽暗的这一面,必须要有十分的警觉。
既然身为凡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当权者也不例外。仅仅指望通过“成德”的君王,指望“内圣外王”,那是靠不住的。因为人心有着太大的陷溺可能,人人都有可能腐败。张先生十分欣赏参加撰写“联邦论文”的汉密尔顿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这也不等于说,权力之外的人都是清白无辜的。”“联邦论文”的另一位起草者麦迪逊这样写道:“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看来有关民主思想和宪政制度,远非只是令人想起“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有关人性的幽暗意识,才是更为深沉的力量和基础。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任何制度设计的背后,都有着某种强大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制度的区别,也反映出人性论的深刻区别。
这个方向上的表述,对于我们的耳朵来说仍然比较陌生。很难说我们已经从过去“高大全”之“高版本”的人性论中摆脱出来。我举两个手边的例子。一是汶川地震之后,那位“郭跳跳”先生在批评范美忠地震中逃脱时,一句“不是人”脱口而出。范美忠的行为当然可以讨论和批评,但是为什么那样做就“不是人”了,而不正好是人性的某种“自然流露”?第二个也是引起哗然的陈冠希“艳照门”事件,许多粉丝对于素来崇拜的明星们的表现极度失望,感到心中的偶像坍塌,有人甚至发出“禽兽不如”的尖叫。然而,对于人能够做出什么来,人性可能何等沉溺,还有什么不能估计到的?最不应该的,是将照片放到网上的做法。
客观地说,“高版本”的人性观其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它体现了对于人性的较高期待,希望人不是像他当下表现的这个样子,应该比当下更好一些,能够通过某种渠道得到提升、升华。但是它埋藏的潜在的危险性是:一个人不是他想成为什么,他就已经是什么;一个人不是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他就已经是这个样子;在他的自我期许和这个人的实际情况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分离和鸿沟。
三
所谓“低版本”的人性观,是希望对于已有的人性知识有所调整。
从表面上来看,它意味着放宽对于人性的认知,以更加放松的态度,接纳人性的种种表现。对于人性中的杂芜混乱,尤其是其种种堕落和沉沦,有着足够的估计和思想准备,而不是动不动拒斥说这种事情不是人干的。要相信人能够做得出任何事情,即使是做出为人所不齿的举动,那个人也仍然是人,他的人性或许离你并不是十分遥远。在同样能够做出令人震惊也令自己震惊的事情方面,或者干脆说——在同样能够作恶方面,人与人一概平等,不分高低。
然而这样说,并不等于放弃对于人的道德要求,恰恰相反,这个“低版本”的人性观,正是为了对于人性做进一步的约束和规训,是强调——不管是驾驭还是化育人性,都首先需要对于人性有正当的了解,对于人性中的阴暗面有所正视,而不是站在坡上唱高调,或者仅仅是旁敲侧击,而不做正面的直击和追击。所谓“低”即意味着,一旦放低了看人性、望见了人性的种种表现时,对于人性中那些幽暗面,便应该有着足够的意识,从而引起足够的警醒、警惕和防范。
尤其是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变和转化”的。任何人性中的因素或侧面,在特定条件之下,都有可能发生性质的变化,从光明的变成半透明的,再变成晦涩的,乃至完全失掉光线,变成黑暗的一部分。就像小说《漂亮水手》中,舰艇纠察长克拉格特形容天使般的比利·巴德:“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包括那些美好动听的词句——为了全人类或者什么的,都有可能演变为性质不同的另外一些东西。走笔至此,我想起三年前去世的何家栋先生,这位当年在太行山参加抗日队伍,北平解放时的地下工作者,在离世前不久与我讨论过这样的话题:“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何等的苍凉,何等的沉痛哀伤!
人性的内部转化现象,要求我们哪怕在体验自己身上的好东西时,也要存有十分的警惕,或需要求证它的反面是否同时存在。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命名自己的工作,那便是“从洁白中拷打出罪恶,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转化无处不在,意味着人性的幽暗无处不在,人们的警觉便也应该无处不在。
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内部转化,提醒人们——人当然有其求善的和向上的一面,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人也有往下坠落甚至堕落的极大可能。比较起来,人往下坠落的速度,比起往上提升的速度,不知道要快多少倍,那几乎是一个无底洞。事到如今,我们理解这种东西应该并不困难。人们发现许多贪官是一些俗话说的“苦出身”,年轻时正派向上,遵纪守法,通过了组织上的考察得到了极大信任,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思想或人性就开始发生转变,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有一种说法叫做“经不起诱惑”,好像事情是从外部开始的。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说到底,他本人应该为自己人性的堕落负责,在外部世界对他发生作用之前,他本人身上就存在这种潜在的堕落的种子。
经常听到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动机是好的”,是“好心办坏事”。但是“动机”或“人心”这些东西怎么会那么清澈、让人一眼看到底呢?别人且不说,即便是一个人自己看自己,也有许多看不清楚的地方——人是一种十分能够替自己圆谎的动物,有时候是故意隐瞒,有时候是视力不够。因此,必须结合动机浮出水面之后的具体行为,尤其是这件事情的结果。为什么动机不体现为结果,要与结果相分离呢?为什么不会事先将可能存在和爆发的危险性多考虑一些?
近年来经常听到这里桥垮了,那里楼房塌了,事先若是多一些“幽暗意识”,将可能出现的危险多想一些,而不是抱有侥幸心理,情况可能会好许多。任何“动机”都需要有科学精神以及实践能力与此相配套,并最终接受结果的审核。实在地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受过“幽暗意识”的训练,而是恰恰相反——好大喜功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幽暗意识”,也是一种负责任的精神,而不是推诿给外部条件。不管发生了多大的事情,到头来仿佛他一脸无辜,什么也扯不到他头上,这是虚假的,也是一种恶的表现。
考虑到人性中盲目、陷溺和坠落的潜能,就意味着在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范围之内,在由人所安排的这个世界上,便不适合设立比如“至善”、“至上”、“至高”这样一些标杆,不宜将凡身肉胎的某个人神圣化,或者将某种力量神圣化和绝对化,任何人都是会犯错误的,任何人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全能的。
在某种程度上,“幽暗意识”比危机意识要来得更为贴切和中肯,它体现了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调整,是自觉地负起责任。这种“幽暗意识”需要体现为看得见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对于权力的运用和管理。论及个人的变质或曰人性的陷溺,没有比拥有权力者来得那么汹涌迅猛。我们周围的无数现实,一再证明了那句著名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将权力抓在手中的,是一些能腐败、易下坠的凡人。
四
在今天,“以人为本”是一个非常富有意义的提法。它清楚明白地划分出我们民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我们民族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迈入一个现代社会也是世俗社会。在这里是一个人的世界,是以人为尺度的世界,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围绕着神的意志转动的世界。这一步非同小可。
然而,在将目光投向人自身、人的世界之后,需要进一步追问到底“人是什么”?如果说人是复杂的、多侧面多层次的,人性中拥有从低音到高音的各个不同频道及其互相转化,那么,到底以什么样的人为本?以什么样的人作为尺度?在取代了“神”或者神性力量的位置之后,人自己是否对于自身的缺陷、沉溺和坠落,有足够的自觉和警醒?而不是什么都以“人性”的名义,弄得人性过于泛滥。当然,这样的问题只是在确立“以人为本”之后才能够提出的,需要我们当代专家学者对此负起责任。不妨稍微想想,“人性”怎么会成为一种名义?
(摘自《思想与乡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定价: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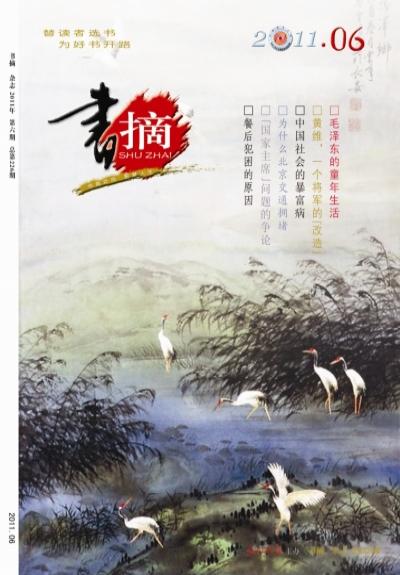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