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先生是北京人艺建院元老,曾长期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曹禺这样评价过他:“他不断思索与实践,专心致意地琢磨构思,沉迷于他所理想的戏剧境界。他精心揣摩,着意推敲,不放过任何能说明戏剧核心思想的光色、画面、音乐与情调,不忽略意义精微的台词与动作。他在舞台上纵横挥洒,创造出既符合作家的意图又丰富作家想象的意境。他的导演工作,精致确切。常常是经过无数昼夜,终于得心应手,立下‘意’根,画出枝叶,放出一片明丽的朝花。”
今晚的表演都是在讨好几个人……
在我的案头上,摆着一封信。那是半个世纪前焦菊隐先生在深夜里,写给于是之和叶子的信。
1953年的冬天,话剧《龙须沟》首演不久,导演焦菊隐看过当晚的戏以后,回到家里仍激动不已,夜难成寐,便给主要角色程疯子的扮演者于是之和丁四嫂的扮演者叶子,写下了这样一封长信——
11月22日下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演员俱乐部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对于《龙须沟》的演出,特别是对于导演艺术和表演艺术,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逐步设法改进的……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意见是没有从生活出发的,也值得我们好好分析辨识。 目前,我国的导演与表演工作,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形式主义、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并且需要长期地、大力地、相当艰苦地去克服。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在我们的批评者们中间的形式主义、概念化、公式化的思想残余,同样没有被肃清,而且常常起来作怪。因此,在我们克服自己的形式主义、概念化、公式化的表演斗争中,应同时向有形式主义、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意见”作斗争。
艺术道路是艰苦的!我们必须走最艰苦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是不易的——一方面,要克服自己的创造思想上的基本缺点和错误观念,要学习正确的创造方法;而另一方面也必须懂得坚持什么是正确的,反对不正确的,肯于为了拥护和坚持正确的而宁肯一时遭受不正确的意见的指责甚至攻击。这才叫战斗。这才叫忠于艺术。
走向形式主义,为了个人一时的得失,为了个人一时的受恭维或受贬斥,而投降于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意见,是最容易走的道路,但也是摧残艺术的道路!
这封信,既指出了那时文艺创作上严峻又复杂的形势和滑坡下去的危险以及十分可怕的后果;又指出了怎样才能不计个人得失地坚持正确的,克服错误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也是需要有胆有识的。
接下来,焦先生说:“听取意见,我们要耐心、虚心,但,对于其中戕害艺术的部分,企图拉回到形式主义范畴去的思想,我们虽受严重批评,也应坚持到底,一切在所不计!”“为了维护艺术,为了达到正确的创造途径,我们是宁愿蒙受‘不虚心’的批评呢?还是为了个人一时得到‘虚心’的虚名而毁害了艺术呢?”
“我今晚看了戏,觉得于是之和叶子的人物形象大大走了样儿,尤其是丁四嫂的形象。为什么把声音变得那样尖,那样亮,那样柔呢?丁四嫂宛如一个风未吹过、雨未打过、毫无忧虑、吃得壮壮的女人,只是因为她懒,或者因为她好赌、好吃,好什么的,才把日子搞穷了,而穿上一身破衣服的!这里看不出反动政治的压迫,看不出四嫂是怎样受苦的劳动的人,看不出她是一个被精神与物质的苦难所煎熬成为嗓音像破砂锅一般的人来了!今晚的丁四嫂,处处是柔情,看不出这一个直率但又没有涵养的女人的挣扎性来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演员在力求美化她的人物,以至甘心放弃了她的表演任务!
“程疯子在许多地方,也和丁四嫂一样,大吵大闹,高声‘演戏’,把第二幕第一场叨念小妞子一段台词,处理成朗诵式的独白——16世纪式的表演!于是之同志竟忘记了你演的程疯子是半夜走出来,不肯惊动任何人,怕吵了任何人的觉,而偷偷出来一个人小声叨念的。我看得出来,今晚的表演都是在讨好几个少许提意见的人,而欺骗了广大观众。今天,作为观众之一的我,是忍受不了这种也可以说是欺骗也可以说是愚弄的!我要不顾情面地向你们抗议——因为你们忘记了你们是艺术家。”
……
“夜已深了,手腕酸痛。我今天虽然为工作谈了六小时的话,看三小时的戏,但,我的心中的苦恼使我睡不着觉,使我不能不写完这封信。如果我说得太坦白,请原谅我有责任如此。朋友,同志,原谅我吧。”
焦先生的信写得如此中肯、坦诚、动情和深刻,使于是之、叶子以及所有读过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惊醒、反思、愧疚和奋起。显然,焦先生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以一副铮铮的风骨出现的。有人说,《龙须沟》站住了,现实主义站住了,北京人艺也站住了,而焦先生正是这一切的探索者、创始者和保卫者。
最后的发言
早在大革文化命的初期,焦先生第一批被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关进了“牛棚”,此时,他为自己的大女儿焦世宏写过一封祝贺生日的信,其中提到:
一、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二、我将来还要做导演;
三、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买生日礼物;
四、我希望你一定要努力上好学。
老实说,在这个时期焦先生对自己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当时,不论报刊还是广播都在大肆宣扬“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焦先生悄悄对别人说:“我在北平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也不能全给否定了吧,样板戏里不少演员都是“德”、“和”、“玉”班出来的,我还是为京剧界培养了不少人才的。”
1973年,北京话剧团(北京人艺在“文革”中被改成的名字)排练了一个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话剧《云泉战歌》,当时上边来了新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实行“一批、二用、三养”。于是,剧院“军工宣队”准备征求一下焦先生对这个戏的意见。
焦先生这时已经离开了“牛棚”,刚刚放到群众当中继续接受监督和改造,接到看连排的通知以后,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演员,马上来到他住的小平房里好言相劝。
演员问:“你真要去看连排吗?”
焦先生答:“要去,不去是不礼貌的。”
“看完以后,你还要发表意见?”
“那当然。”
演员想了一下说:“如果非去不可,我提出三个办法供你选择:第一,是看完戏以后一言不发,这样他们就抓不住你的‘辫子’,顶多说你不够积极;第二,是光讲好的方面,一个字也不要批评,他们顶多说你有顾虑,不诚恳;第三,是凭着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艺术水平,想到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可能是最危险的。”
焦先生听后一阵沉思,没有吭声。
演员继续说下去:“我不希望你选择第三种办法。因为这种办法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即使暂时不批你,也会记下一笔账,以后是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敲打你的。”
焦先生抬头问:“你说完了吗?”
演员点点头:“完了。”
焦先生向演员笑了笑,还是没有吭声。
演员看得出焦先生是要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为此心里不由得有所担忧。
焦先生看《云泉战歌》连排的那一天,特意换上一身衣服——一件半旧的灰色毛料中山装,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连裤线也是笔直笔直的。而且,如同以往一样,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乱,乌黑发亮。他走进首都剧场后楼的三楼排练厅,来到最后一排座位上,和一些演员一起看戏。
连排结束以后,并没有人征求焦先生的意见,他对此也不在乎,自自然然地回到史家胡同宿舍那间又阴冷又黑暗的小屋里去。
第二天,“军工宣队”派人来找焦先生谈看戏的观后感。焦先生认真地想了一下,说出了15个字:“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这些话在“文革”中,出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口,就像是爆破了一颗原子弹。听意见的人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并且深为焦先生捏了一把汗。
这个严重的政治和艺术表态很快就上了剧团的第l3期《情况简报》,当作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突出事件,既上报,又下发。
那位热心的演员马上找到焦先生说:“你可捅大漏子了!三种办法你为什么单单选了最坏的一种呢?”焦先生似乎是有所准备的,缓缓地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良心办事的,你跟我排了不少戏,你应该了解我,我知道你的办法都是出自善良的愿望,谢谢你对我的关心。至于‘军工宣队’对我的意见有什么看法和打算,我是根本不作考虑的。”
这——就是焦先生一生当中,在戏剧问题上最后一次难能可贵的、令我们难以忘怀的发言。想想看,他在艺术问题上一贯不讲情面,不说假话,就是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日子里,也勇敢地没有保持沉默,对一个所谓“三突出”的剧目,竟然提出了公开的、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批评。
就因为如此,在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高潮中,焦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于北京展览馆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一次被定为“为30年代反革命文艺黑线翻案,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新生事物”的、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位曾以“南黄(佐临)北焦(菊隐)”闻名的导演,竟然两眼闪着泪花,万般无奈又悲愤满怀地向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
焦先生的心灵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和伤害,精神近于崩溃。一天,他突然感到胸部不适而住进了医院,经过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癌细胞已向全身扩散,动手术也无济于事。医生们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没有把这个不幸的“判决”告诉病人,但是焦先生还是通过观察病床栏杆上的卡片,从一般人并不认识的拉丁文字里,知道了真相。
为了不给亲朋好友们带来更多的痛苦,他装作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平静地要求见见下乡插队的大女儿焦世宏。当他见到从延安赶回来的焦世宏后,出人意料地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席话来:“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待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焦世宏还没有听完父亲的话,就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她只能连连点头表示一定照办。
此后,焦世宏做好了一切准备,想尽可能详细地、更多地把父亲的话记录下来,为国家、社会和戏剧界保留一份难得的宝贵财富。并且,为此准备好了一个像样的大本子和一支钢笔。 然而,事与愿违,焦先生由于对化学放疗的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到了病危阶段,处于弥留的状态。自己最后的愿望已无法实现。
当医院把病危通知书送交给剧院的时候,“军工宣队”负责人来到病房,竟然大声地追问:“焦菊隐——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要向组织上交待吗?”当遭到焦先生微微摇头拒绝以后,负责人立即向家属宣布了三条必须遵守的“规定”:1.不许给死者穿衣服,只能用一条旧床单包裹起来火化;2.保留骨灰的木盒子只能用最便宜的七元钱一个的;3.不许立碑,骨灰盒只能存放在八宝山公墓的地下室里。
焦先生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疼痛难忍,唯一使其延续呼吸的事,是焦世宏按照政策规定早应办理、却迟迟没有办成的回京之事。他在病床上紧紧拉着女儿的手,含糊不清地问:“你……的户口……落上……了吗?”焦世宏答:“已经落上了!”这时,焦先生才放心地合上了双眼……
焦先生走了以后,大家都在情不自禁地猜想着他那急于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究竟是什么。首先猜想到的是他生前已经拟就的两篇论文提纲,一篇是《论民族化》,一篇是《论推陈出新》。《论民族化》和《论推陈出新》都是1963年初,他准备为探索话剧民族化和不断推陈出新过程中,所写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与感悟,打算每篇论文要写到3万字至5万字。然而,由于当时文艺界“左”倾思潮愈演愈烈,他几经执笔又不得不放下,终于未能把论文写出来。
焦先生缔造了一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的话剧演剧学派,即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不仅是对于中国话剧事业也是对于世界话剧事业的重大的、不可代替的贡献,而且已经和必将产生深刻的、深远的影响。
(摘自《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定价: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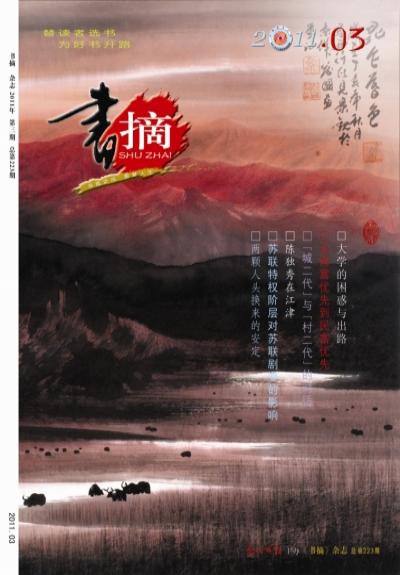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