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生于传统士大夫之家。 1935年被俘在押期间,瞿秋白写下自述性文字《多余的话》,用独特的方式呈现了个体在革命过程中遭遇的不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瞿秋白以及《多余的话》这一文本的评价几经周折。1950年12月,筹措编纂《瞿秋白文集》时,新中国主席毛泽东曾写下题词,既肯定了瞿秋白的烈士地位——“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也提示了他的独特性——“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1960年代后期,瞿秋白被作为“叛徒”彻底抹黑,1980年代他的形象被重新建立,《多余的话》从政治批判目标到学术研究对象,围绕瞿秋白这一形象,已形成多层次的话语结构。其间所书写的个体与历史的纠结,以及围绕瞿秋白形象所形成的话语逻辑与思维惯性,至今仍是个未能被充分解说的话题。
《多余的话》结尾有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句突兀的结语曾引起后世论者的注意,比如单世联认为“瞿秋白在无意识中以豆腐来象征自我,豆腐的纯净值得赞美,豆腐的软弱不妨碍它是世界第一”;“软嫩洁白”的豆腐的对立面是20世纪中国革命中无处不在的强硬残酷的权力斗争,它要求参与者具有钢铁般的意志,瞿秋白的个人悲剧也基于此。
其实这句“多余的豆腐”在更早时候就已经引起人们对于“钢铁”的联想。1960年代批判瞿秋白的热潮中,有署名“白刃”的作者撰文谴责瞿秋白“直至绝灭的前夜还念念不忘‘豆腐’”:
豆腐,也正是“豆腐”这两个字,一语道破了这位“坚贞不屈的英雄”的本来面貌!
钢铁,总是钢铁!豆腐总还是豆腐!……豆腐终究变不成钢铁。
共产党人的意志坚如钢铁,然而,叛徒的骨头比豆腐还豆腐!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随着“刘少奇集团”被批斗,瞿秋白也被定性为“叛徒”,遭到鞭尸的厄运。为此曾专门出版《讨瞿战报》,在后来的文章汇编中,首页赫然是毛泽东头像和语录:
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这段话的来源是毛泽东写于抗战时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知识分子能够起“先锋”、“桥梁”的作用,但他们也是容易消极、动摇、脱离革命队伍的,甚至会变成“革命的敌人”,后者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知识分子能够革命到底与他们投入革命、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决心相关,也有外在的判断标准,这就要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趣味是否已是群众化的,若非如此,他们就是“空虚”、“动摇”的,因为知识分子骨子里带有一种主观的个人主义自大性,非经过长期群众斗争,无法洗刷干净。这段话谶语般地道出了现代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将面对的现实,他们必须在克服自身属性的漫长修炼中才能被革命所接纳。
《多余的话》一度被认为是瞿秋白“叛变”的主要根据。1980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了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的报告,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谈到这一文本:“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的确不提供任何坐实“叛变”的信息,只是其中“消沉的语言”引起猜测。也就是说,这篇自述式的文本,是以一种心境和态度被指为叛变罪证,以致被敌人枪杀的事实在当时也无法使瞿秋白成为“烈士”,“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一个共产党人,不论任何场合,只要还有一口气,那他就没有丝毫权利停止同敌人斗争,他们永远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言壮语铭记心怀”,1960年代瞿秋白显然是被作为“主义”不够真的反面典型,写下“调子低沉、充满绝望、失意的诗”和“唏嘘泣诉、哀怨欲绝”的自白书,“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就无法成立了。
对瞿秋白的批判关联着对陈独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风潮,本文关注的是他们身上的文人气质无一例外地受到批判。 “单纯的文化人”这一身份再也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避风港湾,只要他们存身于社会中,“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就必须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共同规训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钢铁”,那些维护自身的“豆腐”属性还为此自鸣得意的人,只能作为体制的叛徒而被清除。
刊登于1967年《文革简讯·讨瞿专号》上的一篇文章认为瞿秋白的行动逻辑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样的,其中那种以“观察”、“反省”、“闭门思过”等方式来实现的“自我修养”,与投身群众的革命观念根本对立,“因为是‘文人’,所以叛党。因为有‘弱者的性格’,所以投敌。投降有理,变节有理,我们能够听信这样的鬼话吗?阶级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政治动物’,没有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性格’,也没有什么超政治的‘文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60年代后期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建党思想的代表作和纲领”,虽然其中也强调革命的唯物主义者的修养“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像旧文人那样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但其中充分流露的对个体的强调和个性自觉,与时代风气格格不入。
反观瞿秋白这个形象,无论是作为“烈士”还是作为“叛徒”,他对于其时代的独特性都很大程度上缘于自我观照的方式和面对世界的姿态。
瞿秋白去世两年,《逸经》半月刊上刊载了《多余的话》,开篇有署名“雪华”者所写的引言,其中对瞿秋白的政治生涯及其对青年人发生的影响,多抱微词,唯独对这种自我书写的方式击节赞赏。有人认为《多余的话》“充分地流露了求生之意,这对于共产党,要算是一桩坍台的事”。而这篇引言的作者说:“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他何尝不可以慷慨就死?沽得一个倔强到底的‘烈士’‘芳名’,然而他仍然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刹那供出自己的虚伪,揭破自己的假面具,这便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逸经》上的这篇引言将瞿秋白作为“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文人”的典型,认为他在“最后的诉说”中却体现了“文人”身上坚强可取的一面。
“豆腐”还是“钢铁”虽只是比喻,但还是有些指标可寻的。“意志”关联着“躯体”,特别是在躯体的苦痛(受刑)和躯体的消灭(死亡)这两件事上,尤其容易形成对人的评判,也因此有了瞿秋白狱中形象的不同版本。
版本之一是强调狱中受刑,顽强不屈。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持此论最激烈,1950年她曾致信《人民日报》:“我最近听周若华先生说:当秋白被捕后,曾被用酷刑迫取口供,但秋白不屈,同时蒋匪的两派特务又互相争功,乃电蒋匪请示。后蒋匪复电如劝降不成,就地枪决。”她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1935年瞿秋白被捕当夜,“敌人吊打秋白,逼问口供。秋白镇静地掩护自己,敌人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受刑”似乎是就义烈士的必经之途。瞿秋白遇害一年后,在《救国时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就出现了关于瞿秋白受刑的文字:
蒋军既获先生,押长汀师部,深夜严讯,备施毒刑,企望从先生口里可以知道一些中苏(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行动与策划。先生虽炮烙在前而镇定自如,除力言中苏政府及红军志在抗日救国外无他语,受刑痛极,晕死者再,然醒后亦只闭目呻吟而已。蒋知先生非毒刑所能屈,电汀洲令以柔法说降,先生虽被囚入“优待室”,闲且许记者往访,但先生态度仍不稍变,遇有来访者,先生必滔滔说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全国一致抗日救国之方略与全民团结之必要,此外不常作他语,谈者有为蒋介石文过者,先生则折之以事实,闻之以大义,谈者往往语塞;因此说客亦无所施之计。
在这段描述中,国民党对瞿秋白是先威逼施刑,后以利诱,均不见效,反而自取其辱,文章以此证明瞿秋白确是软硬不吃的坚强战士。与此同时,瞿秋白狱中形象的第二种版本——被“优待”——也淡入进来,这是严刑拷打不起作用的自然结果,也打造了瞿秋白从容闲适的面相:“先生在狱中常要求阅报,但被许时极少,因此常作诗作文并从事篆刻以自遣。意态洒然,闻者向慕。”
狱中写字、治章、作文的书生形象在后世引起了“临危不惧”和“摇尾乞怜”的双重解读。实际上,后来杨之华捍卫瞿秋白形象的主要方式是强调被害牺牲这一事实:“二十年前,国民党蒋介石匪帮杀死了秋白同志,宣布了他的‘罪状’,可是当地人民却是同声颂赞:‘瞿秋白被枪毙了,那个共产党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硬骨头!’‘在枪毙前还唱着革命歌呢!’”对于流传出来的狱中诗作特别是《多余的话》,杨认为是蒋介石收买文人写的伪作,用来诬蔑瞿秋白的。在这方面杨之华与丁玲的态度截然相反,后者在延安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就“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因为其中传达的矛盾心情,早在1920年代上海大学时期瞿秋白就曾在给丁玲的信中委婉地表达过多次。
李霁野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瞿秋白在狱中所作诗词,其中有“枉抛心力作英雄”一句。臧克家对此反应激烈,撰文说:“可见这些诗词作为逸事附着于秋白同志的死流传得颇为广泛!这些诗词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它们对于他简直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侮辱!这些东西决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它是敌人埋伏的暗箭,向一个他死后的‘敌人’射击。……据《烈士传》里好几篇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他在临刑前高唱国际歌及红军歌,并大喊:‘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这才是和他雄壮的死、不朽的死合节的雄壮的诗、不朽的诗!这和‘报纸’上所刊载的那些简直不能相比!那四句集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释教徒还差不离。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死,就是永生!至于‘枉抛心力作英雄’,那简直是‘死’前忏悔低头了。一个拒绝诱惑、以死殉人民事业的革命斗士,会在这最后关头否定了一切,连自己光荣的历史也在内!这不但不可能而情况恰恰是相反的。”为此李霁野写信公开道歉,称“完全同意”臧克家的意见,诗词作为附注,只是“表明从容就义的具体事实”,并强调“在那篇纪念文中表示对于秋白先生的崇敬那是应当没有疑义的”,还在括号中附上作者低调的观点“我的意见也许不对,不过我以为这是同样壮烈”。直到瞿秋白早已被平反,1980年代初重新编辑纪念文章出版成书的时候,李霁野的文章中仍只是说瞿秋白“从容就义前还赋诗作词”,再无一句提到诗作内容。
对瞿秋白狱中表现、作品真伪的执著,其实源于人们心目中“革命者”应有之义和由此产生的价值判断。无论是批判瞿秋白的人还是为之辩护的人,所持标准竟是吻合的,那就是革命者必须将生命交付“主义”,并表现出积极、乐观的“钢铁”一面,直到瞿秋白被平反,重新成为烈士,“豆腐”与“钢铁”仍是作为矛盾的二元而存在。如陈铁健撰文重评《多余的话》,认为这一文本的灰色基调是因为瞿秋白“放纵自己思想中颓唐的一面,甚至不惜违心地自暴自弃、自嘲自污,而缺少乐观进取的豪健情感和激昂慷慨的宏伟气魄”,“一个共产党人,是要有那么一股革命的浩然正气的。哀叹、愁苦、懊丧、悔恨,不是无产阶级战士的英雄本色,只能看作是没落的绅士阶级的深重烙痕。这是不足为训的。但是,对于瞿秋白对自己丧失信心的软弱表现,我们不应把它看作对整个革命事业丧失信心,更不应看作是 “叛变革命”。从中可以感到,时代对“豆腐”之内涵已发生松动和宽容。
(摘自《“自杀时代”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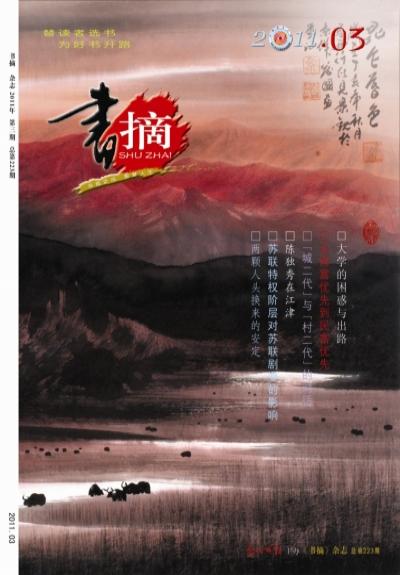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