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就是幕宾、胥吏、长随等。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作伪、敲诈勒索等。
书吏执政弄权一直存在于古代官场。到清朝的官员,他们对大量的案牍文书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习法令世务。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权力更大,人谓之“无异宰相之柄”。吏部掌握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再上报。
对此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和阐述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在《灰牢考略》中又进一步通过对监狱的白、黑、灰的演变,使人们对“合法伤害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辞海》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但从古书和史料上研究,在最初的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者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用来临时关押人了。清朝著名师爷汪辉祖在《学治说赘》里提到班房时说:“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这就是说,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关押场所,就是“灰牢”。“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的“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之官法的人禁锢其中,也是类似“灰牢”的地方。
“合法伤害权”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整人”、“打击报复”等等。
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唐代韩愈写过一篇《蓝田县丞厅壁记》,记载了一个姓崔的朋友,在担任谏官时因上书言事而受人排挤,被打发到蓝田县任县丞。崔县丞本来想,当县丞就当县丞呗,照样能够有所作为,可事情却不那么如愿。韩愈这样写道:办理文书时,办事小吏怀抱已经完成的案卷找到县丞,左手把案卷前部卷起来,右手递上笔,站直了看着县丞,说道:“你应该在这儿签名。”县丞抓起笔,在预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签上名字,再问办事小吏是否合适。小吏说:“可以。”公事就算办完了。至于案卷上写的是什么,县丞一点都不清楚。所以韩愈慨叹道,县丞“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
不能得罪官员的随从、幕僚、小吏。前文已讲过,地方武官得罪了师爷左宗堂就是一例。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叫“品官”,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招募,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做“以工代干”,他们与衙役并无区别,区别只是他们提供的是知识性服务而已。
官场这样不小心得罪这些小吏的官员不是没有,瞿耐庵到兴国州走马上任,因生性吝啬,不肯掏腰包向前任的账房师爷赎买记录各式“孝敬”数目的明细账簿,那师爷一气之下,干脆将账簿的数目都改了。譬如素来孝敬上司一百两银子的,改成一百洋元;应该孝敬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瞿耐庵稀里糊涂地按着伪造的账簿送礼,送一处得罪一处,送两处得罪两处,自己还不明白所以然,很快将上司与同僚都得罪遍了。
起初因为湖广总督湍大人是他干外公,他的干外父戴世昌的腰把子也挺得起,有些上司晓得他的来历,大众看在总督的份上,都不来同他计较。不料湍大人后来调离湖北,关系网络半径变长,权力边际效用递减,戴世昌尚且失势,他这个拐了好几弯的干外孙婿自然无人担待了。接任的湖广总督贾大人初到任,就有人来说他坏话,起先贾大人还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时撤任,后来说他坏话的人多了,终于将瞿耐庵撤了职。
官场上的门子、门政、门丁等,类似于现在机关单位传达室的看门老头儿,他们只是官员的私人奴仆,但是却有无形的权力。这样的人也不能得罪。
话说湖北蕲州有个新任吏目(吏目是州的佐贰官,从九品,协助正印官掌管治安巡捕之事),叫做随凤占,花钱买了个“蓝翎五品顶戴”,请了漆匠将“五品顶戴赏戴蓝翎蕲州右堂”的头衔制成招牌,带着上任。
到了蕲州,随凤占照例先去禀拜知州大老爷,先见了门政大爷,送过门包,自然以好颜相向,彼此如兄若弟地鬼混了半天。见过知州大人之后,还不敢告退,凡是衙里官亲、师爷,打账房起,钱谷、刑名、书启、征收、教读、大少爷、二少爷、姑爷、表少爷,由执帖门丁领着,一处处都去拜过。也有见着的,也有挡驾的,连知州大人一个十二岁的小儿子,他还给他作了一个揖。一个州衙门已经大半个走遍了,出来之后,仍在门房里歇脚。门口几位拿权的大爷,是早已溜得熟而又熟,便是知州大老爷的跟班,随凤占亦都一一招呼过。三小子倒上茶来,还站起来同他呵一呵腰,说一声“劳驾”。
看看随凤占的名头“五品顶戴赏戴蓝翎蕲州右堂”,似乎很能吓唬人,其实这个头衔没有半点权力含量,只能用来向当地烟馆、赌场、窑子、当铺收几块大洋的保护费,绅衿开的当铺还不敢十分招惹,对知州衙里的官亲、师爷、门政,更是执礼周到,连对知州大老爷的跟班和三小子,也要尽量套近乎。不是随凤占这个人为人谦卑识礼,而是权力不如人。
一个九品芝麻官的家奴,能有多少权力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官衙门政在权力链条中的关键地位。以前的官员深居简出,办公之公堂与生活起居之内宅同在衙门之内,日常公务的处理,还有官场上的人情往来与某些隐秘的私下交易,一般都得在衙门内进行,这个衙门入得入不得,就看门子有没有刁难你。如果门子有意刁难,他有许多法子让你吃闭门羹,比如不给通报、谎称老爷外出或不见客等。常言道:“大人易见,小鬼难缠。”“小鬼”指的就是门子,“难缠”则显示了门子的权力的能量。
咸丰年间到福建任布政使(副省长)的张集馨就遇到了一个权势很大的门子——闽浙总督庆瑞(福建、浙江二省的一把手)的司阍。此人叫做张七,是庆瑞的心腹亲信,司道州县送给他的门包,必须是成色、分量达到官方标准的银子,洋元是不收的,每次属员送来门包,当面在门房拆封,看是不是够分量、够成色,短缺几分,立即掷回去,补足再送来。庆瑞则认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这个张七,更加肆无忌惮。
张集馨刚到任时,第一次送门包,因为银子重量欠缺六分(0.06两),就被张七掷出来,张集馨本想发火,但想到庆瑞已经批评过他脾气太刚硬,只好强忍下来,叫家人再加一钱银子送去。以后每次送门包,都是足色足量。
小吏大害,说的就是官场上那些看似很小的人物,他们没有官位,更没身份地位,但是只是跟随上司身边的,就有着无形的权力,只要有权力,任他是什么身份的人都要巴结,都是不能得罪的。
(摘自《官规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版,定价:28.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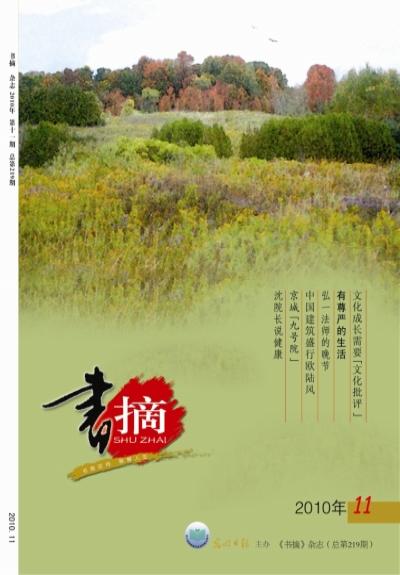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