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笛:我看网上流传一个帖子说,武汉大学的校级腐败高官落马了,武大师生评论此事是大快人心。这世道真是变了,以前说家里出了家贼的时候是引以为耻,现在叫大快人心。
闫肖锋:有人说大学腐败案80%都是跟基建有关系,凭良心说,实际上大学还是一个清水衙门,因此基建是它唯一可以捞的。
王牧笛:除了基建之外还有招标,还有后勤,还有招生。主要集中在这四大块。武大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媒体评论说震惊了大陆教育界。我看着就觉得好笑,如果这叫震惊的话,那大陆教育界一直在被震惊。
郎咸平:让我感到比较难过的是这些学生的幸灾乐祸。
王牧笛:说明武大校园的师生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但是苦于没有发言权,所以就等着他们俩出事之后放鞭炮呢。这是官场文化对大学校园最恶性的介入。在校长的选拔过程中,师生是没有任何能力说话的,这就是所谓的大学“衙门化”。人民大学的著名学者张鸣写了篇文章评论这件事情,他说大学校长最大的过失不是把钱揣错了口袋,贪污受贿固然可恶,他最大的过失是把大学的教育搞得一团糟,把学术当儿戏,最终毁坏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
闫肖锋:教书育人。这个育人更关键,那些楼堂馆所实际上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如果把育人这个规矩破坏了的话,大学就不能称之为大学了。
王牧笛:当年梅贻琦不是说吗,“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现在倒过来都去追大楼了。网友有帖子调侃说,现在叫“大学建大楼,大官捅大娄”。
闫肖锋:还有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现在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教授叫不响。
郎咸平:美国、中国香港跟我们内地的教育制度完全不一样。在美国,不做研究的才有可能去当系主任,当院长的根本就不是做研究的人。在学校里最受学生尊敬的不是什么系主任、院长之类的行政人员,而是大学的讲座教授。
王牧笛:我以前在查郎教授资料的时候,发现您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教授,当时也没太搞明白什么叫讲座教授。
郎咸平:你拿了博士文凭后到大学教书,先是助理教授,再升到副教授、正教授,这是三个级别。有重大学术贡献,由校长另外再特聘的叫讲座教授。莫里斯本来在剑桥大学当院长,后来就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特聘过来当讲座教授。还有像杨振宁、高锟、丘成桐也是讲座教授,都是对自己的学科有重大贡献者。
官员型学者
王牧笛:在欧美、中国香港,教授的地位是很高的,但在内地不行,教授首先得兼个一官半职。
郎咸平:否则你玩不转。
王牧笛:科研经费你拿不到,只有沾了系主任,或者沾了院长这个行政职务才能如鱼得水。
郎咸平:中国香港大学的研究经费甚至比美国还要多,但真正有影响力的绝对不是系主任。像我以前就常常被邀请去给年轻教授讲如何申请研究经费,他们不会找系主任去讲。而且一般大学在决策过程当中,会征询一些教授的意见,教授是大学的主体,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很多人问我说:“郎教授你只是个教授?”他觉得好像我怎么也该有个一官半职。
王牧笛:2009年评的 100个“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只有10%左右是一线的老师,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了九成。
闫肖锋:我发现这几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很多都是大学教授。
郎咸平:基本上都是。但很难看到有什么系主任。
闫肖锋:中国大学教授里面出个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不大。有一种说法,一流的教授去了国际机构,像跨国公司;二流的去大国企、大的垄断集团;三流的才去象牙塔教书、搞学问。去大学里面当教授的是混得不好的。
王牧笛:现在是用财富来衡量知识水平。
郎咸平:有些人问我:“郎教授,你只带博士生吧?”我说:“不是的,我还教本科生。”他们会很惊讶,我怎么会去教本科生。整个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本科生,我为什么不能教本科生呢?
王牧笛:现在内地大学稍微有点声望的老师,就不理本科生了。
郎咸平:我上次打电话去某大学找个人,我说请问你是哪位啊?他说他是某某校领导。要是我,我肯定说我是某某教授。
王牧笛:中国有一流大学吗?有,西南联大。它当时的校长梅贻琦说:“校长重要吗?重要。但是教授更重要。什么叫校长呢?校长就是带领这些单位的职工为教授搬凳子的,教授才是一个大学的灵魂所在。”今天不是了,听校长话的,同时能当上校长的教授,这才是最好的。
闫肖锋:还有一个是论文得达到一定的数量,这像工厂里面考核打工妹的办法——计件工资,你的论文要到一定的数量,才够评职称。逼得老师没有办法就去大量地复制。
郎咸平: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大学也有同样的要求。你要签合同的话,它会跟你讲得很清楚,你在未来的五六年之内要在什么样等级的期刊里面发表几篇论文,才会得到相应的待遇。但是你要注意,这些人都是从美国、欧洲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分析技能都已经定型了。你要把这种发表论文的标准用到内地的大学那是不可行的,除非他们是从美国读了博士回来的,否则根本不理解这个游戏规则。
王牧笛:也不是所有的教授都会去认认真真地写论文,我看到某高校四十多个教授不写论文而去竞聘一个处长职位。武大这个副校长前几年也是做学问的,后来转做政务工作去了。
闫肖锋:学而优则仕嘛。
郎咸平:在美国也是一样,奥巴马总统当选之后从哈佛、加州伯克莱分校找了很多教授过去。他们去的时候是向学校请了几年假,等到他们从政府部门退休之后,有的可能回大学继续教书。
闫肖锋:包括美国的财长最后去了哈佛当校长,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我们这是不归途啊,你一旦去当了官以后,很难再回来做学问。
王牧笛:中国以前叫学者型官员。
郎咸平:现在是官员型学者。
王牧笛:其实现在整个世界的教育界的一个共识就是,必须要教育家来办学,或者说教授来治校。鲁迅当年说过:“别以为教育当局是在办教育,教育当局是在办当局。”现在中国面临的学术环境跟当时也很像,就如张鸣总结的新“四化”——学术行政化、大学官僚化、校园衙门化、学者奴才化。咱们天天说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诺贝尔奖,我们大学教授都忙着当官呢,怎么能拿到诺贝尔奖呢?
不破不立
闫肖锋:最近我看到教育部的官员按照一个调查说,中国高校的科研能力全球排第五,说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的话,我们获得诺贝尔奖指日可待了。
郎咸平:我不晓得这个排名是怎么排出来的。
闫肖锋:可能是按照科技文献的数量排出来的。
郎咸平:在美国高校看你的科技文献,不是看数量,而是看你的论文引用率有多少,也就是你发表完这篇论文之后,别人写论文的时候参考了几次。那是非常规范的,像我的论文有多少引用,每篇都有统计。我们对诺贝尔奖的理解是不够的,它其实就是要找到在某个专业学科里面第一个提出某个新观点的人。这个观点是你先提出来的,拿诺贝尔奖的才会是你。
闫肖锋:原创性。
郎咸平:而且要经过二三十年之后,才知道你的贡献有没有影响力,到时候还得看能不能追溯到你,如果是几个人同时提出来的,到底选谁都很难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遴选过程。
王牧笛:每年诺贝尔奖结果一出,国内的媒体总会反思,除了反思科研模式,媒体一直都在说,中国的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的人创新性不足。
郎咸平:对,中国科技大不是搞了个少年班吗?少年班毕业的学生后来也有不错的,但只是在各行各业小有成就,没有出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天才,这不是少年班的初衷。为什么出不了天才呢?它遴选过程就是有问题的,当初在高中和初中所选拔的尖子学生都不是天才,而是些解题高手。
闫肖锋: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为什么30年高考出了这么多高考状元,但没有一个在政经各界成为杰出的人才;这么多在国际奥数上拿大奖的,但是没有出一个正牌的数学家。还有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内地学汉语的学生竟然比不过在美国学汉语的学生,因为教育方法不同,中国是背语法、背偏旁,美国是从语感、从对话上来训练。
王牧笛:一种是用感觉来学语言,一种是用语法来学语言。
郎咸平:所以到最后我们学生只能看,甚至看也看不很明白,不会听、说、读、写。
王牧笛:中西方教育里面,对于质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以前写字是从上往下写的。所以会不断点头,不断地确定;而西方人是从左往右写的,不断地摇头,不断地说NO。这种质疑精神对于科研或者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
郎咸平:我们是当看到一篇论文的一个假设条件可能有问题,我改变这个假设条件之后,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就能发表论文了。所以我们在美国做研究的过程就是要质疑前人,不断地怀疑才能够积累,才能创建出真正的科学,质疑就是创造力的开始。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什么东西,学生要全盘照抄、要背,背完之后要考试,考题还有标准答案,这样教出的学生就不可能有创造力。
闫肖锋: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萎缩。
王牧笛:我妹妹前两天刚上大学,给我发封邮件,说:“哥,我最近遇到一个困惑,你说这个背东西,我是死记硬背呢?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背?”
郎咸平:我们就不能按照自己理解的去背。
闫肖锋:实际上,你真正理解的东西别人想拿都拿不走,死记硬背的东西第二天就忘了。
对学术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有很多人问我:“郎教授,为什么你在中国能够看到那么深层次的问题,而别人看不到呢?是不是别人不敢讲啊!”其实不是的,我看问题的方法是在美国学的。就是一定要从既有的理论当中找出新的理论。怎么找呢?要质疑对方,把他所讲过的话,按逻辑全部过一遍,会发现有的地方有问题;然后找到问题的本质,再从这里做修正。因此,我看任何问题的第一眼,不会觉得你讲的对,而会觉得你讲的一定有问题。
王牧笛:马克思当年的名言——怀疑一切。而现在大学校园里流行的一个文化叫规训文化,教授被校长规训,青年学生被老师规训,彼此的规训就导致现在大学的怪现状。官场文化侵入大学,现在市场文化也进入了大学,教授不正经做事了——教授老板化,有多少教授在外面有公司。
闫肖锋:即便是没有公司的,他如果申请到研究课题也相当于一个项目经理,然后再组织一些硕士生、博士生给他打工。
王牧笛:现在的研究生管自己的教授叫老板。
郎咸平:在美国也叫老板。因为在美国做科研也要找经费,向公司、向政府申请。但不要以为这些教授拿了它们的钱之后就会替它们说话。从政府、从企业拿钱做研究全世界皆然,问题是你做了研究之后,要实事求是地发表你的研究成果,而不能成它们的代言人,美国对这个规定得非常严格。
闫肖锋:现在教授的收入里面,课题经费占了他收入的大部分。
郎咸平:这在美国是不可以的,经费必须完全用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放进自己的口袋。
王牧笛:现在教授手下的硕士生、博士生越来越多,而以前可能是几个教授合伙培养一个学生。陈丹青在谈到目前学术行政化、官场文化进入学校时说:“整体而言,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大学没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其实,中国人近些年对于教育政策的理解集中体现在所谓的教改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扩招。今天教改已经走过了十多年。
郎咸平:这十多年之后是什么结果呢?大学生毕业后基本失业。为什么?因为教改的本质错了。当初就因为看到美国大学生比例特别高,简单地认为美国一定是透过人力资本的投入造就了繁荣,因此我们扩招之后,培养出更多的大学生,也就能够像美国一样的富强。我们没有搞清楚本质的问题,以产业分工而言,中国是干嘛的?制造。美国人是做除制造以外的其他所有环节,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那些环节,制造是不需要大学生的。
王牧笛:过去一直都说大学是座象牙塔,其实象牙塔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现在哪有象牙塔呀,社会上发生什么事,大学就会发生什么事。以前大学里遍地知识分子的传统已经不在了,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了。
闫肖锋:把知识从这个地方倒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像我们一样进入媒体,把自己的名声最大化。易中天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要是2000多年前的孔子来到我们这个传媒社会的话,他也不会拒绝上电视的,这是一个趋势。”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能因为这种市场化、官僚化而消失。作为一个学术人,所谓立德、立言、立功嘛。立德在前面。
郎咸平:所以讲到最后,一个本质问题就是你的良知。换句话讲就是你对学术的信托责任,你既然在这个位子,就要承担起对国家、民族、老百姓的信托责任。
王牧笛:我们以前要勾勒知识分子,一般用的语言应该是独立的精神、批判的立场、边缘的姿态。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些“知道分子”的宣言是什么?就是只说别人想听的话,说别人想要知道的东西。这是一种迎合,这种迎合展现了现在中国知识阶层整体的面貌。
(摘自《财经郎眼03:需要了解的经济问题》,东方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2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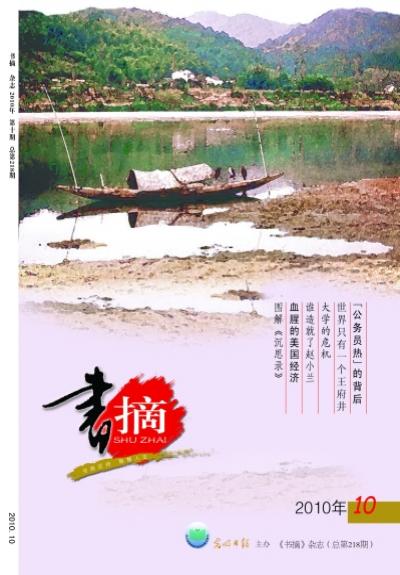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