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们
我有四个母亲。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爸爸既然给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家庭,我也感受到它的温暖,那就接受它吧!我爱我的爸爸,也爱他身边的人,就像我妈说的:“我爱我的丈夫,也爱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个家庭成员。”
我的母亲曾正蓉(1901—l961年)60岁时病逝于四川。我的外祖父曾星五是四川内江人,老实憨厚,心地善良,但不是很精明。他开了个绸缎铺,生意还过得去。母亲有三个弟弟,家里就她一个女儿,所以外公很疼她,特别请了私塾老师教她读书识字。母亲虽然没有正式上过学,但能看报、写日记、记账,特别还看过不少古典小说。
我母亲因为结婚11年才生了我一个女儿,所以非常疼爱我。我们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爸爸时常在外面东奔西走,很少在家,更何况他们两人是包办的婚姻呢。真的,他俩都有说不出来的苦。不过,母亲的气度还比较大,心态也比较平和。她时常说:“既然父母做主,把我嫁给了你爸,我就要把这个家担起来。他喜欢的人,我当然要学着去爱她们;他的儿女,理所当然也是我的儿女,我要用心去抚养他们。”因此,父亲去敦煌的三年,我们五个姐妹上学、读书、穿的、吃的全由妈妈一手操持。特别是我们五个人从头到脚,包括毛衣、毛裤、鞋袜,都是妈妈一针一线亲手缝制出来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从睡梦中醒来,妈妈还坐在灯下不停地缝补。家里的生活费,每月都是她本人从乡下辗转到城里肖伯伯的钱庄上去借,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
我觉得妈妈在处理一些大事上,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地方是很明智、很爱国的。1953年,父亲早已在国外,而临摹的敦煌壁画有279幅留在家里。成都的天气阴冷潮湿,母亲很担心那些画会霉烂损坏。在大哥(心智)回家探亲时,母亲和他商量:“是不是把爸爸的画捐给政府比较好?如果霉烂或丢失,我们会后悔的啊!”于是,母亲和大哥就去四川省文化厅联系此事。没想到,当时的官员竟然这样回答:“张先生是自由职业者,没经他本人同意,我们不能接受这批东西。”我母亲急了:“这不是一两张画,而是二百多张画,要是损坏或丢失,也是历史的损失。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捐赠,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委托你们保管?”后来,几经磋商,文化厅方才同意代为保管。事后,母亲去信给父亲,告知此事。父亲的态度很鲜明,完全赞同。几年后,母亲过世了,父亲仍旧没有回来。1962年,文化厅通知我去办理正式的捐赠手续,并颁发奖金四万元;明确说明,两万元给张大千的家属和子女,另外两万元留给张大千归国旅游时使用。但父亲一直没有回来,最后,这两万块钱也分给几个子女了。
母亲到了晚年,雯波妈生的小弟弟心建,也由母亲照管。在她死后,我看到她的日记,不禁伤心地哭起来了:“我年轻时,坐在写字台旁等待我的丈夫回来;到了晚年,我依旧坐在这里盼望我的女儿下班回家,我一生都在期盼和等待中……”还有一段让我更伤心:“我今天真后悔,为什么要打小多毛(心建)?他是个孩子,调皮不懂事。婴儿时,父母就把他扔给别人,没人管。而我呢?长时间没和丈夫在一起,我们都是在感情上被遗弃的人,我们就是孤儿寡母,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我应该加倍地爱他才对。我发誓,今后再也不碰小多毛一根汗毛了。”
还有一件令我挂怀的事。小时候,我曾和妈妈长期住在苏州,父亲在北京。某天,二伯父对妈妈说:“八嫂,你应该带着孩子去看看老八,也正好在北京玩玩。”于是,我和妈妈就去北京看爸爸。爸爸见到我们,对妈妈说:“你也看见了,我很忙,你来北京一趟也不容易,我特别请个人带你们去故宫玩玩,也开开眼界。”没想到的是,爸爸请的人竟是当年宫里的一个小太监。小太监把我背在背上,一边走,一边介绍当年宫里的情形。我没有想到,妈妈把这件事记得特别牢,她幽默地对我说:“十一呀,你还真有福气,小太监背你游故宫啊。”现在,我猜想妈妈当时的心情,可能会有些遗憾——终究还是没能和爸爸一同游玩。
母亲去世前,脑子非常清楚,拽着我的手说:“十一,我和你爸爸的婚姻是你祖母包办的,你爸爸和我没有什么感情,但我们毕竟夫妻一场,在生活上他没有亏欠我一丝一毫,尽到了做丈夫的责任。我在家庭里也做到了我该做的,上侍候公婆,下抚养子女。我们俩只是完成人生的这一幕戏而已。我从没有半点怨恨,这是命中注定的。可是,你是他的亲生女儿,我死后,你就是爬也要爬到美国去,把我心中的话说出来!”
我的第二个母亲黄凝素,出生于1907年,比爸爸小8岁。我爸爸、妈妈结婚时,她只有12岁,还是个小女孩。她是我奶奶娘家的远房亲戚,父母早死,只留下姐弟两人,弟弟叫黄文度。奶奶见他们无依靠,就收留了他们,父亲也很关心他俩。几年后,小女孩渐渐长大了。她与我父亲冲破旧的封建观念,自由恋爱了。她16岁时有了我大哥心亮,接着心智哥、心瑞姐相继出世。凝素妈和爸爸感情很好,也是四个母亲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她聪明伶俐,接受新事物快,而且嗓子特别好,很喜欢京剧,唱得一口程派青衣。
凝素妈一共生育了11个儿女。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有了我第三个母亲。
第三个母亲杨宛君(1917年出生)是1935年到我们家的。她是北京人,唱京韵大鼓出身。姨的身材高大丰满,很像杨贵妃,也有一些文化,而且聪明好学。她每天给爸爸展纸磨墨,看父亲画画,后来也学会画几笔。1941年父亲去敦煌时,她也跟着去照顾父亲。另外,她还唱得一口漂亮的京剧老旦,二胡也拉得特别好。
1949年,爸爸和雯波妈走了,把姨留下了,她当然很苦恼。此后,她的生活来源,一方面是父亲断断续续给她寄些钱;另一方面,她还把父亲给她的一些画拿来变卖。后来,她参加过西南铁路文工团,唱京剧;最后回到北京,自己画一些扇子之类的小工艺品拿来卖,还曾做过某某区的政协委员。姨为人比较直率豪爽,张家晚辈们都很敬重她。
我的第四个母亲徐雯波(1927年出生),曾经是我们家的邻居(在成都郫县太和场)。起初,她和我大姐是好朋友,常到我们家来玩儿。她当时没有工作,有时也帮忙照顾我们几个弟妹。上一辈人的事情,有些我也搞不清楚,后来,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在解放后,我曾给她写过一封信:
雯波妈妈:
您好!
今天我很想和你说说心里话。这些年来我一直很敬重您。我们做儿女的没有在父亲身边,一直是你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老人家。还有,你令我最钦佩的是,你和父亲离开大陆时,带走了凝素妈的小女儿满妹,却留下了你的一对亲生儿女,这体现了你的无私,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最后,我再说一句,如今我已为人之母,而且和你一样是继母,这才渐渐明白了你的苦衷。要别人尊重我,首先得尊重对方,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心声……
十一女 心庆
当时。父亲也看了此信,感触很深,并说:“十一这封信写得很诚恳,你一定要回她一封信,表达你对她的爱。”
父亲走了二十多年了,弟妹们也长大了,我想雯波妈妈也应该有个幸福的晚年。
美食家爸爸
我小的时候非常崇拜爸爸,觉得他像个万能博士,什么都会,写字、画画、写诗、照相、雕刻、搞园林……没想到,他还烧得一手好菜。爸爸做的菜,色香味俱全,吃了还想吃。有的时候,看到他做的菜,还没吃,就想流口水了。
父亲的一生中,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到了香港、巴西、美国,以至最后在台北,宴请宾客都在家里,每次都是他亲自动手安排指挥。事前,他要精心准备菜谱,亲手写菜单。关于菜单,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三张(父亲当年在台北时,和张学良、张群是至交,大家都称他们为“三张”)在我们家聚会,饭还没吃完,爸爸就发现张学良将军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后来才知道,他跑到厨房里,去揭墙上的菜单。原来,他是见到爸爸的菜单做得精致,揭去收藏了。这秘密被大家发现后,都争先恐后去揭那菜单了。
凡是在父亲家里当过差的厨师,离开后出去开餐馆,都是红火得要命;有的连餐馆名字都是父亲给取的,其中一家就叫“青城山”,招牌菜品取名为“大千鸡”、“大千鱼”……俨然大千亲授。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几样菜风味独特,给我的感觉是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红烧狮子头、东坡肘子、宫保鸡丁、火爆腰花、回锅肉、冬瓜盅、一品豆腐、香茶熏仔鸡……
小时候,爸爸也曾教我们姐妹做菜,只是因为我又懒又笨,什么本事也没学会。十姐和十二妹倒都会做不少菜。我这个笨丫头,只学会了一两样,而且功夫不到家,手艺极差。不过,我的确是爸爸的徒弟。
1944年初夏,成都连续阴雨,结果,城里大部分街道被淹,根本无法行走,家家户户的木盆、澡盆,甚至木板都成了临时的代步工具。
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地势低洼,淹得更厉害了。糟糕的是,厨房给淹了,大家连吃饭都困难了,更谈不上吃菜了。老师进不了学校,学校里的学生也出不了校门,被困在学校大约有十天左右,天天吃的都是盐水泡饭,大伙个个都饿得肚子咕咕直叫。
父亲知道后很着急,就让大哥送菜到学校。一天中午,哥哥淌着水,提了一大篮子菜,送到了学校。门房在传达室广播:“张心庆、张心裕,你们家送东西来了,快出来。”我俩看见哥哥高兴极了。到了食堂,哥哥得意地把菜盒盖打开,里边有三四层格子,放着的都是爸爸做的拿手好菜:狮子头、一品豆腐、火爆腰花、莲花白等,菜品摆成的图案是百鸟朝凤、荷花、采莲图,还有牡丹,漂亮极了。
这时,同学们都围过来看热闹。大家都惊呆了,七嘴八舌地说:“这一幅幅美丽的画,我们把它吃掉了,多可惜啊!张伯伯不但是画家,还是美食家呢!”大家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谁都不敢动手下筷子。哥哥说:“你们快吃呀,待会儿莱凉了,吃下肚子会生病的。你们不好意思,那我赶快走了。”他还没走出校门,我们就七手八脚地把盘子一扫而光,个个吃得乐呵呵、笑嘻嘻的,像一群小麻雀,叽叽喳喳闹个不停: “张伯伯的手艺高……”
这是天下最美的午餐,这是天下父母的一颗爱子之心,我永远忘不了,可是我怎样才能报答父亲的深恩?
特殊的“汇款单”
1947年快要过年了,母亲成天忧心忡忡,闷闷不乐,好像有什么心事。母亲常常到大门口看看,期盼着爸爸的来信,或是汇款单。我说:“妈,你急什么!爸爸在外边那么忙,别等了,反正他绝不会把咱们娘儿俩饿着的。”
一天,大概是腊月二十三左右,门口传来邮差的叫声:“曾正蓉,来签字盖章,是挂号信。”母亲高兴极了,取回来急忙把信拆开一看,是两张画。一张是绿梅,绿色的梅花用白边勾勒出来,特别有立体感,朵朵梅花娇艳欲滴。最妙的的是构图,花并没有几朵,但那古老的树根,盘根错节,造型十分奇特。另一张是茶花,颜色鲜艳夺目,红色的花瓣衬托着黄色的花蕊,枝头上还站着一只小鸟。我看了真的爱不释手。母亲在旁,手捧信笺,轻声地念:“记着,请肖伯伯找人把画卖了,以作过年的开支。我一时还不能回来,你们母女安好,过一个祥和的年。”
我拽着妈妈的手:“妈妈,你可不能把那张梅花卖了。我真是爱得要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梅花。你就答应我吧。”妈妈苦笑着说:“十一,你以为我不喜欢你爸爸的画吗?我大概比你更爱呢!把画留下来,开学时拿什么交学费、书费?那你不要上学好了。”我急了:“那怎么行?!妈妈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爸寄画来,就是为了解燃眉之急。我是妇道人家,又不能赚钱,怎么办呢?你喜欢爸爸的画,等他回来以后,好好跟他说,再给你画一张不就行了?”我想想,妈妈说的确实有道理,也就不再闹了。
于是,母亲把画拿到肖伯伯城里的钱庄寄卖。肖伯伯明白我们的处境,把钱先付给了我们,画留下,慢慢想办法。
爸爸那些年真是挣不完的钱,还不完的账,经济负担特别重。有时,我的心里也很闷,替爸爸担忧发愁。我们家本来姊妹就多,负担沉重,二伯父过世后,留下二伯母、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读书、嫁娶,父亲也都一手管了下来。三伯父、三伯母也已年迈,父亲时常牵挂;还有一些爸爸的学生也住在我们家,甚至连他们的家属爸爸都照顾到了。这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我们家就像个无底洞,每年究竟要花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我扳着指头算,父亲至少要供养三十多口人,此外,家里经常是宾客盈门,还常有突如其来的求援者,每年总是入不敷出。但父亲是个乐天派,在我们面前从不叫苦,所以,才有朋友说他是世界上最富的穷人。
这是真实的故事
1983年夏天,父亲在台北病逝后不久,文化部、美协、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纪念展”,并邀请家属前去参观。作为女儿的我感慨万分。
画展开幕的这一天,我随着参观的人流由展览馆门口进入到大厅,举头一望,墙上一幅醒目的巨画是《墨荷》。我被这幅画紧紧地吸引住了,仔细看画上的题款,上款是“润之先生法家雅正”,下款写着“大千张爰”。
这张画把我带回到了二十年前……
1963夏天,我到香港探亲,和父亲在乐斯酒店住了近两个月。晚上,我们父女常聊天、摆龙门阵到深夜,无话不谈,内容大多是家里的亲人、老朋友的近况。
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我跟你说件事,你肯定猜不着我给谁画了张画?”我摇头说不知道。父亲得意地说:“你猜不到吧,我给毛主席画了张画……”我半信半疑,吃惊地打断了他的话:“爸爸,你在开玩笑吧。你在国外,毛主席在北京,你又不认识他,怎么会给他画画呢?”爸爸说:“这你就不晓得了!那年我在香港,革命老前辈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前来找我给毛主席画一张画……”父亲的话还没说完,我就急着问:“你怎么称呼毛主席?画的是什么呢?”爸爸笑了:“我画了一张《墨荷》。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先生喜欢国画。他托朋友来找我要画,也是对我张某人的尊重。每个画家的画都是让别人来欣赏的,当然应该画啦。至于称呼嘛,我的画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称呼题款却很固定简单,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或是乡亲邻里,我都一律称呼先生、女士,或者更熟悉的人就称呼仁兄或某某夫人,再没有别的了。因此,我的题款为‘润之先生’。”我们父女那天晚上谈得很高兴、很开心。
过了些日子,我的探亲假满了,回到家乡,把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的同事朋友,并兴奋地对他们说:“我爸还给毛主席画了画!”
没想到,事隔几年,十年浩劫中,这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张心庆,你爸是叛国分子、反动画家、卖国贼,怎么可能给毛主席画画?你这是给你父亲脸上贴金子,瞎吹牛、瞎编,瞎说也不嫌害臊,说话不怕牙疼?”我悄悄地、伤心地哭了。多少年来,这件事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这阴影怎么也抹不掉,怎么也忘不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1983年,在父亲的纪念展上,我亲眼看到了这幅画。这个谜解开了,我心中的石头也放下了。这不是“谎言”,这是历史,是真实的故事。
(摘自《我的父亲张大千》,中华书局2010年3月版,定价: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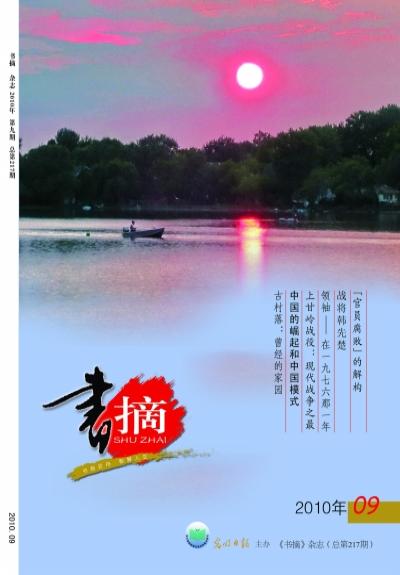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