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地做人
迈阿密,人称“拉丁美洲首都”,66%的人讲西班牙语。有些社区讲西班牙语的人的比例高达95%。不会西班牙语,连上超市买菜都有困难。到迈阿密上学不是我的初衷,虽然上初中时就知道了佛罗里达,有书介绍说,作为人类进化的证据大沼泽国家公园边上的人还长着一条尾巴;上大学时又知道了风流浪漫的迈阿密海滩。是前妻先申请出国留学,选了迈阿密的大学。我算是来帮她打前站的。
香港电视剧常常会有那么一句父亲训斥不孝儿子的台词,“你再不听话,我送你到南美砍叉烧!”可见到拉丁美洲开餐馆砍叉烧在香港人的眼里与清朝时期充军新疆伊犁无异,与右派被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无异。在迈阿密的中国人,许多都是从南美移民过来的。去南美的很多人原籍是广东恩平。
餐馆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企(广东话,即饭店侍应或服务员)“咸蛋黄”,斯斯文文像一个学生,原来却是水手,跳船,滞留在美国。企“瘦马”,志大才疏,从广州几经周折跑到了墨西哥,又从墨西哥边境偷渡来了美国。人家问他为什么那么瘦,他说瘦点正好在香港跑马地当驯马师和骑士。企阿乐,单身大帅哥,原来却在洪都拉斯印第安人部落和一个部落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他告诉我,三个孩子都是他亲手接生的,绘声绘色。我仿佛看到,在那个印第安茅棚里,鲜血淋漓;听到传出的婴儿的啼哭。
企郑生是从尼加拉瓜移民过来的。原来正人君子到处都有,中国有,美国有,南美的中国人也有。郑生就是正人君子的代表。他当企从不迟到早退,从不偷工减料,从不欺骗老板或欺骗顾客。中国乒乓球队访问迈阿密,他还请江嘉良吃了顿饭。老华侨十分热爱伟大祖国,曾和他哥哥一起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说是临别时,送给了接待他们的中国官员每人一块纪念金币。
郑生原来也是一方豪绅,在尼加拉瓜首都附近的一个小镇,拥有一条商业街。不是一两个店铺,而是整条商业街都是他们家的,包括一个电影院。1978年,武装起来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推翻索摩查亲美家族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郑生害怕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土豪劣绅清算,慌慌忙忙把家业变卖,把钱埋到地下,然后跑到了美国。1979年,尼加拉瓜共产政权建立。情况稳定了,郑生跑了回去,把钱挖出来。可惜啊!索摩查统治垮台以后,自然,他们的货币就不用了,所有的钱变成了一堆废纸。郑生一辈子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业,基本都泡了汤;只好携家带口,跑到美国打餐馆工,从头来过。
郑先生的遭遇,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做人要高瞻远瞩地看到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怎么可以被人家杀到了家门口,才慌慌忙忙地把一辈子的积蓄埋在地下,然后逃跑呢?怎么说,都要预先把钱换成美元,然后带着美元跑呀!
谁知道呢?也许,换了美元带着跑,刚好美元也不再值钱了。
有事没事都找警察
从一个环境换到另一个环境,有一个适应过程。我来迈阿密的时候连沃尔玛、道奇是什么都不知道,其他很多东西自然就没有办法明白了。有时候,一个问题要问别人很多遍,别人回答很多遍,才能够弄明白。当然还要对比一下,在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的东西。如果找不到一个跟中国的东西相对应的,就只好干着急,或等以后慢慢再去理解。我知道,遇到的有些东西,一辈子都是理解不了的;也就只好抱憾终身,死不瞑目。
工作上,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一样,有一个适应过程。例如,在国内的时候,那时还没有手机,在街上办事打电话;要找公检法单位的要不就是到民警的交通岗(现在连交通岗都没有了),要不就是到派出所,反正是有事就找警察。
刚到迈阿密的那天,律师朋友拉里刚好有事到加州去了。他给我留了一个条子,说要过几天才回来。这几天如何安顿?那时候出国不像现在,现在出国的都腰缠万贯,那时候总共带的就那么几百块钱。要不先找警察问一问,看他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下飞机的时候,我已经把行李寄存在机场的行李寄存处了。现在是轻装,习惯性地,我截了一辆警车,是一个女警察。我把我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我说我是中国人,主要是带的钱不多,不想住太好的旅馆,看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去住几天?首先,她建议我去难民营,说这里有一个难民营,正住着一拨从泰国来的难民。我问她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更好一点的选择?她想了一想,说:要不去中国餐馆?我说:行!她用警车里的电话跟警察局汇报了一下,便让我坐上警车,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中国餐馆的经理对警察说:“就把他交给我们吧!”警察走后,中国餐馆的经理就把我带到迈阿密大学的中国学生宿舍。
当然,在美国,警察不是随便能找的。大多数情况是警察来找你。要是警察真来找你了,多半不是什么好事。
妻子来了以后,我们住进了迈阿密大学的宿舍。晚上从餐馆打工回来,学校停车场都泊满了,总找不到泊车的位置。我总是泊在停车场的边上,车子有一大半在停车场,却有两个轮子压到了停车场边的草地。我总觉得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买了准许泊车的许可证的。你学校收了钱,总得让我有个泊车的地方吧?
有一阵,警察每天来给我一张罚单,说我压草地了。那天星期天,我正要上班去餐馆打工,看到车前玻璃的雨刷上,警察又罚了我一张新的罚单。一想到一天打工的工钱就让警察罚没有了,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开着车就去追那辆警车,要找警察评一评理。警察没注意我来找她,在另外一个停车场停下来,女警察下了车,一扭头,看到我怒气冲冲地开着车向她冲来,马上就呼叫了增援。很快很多警车就围了过来,我还手里拿着罚单,要跟他们评理。他们要抓我。几个警察商量了老半天,然后一个警察走过来说要逮捕我,罪名是袭警,刑事重罪Felony。
我还要争辩:“这是在校园停车场呀!”他们帮我带上手铐。
“你现在有权不说话,但是你说的所有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警察对我说。
在把我带到警察局的路上,警察问我是什么签证?是不是E签证,有没有外交豁免?那天是星期天,警察局拘留所没人上班。警察对我说,对不起,今天你运气不好,认栽吧!今天这里没人,我们要把你关到迈阿密县的监狱去。警察还对我说:“这不是我要这么做,是上头的意思。”警察还说,“我会叫县监狱的人对你好一点的。”
迈阿密县监狱是大监狱。还关过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国内的监狱,我去过几次,是带外国司法代表团去参观我们的模范监狱。没想到,我也有机会蹲一蹲监狱。还是蹲美国的大狱。
监狱的门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森严壁垒。跟着警察进了里门,一条走廊,边上长条的木凳上放着包装好的三明治,进来的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拿来吃。进到里面,办入狱手续,把身上所有的东西交给监狱保管处,然后要被关到一个临时大间。我跟带我来的警察说,我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能不能让我给我的律师朋友打个电话,警察跟监狱里的看守说了一下,便把我带去打电话,然后,警察就走了。
我的律师朋友拉里在电话上一听我蹲了大狱,他笑了,说他以前看球赛后跟球迷闹事,也蹲过大狱。先蹲着,他会把我弄出来的。
我又给很多地方打电话,给妻子啦,给餐馆啦,给学生会啦。一转眼,晚饭时间到了。看守端来了一个很大的黄色的塑料盒子,打开里面有四格,一格放的是牛肉饼,一格是奶酪通心粉,一格是玉米粒红萝卜,还有一格是水果。量大,起码够两个人的份。难怪街上这么多的人想进监狱。吃完饭,看守要我进里面的临时大间。
里面都是今天刚抓进来的人。除了衣衫不整的黑人、南美人以外,有一位老人是跟他的老太太一块被抓进来的,进临时大间以前,把他们俩分开了。女的另有一区。他们俩是在高级商场偷东西给抓的。里面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白人青年。他在大喊大叫,要放他出去。不知他犯了什么事。天黑以后,看守把我们带出临时大间,去换囚衣,洗澡,然后是分牢房。这时,保我出去的人来了。他把我领出监狱,送回了家。
我的律师朋友拉里没有直接来保我,而是花钱请专门做这一行的人来保我出狱。原来美国专门有人吃这一行饭,专门保人出去的。他们的收费是法定担保费里面的一个百分比。那天他收了律师行10%或150美元。我的保释金是1500美元。中文叫“取保候审”。也就是说,在法庭传唤的时候,我要按时出庭。不出庭应诉,1500美元就没有了。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的警署取回被扣下的车,那个送我去监狱的警察一脸歉意。你们一脸歉意,我以后麻烦事就多了。
律师行先派人帮我出庭。带我上庭应诉的那位律师与审案的法官过去是同事,法庭上互相问好,聊了几句以前的事,控方警察也没来人,法官便把“袭警重罪”打成“交通纠纷”,发配到交通庭。过了两个月,又去交通庭打成“无罪”。从此以后,什么搞绿卡,入籍,申请政府工作“安全清查”都要把这个“无罪”的法庭记录附上。
寻找归属的感觉
临毕业前,我跟一个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在学生会谈论日本文化和文化冲突、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山口百惠和高仓健。我特别推崇高仓健的冷峻、坚忍和刚毅的男人性格。这位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是原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汉语的时候认识的,在北京待过一年,他们对北京比我熟悉多了。当时北京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他们约我第二天到迈阿密当地的电台做一个关于中国的专题节目。
第二天,我们到了迈阿密的WNWS790电台,作为嘉宾,以北京突发事件为背景,回答美国听众打电话来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主要是回答北京的市容和地理环境。电台节目主持人和我主要是回答一些关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传统文化等问题,如中国的户籍制度、档案制度、毕业分配、旅游限制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多人出国留学。留学生放洋,他们对中国的户籍制度和档案制度不信任是自我放逐的原因之一,认为这两大制度,约束了个人才能的发挥,使那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成了“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
美国听众对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的反应比较激烈。当听说没有户口本,就不能在北京住,就没有粮票,没有粮食供应,饭都没得吃,他们就不知所措了。当听说没有档案,就不能调单位、不能换工作,大伙儿都说我在瞎说。他们在电台的节目上问,“档案不是自己编写、自己拿着的吗?”对美国的个人档案管理,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是:九年级(等于我们的高一)开始,学习成绩开始算总分平均分作为入大学的参考;个人病历可以到医生那里要回来,自己保管;求职信是自己写的,是工作调动最重要的档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不一样了,我解释说:“如果原单位拿着档案不放,你就无法到新单位上班;就算新单位给你一个工作职位,你上班了,新单位也不能给你发工资。”所以有不少的人,当年在中国就因为调动工作调动不了,索性跑国外来了。打电话到电台参加我们节目的美国听众对这一档案制度不可理解。而迈阿密的南美人多从拉丁美洲移民过来,特别是古巴移民,对于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还能理解。他们认为,这跟他们从拉丁美洲移民美国要搞一个绿卡差不多,搞身份的档案可是连指纹都要记录在案的;而没有合法的身份,就等于没有户口,就不能工作,就没有饭吃,就那么简单。
对于我这样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个组织纪律的约束。这一点,我在电台上没有讲,听众也没有问;估计就算我讲了,他们美国听众也不会明白。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和辅导员会安排好一切,连睡哪个房间、哪个床铺都有所规定。而到了美国,一下子就“放了羊”,心里头,有点失落。刚来美国上学的时候,老是想要找领导汇报工作、汇报思想。我跟我们商学院的张孙教授说,我要不要定期向她汇报一下,她一脸茫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后来,她要我到他们家参加他们的教会查经班——《圣经》学习小组。我跟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校长助理托马斯也说了汇报思想的事。他好像听懂了一点。他要我每周两个中午去教他学汉语,他每周付我40美元,并请我吃午饭。他还像带研究生那样,每星期给我一批书目,让我去读一些书,并写书评,然后向他汇报。名义上是要我帮他做研究,兼教他汉语;其实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朝对外关系的,汉语根本不需要我教。他只是想用自己的钱,尽自己的力,帮一帮我,使我有那种“找到了组织”,能“汇报工作”的感觉。他不想看着我沉下去。然而,我还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组织”。
他们告诉我,如果真有思想问题的话,要去找心理医生。美国人都这样,如果有对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想家了,有情绪上的苦闷、孤独和失落,有家庭纠纷,要找心灵的“归属”等等,就去找心理医生。
“找心理医生”?这挨得上吗?
小时候看着到处写着的标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都是一些组织纪律。久而久之的熏陶,养成了一种严格要求自己的自觉性和一定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素质,但这正是一个人独立处世所必要的。
现在,我明白了,没有了户口,没有了档案,没有了旅行限制,没有了组织纪律,没有了一切约束,我要找的“组织”就是我自己,一种控制自己情绪和心态的能力。依靠自己吧,现实一点,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抓到什么机会就抓什么机会。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找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守住自己的阵地,尽自己的责任,能为周围的人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那个体制。
就这样,我毕业了。
(摘自《达尔文是对的:一个世界级打工仔的生存笔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2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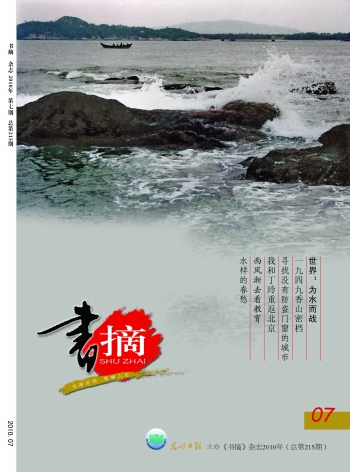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