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9时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炽热的火焰,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汽。
火箭起飞了。
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
开始时飞船非常平稳,缓慢地、徐徐升起,甚至比电梯还平稳。我一看情况远不像训练中想象得压力那么大,心里稍有释然,全身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
火箭逐步地加速,我感到了有压力在渐渐增加。但曲线变化比训练时还小些,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
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
共振是以曲线形式变化的,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心里就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要承受不住了。
当时,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的共振并非正常现象,不应当有这种情况出现。
共振持续了26秒后,慢慢减轻。当从那种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之后,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我感觉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飞行回来后我详细描述了这个难受的过程。经过研究,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之后改进了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神七飞行中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不仅我当时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我一动不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怎么一点都不动呢,甚至眼睛也不眨。
后来,3分20秒,在整流罩打开后,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下,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
当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我感动得说不出任何语言。
我看到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盯着大屏幕掉眼泪,哭得像个孩子。
我看到我的大队长申行运哭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在那里捂着脸哭。我看到我的教练也在流眼泪,朝夕相处的航天员战友们,我的领导们,还有工程技术人员,那一刻大家都在流眼泪。
有这么多人在关心我、牵挂我!那种真诚,那种真情流露,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有种很酸楚的感觉。
我看到了什么
从载人飞船上看到的地球,地球不会呈现球状,而是一段弧,所以我说:“看到地球的弧面。”因为地球的半径有六千多公里,而飞船飞行的轨道离地高度是343公里左右。我们平常在地理书上看到的球形地球照片,是由飞行轨迹更高的同步卫星拍摄而来。
在太空中,我可以准确判断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方位。因为飞船有预定的飞行轨迹,有“星下点”实时标注飞船走到哪个位置,投影到地球上是哪一点,有图可依,就跟电脑程序一样,打开来看一目了然。
不借助仪器和地图,以我们航天课程中所学的知识,也基本可以判断出飞船正经过哪个洲的上空,正在经过哪个国家。
飞船绕地飞行14圈,前13圈飞的是不同的轨迹,是不重复的,只有第14圈又回到第一圈的位置上,以备返回。在离地三百多公里的高度上,向下看时有着很广阔的视野,所以,祖国所有省份我基本都看到了。
我曾遥望我们的首都北京,白天它是燕山山脉边的一片灰白色,分辨不清,夜晚则呈现一片红晕,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
但是,我没有看到长城。
曾经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人工建筑就是长城。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想验证这个说法,我几次努力寻找长城,但没有结果。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我曾嘱咐航天员们仔细看看,但他们也没看到长城。
在太空,实际上看不到任何单体的人工建筑,我接触过国际上的很多航天员,没有谁拿出确凿的证据说看到了什么。即使是巨大的城市,也只能在夜晚看到淡淡的红色。
我也没见到外星人!
上天之前就有人问过我:“如果遇到外星人,你会对他说点什么?”返回地面后,许多青少年朋友也多次问:“你见到外星人了吗?”每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很感兴趣地笑。其实外星人至今还属于科学幻想的范畴,我想象不出,会有一个像电影上那样的、长着三角形大脑袋的外星人,趴在舷窗外向里张望,实在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情形;或者是外星人站在他的飞船外跟我打招呼,我想这种情景大概不会发生。
也有人问我,是否看到了卫星或其他航天器。我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因为在设计轨道时要避开其他的航天器。
但在太空中,我的确看到了类似小尘埃的东西。我看到不时有棉絮状的物体从舷窗外飘过,小的如米粒,大的像指甲盖,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感觉不到这些东西的任何撞击。
不知道那是些什么,我认为那些也许是灰尘,高空可能不那么纯净,有一些杂质,也有可能,是太空垃圾。那些物体在飞船外面,我无法捕捉回来,至今还没弄清到底是什么。
我在天上的任务之一是拍8分钟的录像,我分两次把拍摄到的地球景象实时传回地面,每次图像传到地面时,在我的耳机里都会传来指挥大厅里人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后来,从我带回来的很多录像中,提取了5分钟,给中央电视台播放,其余的片段全部由我们单位保留,至今一直没有公开。
在太空,我拍了很多照片,带回来一百多幅。实际上我拍的不止这个数,我对效果不太满意,又担心存储不够使,在太空时我就删掉了。出于控制携带总重的考虑,我飞行时只带了一个卡片相机,500万像素,器材有些简陋。许多壮丽的景色无法拍下来,比如日出和日落。
其实,我一个人在上面拍照和录像费了很大周折。拍摄外面或舱内情形时相对简单,我只需要把自己在窗边固定好就行。但我想拍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情形,就不那么容易了。
开始时我把胳膊伸出去,把镜头对准自己,自拍。但这样只能拍到我的脸或者身体的局部。后来想把摄像机放在什么地方,但失重会让机器飘浮,无法稳定拍摄。试了几次都不成,我很着急。
后来终于在工具包里找到一个胶带,我把摄像机用胶带粘到前仪表板上,对着自己拍摄。拍工作场景,也拍自己吃饭喝水,我希望把这些拍下来后给其他航天员看,这样,下次再执行任务的时候,就知道在飞船里究竟是怎样的状态了。
太空神秘的敲击声
作为首飞航天员,除了一些小难题,别的突发的、没有预案的、原因不明的情况还有许多。
比如,当飞船刚刚入轨,进入失重状态时,这个阶段,百分之八九十的航天员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这种错觉很难受,我明明是正着坐的,却感觉脑袋冲下。如果不克服这种倒悬的错觉,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很难受,而且还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的完成。
在地面没人提到过这种情况,而且即使知道,训练也无法模拟。相信在我之前邀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有过类似体会,但他们从没有跟我交流过。
在这种情况下,没别的办法,只有完全靠意志力克服这种错觉。想象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眼睛闭着猛想,不停地想,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几十分钟后,我终于调整过来了。
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升空后,航天员都产生了这种错觉,但他们心里已经有数,因为我跟他们仔细讲过。而且,飞船舱体经过了改进,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类似于家庭房屋的简单装修,天花板是白色的,地板是褐色的,这样能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错觉。
在飞船飞行过程中,外面强烈的闪光考验了我的神经。
飞船出了测控区,进入短暂的夜晚。我坐在座椅上,突然发现窗外特别的亮,而且一闪而过。我当时吃了一惊,想:哟,这是什么啊?怎么会这么亮呢?
我顺着舷窗向外寻找,闪光却消失了,看不到了。我揣摸,是不是飞船有什么问题?我迅速返回到仪表板前,翻看各种数据,检查飞船的各个系统,并没发现任何异常。
因此,当飞船再次进入阴影区(相当于黑夜)的时候,我早早就在舷窗边上等着,但闪光并没有出现。
在太空中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感觉到不正常,心里肯定会紧张,少不了要胡思乱想。
在第三次进黑天之前,我又早早就趴在窗户那里等待,后来贴着地面有一个光柱一闪,将太空瞬间照亮,又消失在黑暗中,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是地面上空的雷电在打闪嘛!那耀眼的亮光不是别的,而是地球上的闪电,是很简单的一个自然现象。
找到了原因,我不由松了口气,刚才还紧张得出汗,这时却可以饶有兴味地观赏闪电的奇诡景象了。
我在太空碰到另外一个仍然原因不明的情况,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敲击声。这个声音也是突然出现的,并不一直响,而是一阵一阵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毫无规律,不知什么时候就响几声。不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而仿佛是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无法准确描述它。
因为飞船的运行一直很正常,我并没有向地面报告这个情况。但自己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飞行,生怕哪里出了问题。每当响声来的时候,我就趴在舷窗那里,边听边看,试图找出响声所在,却没能发现什么。
什么问题都没有,没事它响什么呢?飞行时,对声音变化是很敏感的。飞船哪个地方稍稍有点什么动静,心里都会紧一下——嗯?怎么会有这个动静?嗯?风机的噪声好像比刚才大了呀?
敲击声一直不时出现,飞船也一直正常。我想,虽然总响,也没怎么样啊!后来就不太当回事,不担心它了。
回到地面后,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声音有许多猜测。技术人员想弄清它到底来自哪里,就用各种办法模拟它,我却总是听着不像。对航天员的最基本要求是严谨,不是当时的声音,我就不能签字,所以就让我反复听,听了一年多。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确认,那个声音再没有在我耳边完全准确地再现过。
在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这个声音也出现了,但我告诉他们:“出了这个声儿别害怕,是正常现象。”
由于从来没有人体验过,所以我在飞行过程中经历的好多心惊肉跳的瞬间,等回到地球后分析,发觉其实并不复杂。虽说航天员的心理素质高于常人,但说实话,那时还是会本能地紧张。
归途如此惊心动魄
5时35分,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就像刹车一样。
飞船先是在轨道上进行180度调姿——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这就需要180度“调头”。
“制动发动机关机!”5时58分,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此后的飞船飞行并不是自由落体,而是使用升力控制技术,按照地面输入的数据,瞄准理论着陆点,依靠飞船上的小型发动机不断调整姿态,沿返回轨道向着陆场飞行。
所谓升力控制技术,就是当飞船进入大气层时,它的气动外形(与飞机外形设计是同样道理)在空气中产生升力,让它沿着一个缓慢的抛物线飞下来,它是可控的。
如果出了故障,升力控制失效,飞船返回就会是弹道式的,不可控地下来。比如2008年4月19日,韩国的李素妍搭乘俄罗斯“联盟TMA-11”飞船,与一名美国航天员和一名俄罗斯航天员一同返航时,飞船就是以弹道式着陆的,当时偏离预定地点420公里,航天员除了遭遇颠簸,还承受了最高10个G的过载,据称李素妍因此受伤。
6时04分,飞船飞行至距地100公里,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
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很大,遇到空气阻力,它急剧减速,产生了近4G的过载,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压力。这种情况我们平时已经训练过,身体上能应付自如,心理上也不会为之紧张。
让我紧张以至惊慌的另有原因。
首先是快速飞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接着在通红的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飞船的外表面有防烧蚀层,它是耐高温的,随着温度升高,它就开始剥落,实际上这是一种技术,它剥落的过程中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我学习过这个,知道这个原理,看到这种情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但接着看到的情况让我非常紧张。我看到右边的舷窗开始裂纹。外边烧得跟炼钢炉一样,玻璃窗却开始裂纹,那种纹路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之后那种小碎块一样,这种细细的碎纹,我眼看着它越来越多……说不恐惧那是假话,你想啊,外边可是1600℃~1800℃的超高温度。
我的汗出来了。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飞船急速下降,跟空气摩擦产生的激波,不仅有极高的温度,还有尖锐的呼啸声,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还不停振动,里面咯咯吱吱乱响……外面高温,不怕!有碎片划过,不怕!过载也能承受!但是一看到窗玻璃开始裂缝,我紧张了,心说:完蛋了,这个舷窗不行了。
当时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嘛,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一个裂缝,然后高热就让航天器解体了。现在,这么大一个舷窗坏了,那还得了!
先是右边舷窗裂纹,等到它裂到一半的时候,我转着头一看左边的舷窗,它也开始裂纹。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哦——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
回来之后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是这个涂层烧裂了,而不是玻璃窗本身;为什么两边不一块儿出裂纹呢?因为两边用的不是同样的材料。
以前每次做飞船发射与返回的实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烧灼,舷窗被烧得黑漆漆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而如果不是在飞船里面亲眼目睹,谁都不会想到有这种情况。
此时,飞船正处在“黑障”区,离地大概80公里到40公里。当飞行到距地面40公里时,飞船飞出“黑障”区,速度已经降下来了,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减弱。一个关键的操作——抛伞,即将开始。
我坐在里面,怀抱着操作盒,屏息凝神地等着配合程序,到哪里该做什么,该发什么指令,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
6时14分,飞船距地面10公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
这是一个激烈的动作。能听到“砰”的一声,非常响,164分贝。我在里边感觉被狠狠地一拽,瞬间过载很大,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
接下来是一连串快速动作。引导伞出来后,它紧跟着把减速伞带出来,减速伞让飞船减速下落,16秒之后再把主伞带出来。
这是一个二十几秒的连续过程,人在里边是什么感受呢?
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了。随着一声巨响你会感到突然一减速,引导伞一开,使劲一提,这个劲很大,会把人吓一跳,减速伞一开,又往那边一拽,主伞开时又把你拉到另一边了……每次都相当重,飞船晃荡很厉害,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他们不给新航天员讲这个过程,就怕他们害怕。我回来讲了,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每一步都讲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告诉他们不用紧张,很正常。
我们航天员心里是很重视这一段的:伞开得好等于安全有保障了,至少保证生命无虞。所以把我七七八八地拽了一顿,平稳之后我心里却真是踏实——数据出来了,这个时候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
后来,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都有红外,能看着开伞,这比较让人放心。我那会儿还没红外,地面人员也看不到,完全靠我凭感觉报告,我实时告诉地面:我听到什么声音,感受到减速,感受到开伞,我判断伞开得正常,因为速度多少多少……
接地时,我第一个要做的是判断是否落在实地,第二个要做的是切伞。伞不切的话,它会乘风带着飞船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这个1200平方米的大伞带着像球一样的返回舱,顺风跑起来汽车都追不上,而且它还边跑边颠簸,人在里边会被颠坏。
飞船离地面1.2米,缓冲发动机点火。接着飞船“嗵”的一下落地了。
我感觉落地很重,飞船弹了起来,在它第二次落地时,我迅速按了切伞开关。
飞船停住了。此时是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
落地后飞船倾倒了,我是头冲下,脚朝上,动也动不了。总不能就这样等着来人吧!等报告完后,我稳定了一下,之后把束缚带解开,一用力翻了下来。
过了几分钟,我隐约听见外面有人喊叫的声音,手电的光从舷窗上模糊地照过来。我知道:他们找到飞船了,外边来人了!
我心里那个高兴啊。
(摘自《天地九重》,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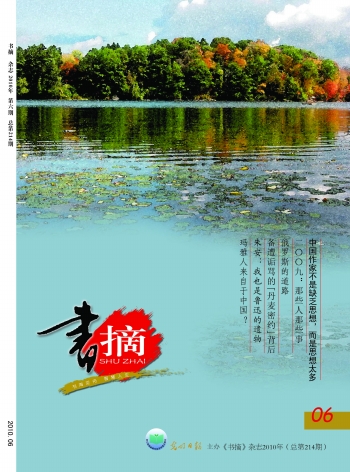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