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夏初的天气。
我爱看树和草的鲜嫩的绿叶子。
古人说:“春秋多佳日。”今人鲁迅先生又说:“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由后之说,则北京这地方未免可怜了,连多佳日的季候都没有。但是我对此并没什么不满,因为我喜欢夏初。
一天的上午,我走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住户的门都关着,使我几乎要遍叩所有的门,问一问有没有人在里面住着。老槐树的阴凉是那么浓密,我又疑心地下的树影儿都是绿的。
在青岛时,常常跑到山顶上看山下的树一碧无际,望去一直接连着大海。在济南时,常常立在铁公祠前,看出水一筷子来高的苇子芽。现在只有这样的槐阴供我玩赏了。然而我依然满意,因为这已经足够使我感到夏初的味儿了。
有人说我现在是住在乡间,所以这样想;假使住在北京城里,便另是一种情调了。
我意不然。
我也常进城。在南城有一个古老的会馆,屏兄占据着一间屋。半年以来,一星期内我倒有两三夜要住在那里。窗外的三棵马缨树——北京人叫做绒花树的——已经长出了绿叶。因为是北房,又没有廊子,正午的太阳穿过了树叶,洒在窗纸上。吃完午饭,屏兄歪在床上睡晌觉。我歪在竹子躺椅上,随手在架上拉过一本书来看,有意无意地。院子里太阳是那样好,马缨花的嫩叶微微地在摇动,绿光便闪到我似睡非睡的眼里。大门外时常有汽车鸣着各种不同的声音的喇叭驰过去,但我也觉得很辽远,很模糊。屏兄也香甜地睡着,轻轻地打鼾。
假使没有朋友来,我们两人常这样地过去礼拜六的一下午。
上次进城,看见屏兄的案头瓶中,还供着花。
“啊,芍药!”
“在市场买来的。”
屏兄似乎很高兴。他总嫌他的屋子狭小,没有生气。狭小,没法了。没有生气,他想用花来点缀一下。然而他忙,忙得没有养花的余闲。这次买来芍药做瓶供,在他许是以为不但添生气,还有些春意了吧。
芍药是有名的“殿春”花,但在北方,有时开时已是夏初了。屏兄似乎不曾理会到这里。他实在忙,忙到连去公园或北海看牡丹的工夫都没有。在北京,倘自己住的院子里没有花,再不去北海或公园走一走,真不知春天的来临与归去的。我似乎曾对屏兄说过这样的话。他却说坐电车时,看见马路两旁的柳树发了芽,也感到了春意了。但也很怅惘于始终没有工夫到公园或北海看看牡丹。现在有了芍药在案头,怪不得他高兴。他总以为这是春花,也不管它开在什么时期。
奇事又发现了,在一个大的纸盒子盖里,还有几条长成的蚕。
“哪里来的这个?”
“学生送给的。”屏兄微笑着说,仿佛又很高兴。
我有许多年不曾见到那么大的蚕了,于是就坐下看蚕吃桑叶。我长到这么大,才知道蚕的嘴是竖着的。
屏兄出去了。不大的工夫,又进来,手里拿着桑叶。原来在院子里的南墙根下就长着丛生的一人多高的桑树。屏兄把新采来的叶子撒上,不久,蚕都抬起头来,用了胸前类似乎脚的东西抱了叶子的边缘,细细地嚼食。一会儿,叶上就是一个缺口,半圆的。又整齐,又细致,像用了指甲掐去了一块儿似的。
“咦,怎么少了两条?”屏兄不自觉地喊出口来。但随即在半干的大叶子下,发现了两个茧。一个长圆的,一个中间凹进去,有如一个亚腰葫芦。
“这个怎么这样?”
“日本蚕好做这样的茧。”屏兄答。“半天的工夫,没看它,不想竟结了茧。”他又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吃过了晚饭,没有事,仍旧看蚕。有一条爬到盒子的旁边没有桑叶的地方,翘起头来,静候着什么似的,时而又把头左右地摇摆。
“这一条怎么不吃了?有病了吧?”
“大概是要结茧了。”屏兄答,“结茧需要找一个角落的地方方好。有如蜘蛛的结网,先要把几根主要的线附着在别的事物上,才能结成。亏得那两个蚕巧,就在那个大桑叶下结成了。”
我抓过纸烟来吸。忽然想:把那条蚕装在盛烟的纸盒里吧。于是把那所有的余下的烟都倒出来,把蚕装进去,只开着盒的一端。
“干什么?”屏兄问。
“让它在这里面结茧呀!”我答。
屏兄掀须大笑了,仿佛觉得我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子。
我真有点像小孩子了。隔十几分钟,便把烟盒子拿起来看一看。一会儿,见蚕的头向着那一端;一会儿,又向着这一端,一会儿,又见里面有了蚕矢,而且盒子也湿了一大片。蚕在里面,也忙起来,不住地左右上下摇摆它的头。
“盒子里怎么湿了呢?”我问。
“大概是它排泄的吧。想来它必须排泄净尽,方可结茧;否则自己结在茧里之后,岂不太费事了,况且它又不能随便出入的。”
我们两个都笑了。
待到睡觉的时节,我又看了看,盒子开着的那一端,已经被几条丝稀稀地络起来了。
第二天起床之后,才穿上鞋,便拿起盒子来看,里面是一个茧。我把那一端也打开了,冲着亮一照,却见茧还很薄,清楚地看见蚕在里面摇摆它的头。
又有一条也不吃叶子了。这回是屏兄把它装在一个盛牙膏瓶子的纸盒里。但下午我出城时,看了看,它还没有结茧。
忘记是星期几。到一个小饭铺子里去吃午饭。却见柜台上,用玻璃瓶子供着两支盛开的芍药,比屏兄所供的又大又艳丽。我问伙计在哪里买的。
“在街上。”他回答。
“随时有卖的么?”
他稍一沉吟,便说:“您看着好,就拿去吧。” 、
“谢谢你。”我很高兴。
他笑了。
饭后,我就真格拿了一支回家。在老槐树的阴下走着时,我嗅着一阵一阵的甜香。一个蜜蜂儿飞来,落在花上。我摇动那支花。但蜂儿似乎不觉得,在花蕊里连打几个转身,全身都是粉,益发黄了。在走近寓所的时候,不知何时,蜂儿又飞走了。
瓶子里注上水,把花也供在书桌上。下午,鹰北来坐着,看见了,便说:“你在什么地方弄了这样的花?盛开的,不好。不久,就要谢。”
我没有答应什么。
听差的送进一封信,屏兄的。拆开看时,是报告那条蚕在盛牙膏的纸盒子里结茧的事,而且这个茧特别大。又说马缨花已经有了花蕾了。
我回头看,瓶中的芍药,果然谢了;案上就有许多片零落的花瓣,虽然香甜依然散布在小的书室中。我因为屏兄信上说马缨花有了花蕾,便想看看我这个小院子里的那两棵马缨有花没有。看的结果是没有,大概因为树还小不会开花的缘故。但我并不失望。看见树上的叶子绿得有如涂了油,便已觉得高兴,不知怎的总仿佛看见了一个青年健康地转入了中年。
1930年6月
(摘自《诗书生活:顾随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定价:3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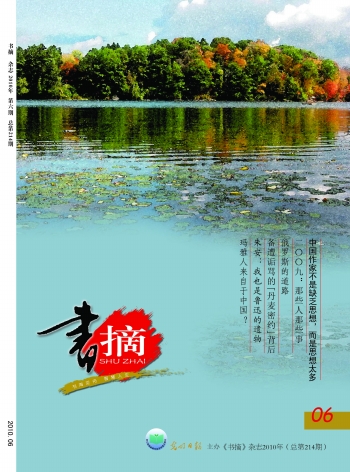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