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
记者:前一段时间,作家王安忆针对当前中国小说缺乏故事缺乏想象力提出批评。写小说的人需要想象,看小说的人需要想象,编小说的人也需要想象。您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意见?最需要的是什么?最缺乏的是什么?
莫言:这很难回答。实事求是地评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文学逐步回到文学的本位,过去很多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被带到文学里,现在大家都慢慢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像大浪淘沙一样一步步过来,80年代很多红得发紫的作品,现在已经无人关注,作者自己回头看,也会觉得自己浅薄幼稚。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希望作品能成为拨乱反正的工具,能够提出时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后来大家渐渐认识到,这些恐怕不是文学要承担的责任。我的观点大概是在唱反调,不合时宜。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国作家缺乏思想,我认为不是缺乏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很多作家经常把自己错以为是国家领导人、救世主,肩负着改变社会的历史责任。而且经常在作品中灌注那些所谓的伟大思想,结果就是思想伤害了艺术。我始终认为好的小说是作家无意识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高举着思想的大旗,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时,那基本上是在发疯,伟大作品、有思想的小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我们现在评价那些伟大作品的思想性,作家写作时未必意识得到。比如《红楼梦》,每一个读者读完它都有自己的结论,毛主席从中看到了四大家族,看到了阶级斗争。另一个人可能看到了男女爱情,道学家和流氓看到的又不同。也有人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的思想,看到了封建主义的必然灭亡。这些是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想到的吗?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最初动机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们后来所想到的这些所谓的思想。他绝对没有想要通过《红楼梦》来反映封建制度必然要灭亡,资本主义必取而代之的意图,如果想到,他就不是曹雪芹而是马克思了。但你不能说毛主席理解得不对,你不能说某一个红学家的解释是错误的,文学的魅力所在,它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者,就在于它能被误读。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被误读。对作家而言,如果想得太多,思想大于形象,就犯了可怕的毛病。好的作品是形象大于思想,唯如此,作品才能超越时间、地域、阶级的限制,才可以走向世界。你如果让所有的人只能从中读出一个阶级斗争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那这部小说的价值除了让无产阶级来读,或者让国民党当做反面教材来读,别的人还能读出什么?一部作品能吸引读者,能变成世界的文学,它没有那么多限制,它是从人物出发的,从感觉出发的,它描述的是人类最基本的——不论是白种人黄种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能理解的共同感情。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流传了几百年,每个时代都在读,每个时代都在解释。它把生活当中最本质的东西描述出来了,把人身上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讲,作家最好没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写不好。这一观点经常被人批评,被很多人嘲笑。我实际上也是一种拨乱反正,一种过正的矫枉。我觉得现实情况是,浅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装模作样的思想太多了,实实在在的思想太少了;虚伪的思想太多了,诚实的思想太少了。你不能从思想出发来写小说,你得从人出发来写小说;你不应该从理性出发来写小说,而应该从感性出发来写小说。这又带出我的另一个谬论,即:作家理性思维能力越强大,其小说越缺乏感染力。当然,我如果完全没有思想没有逻辑,那我该进精神病院了。我意识到一些东西,但我不应该采取直露的方式来表现。我对很多事情想不明白,但我不能说没有想明白的东西就不能写,如果我对这种生活现象了如指掌,我就可以从感觉出发来写,从人物出发来写。有切肤之痛、切齿之恨、丢魂落魄之爱,或者有看破红尘之凄凉,管它有没有思想,都可以放手写来。我觉得这是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一种方式。
对作家毒害最严重的是权力和地位
记者:您曾提到澡雪精神,古希腊哲学家有一句话,说冷水让人精神,热水会让人昏昏欲睡。从中我有两个问题,一是作家境遇的改变对其创作的影响。您现在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现在这种优裕的生活和众星捧月的局面,有没有影响到您的创作?
莫言:说到澡雪精神,(澡雪精神,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一种说法,把身上、头脑中龌龊的沾染了世俗观念的东西像用雪洗澡一样洗去,使思想得到升华净化。)我原来觉得很抽象,来日本后觉得具体化了。我们下半身在热水里,上半身在冰雪里,这种环境的变化让我们产生一种非常伟大的感觉。外界环境的变化确实带来心境的变化,大概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作家境遇的变化——他过去没钱现在有钱了;他过去没书房,现在有书房了;他过去连笔都没有,现在有电脑了——这些变化肯定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但我觉得这种外在的变化还不是最重要的,对作家毒害最严重的是权力和地位,比如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了一个领导人,他想要保持不变是不可能的。香车宝马,前呼后拥,权力的腐蚀,跟鸦片对人的腐蚀一样。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中国从前苏联学来的,文学的功能给予了无限的夸大,作家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极度的提高和极度的夸张,前苏联有许多人民作家,我们的一些人也动不动说“我是人民诗人”,“我是人民艺术家”。当他坐火车让他坐硬座时,他说“我是人民艺术家”;当他住酒店没有热水洗澡时,他也说“我是人民艺术家”。这才是非常可怕的。
2001年,我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论坛作一个演讲,题目叫《作为老百姓写作》,我们都知道,现在流行的口号是“为人民写作”,替老百姓说话,做老百姓的代言人,这样的写作态度好像是主流,显得很谦卑,但我觉得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就像我们有的领导干部说是人民的公仆,是这么回事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作为老百姓来写作,我反映的就是我个人感受到的痛苦。当我真切地感受到老百姓所能感受到的痛苦时,我写我个人的痛苦,写我个人的愿望,也就代表了老百姓的痛苦和老百姓的愿望。我说的是我的心里话,恰好也是老百姓的心里话,这两个点契合了,这个作品就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也能引起非常好的反响。如果你千方百计地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居高临下地看着芸芸众生,然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政府,批评党派,这未必是在替老百姓说话,实际上你是在作为一个高等人说话。
记者:但是作家和老百姓不是一回事。
莫言:这种状况确实是存在的,我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要被眼前种种东西所迷惑,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纠正错误的立场,使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多地保持草根性,即所谓的老百姓气息。当然你现在把我赶回到高密东北乡去也不太现实。
记者:但可以去体验生活。
莫言:那种体验也是肤浅的,我向来讨厌为了创作去体验生活。这个问题与人的出身和本质有关系,当然有些出身低贱的人一旦爆发,会变得非常的坏,虚荣浅薄。但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时刻不忘根本。我是时刻不忘根本的,我可以坐飞机的头等舱,但我也完全可以坐牛车。可以住高级饭店,十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我也睡得很香。
记者:适度的贫困,是人生的财富。在您声名鹊起的二十年中,有没有渴望过权力?包括话语权、支配权。
莫言:应该是没有,我从来是渴望被别人领导,从来没有渴望当官。年轻的时候不是没有,比如在部队的时候,想当连长,想提干。当我三十多岁成为师职干部时,我也曾经暗自得意过。但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还对权力恋恋不忘的话,那就荒唐可笑了。
我想做一个坦率谦虚的人
记者:你是否关心其他中国作家的创作?你对当代中国小说写作的现状如何评价?
莫言:前些年年轻时,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我曾经撒谎说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好像那样就显得不同凡响。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应该努力做一个坦率的人。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都在我的关注之内。我不开列名单是因为这个名单会漫长得如一条红绸腰带。我阅读他们,第一是想向他们学习,第二还是想向他们学习,第三还是想向他们学习。人到中年,我除了想努力争做一个坦率的人,我还想努力争做一个谦虚的人。做一个坦率的人是为了夜里不失眠,做一个谦虚的人是为了能够进步。至于当代中国小说写作的现状,一个谦虚的人是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
记者: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其获奖演说中提到你的叙述语言令他羡慕,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称赞的?我还想问的是,你认为自己的语言特色特别在哪里?尤其是与其他汉语写作者相比较。
莫言:大江健三郎精通多种文字,但好像不能阅读中文。他读过的大概是我的作品的日文译本。这说明,我的作品的日文翻译者是很出色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忠实于我的原著,但我知道他写出了很好的日文,否则也就不会得到大江的称赞。所以我现在拿不准大江称赞的是我还是译者。
你让我自己评价自己的语言,其实是给一个正在努力想学习谦虚的人出了一个难题,更给一个正在努力争做坦率的人和谦虚的人出了一个双重的难题,知难而进从来就不是我的天性。
(摘自《莫言对话新录》,选自书中《写作时要调动全部感受》和《我想做一个谦虚的人》两文的部分内容。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2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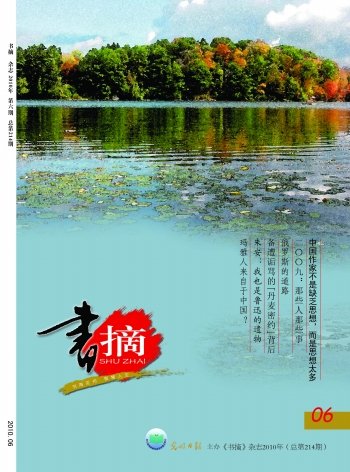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