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沛霖:以学为友,不改其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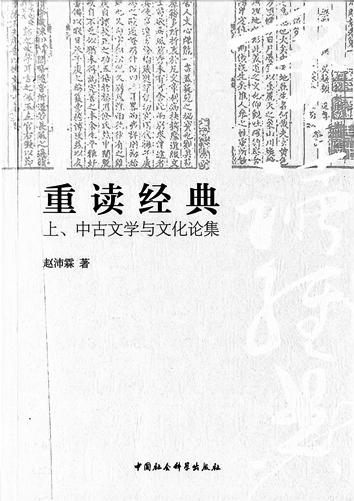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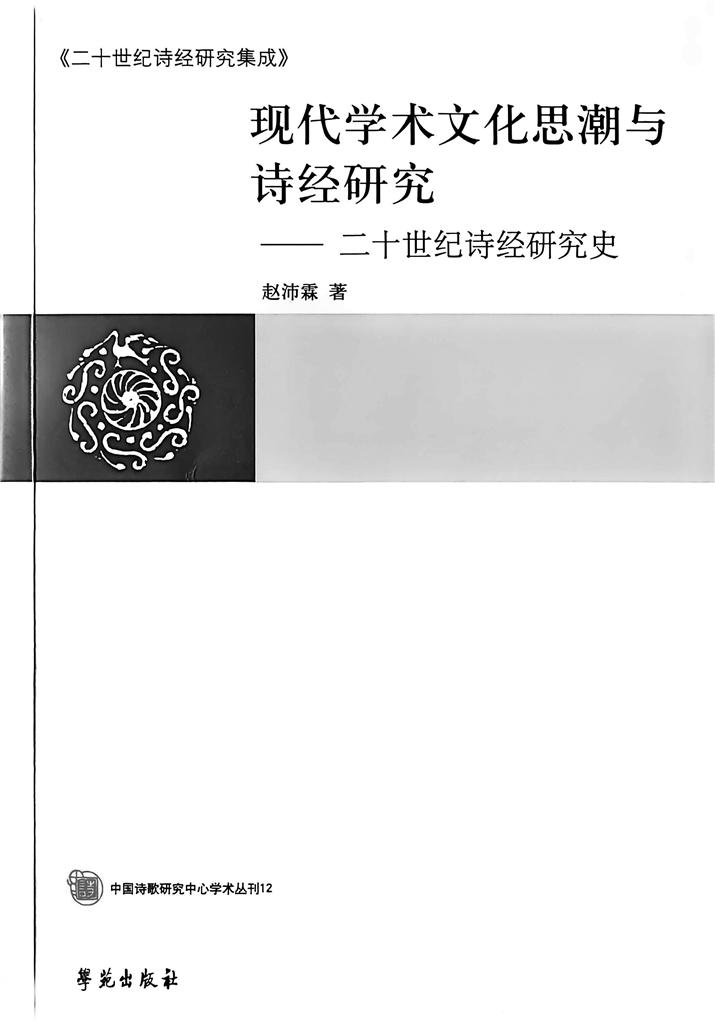

在天津社会科学院,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位瘦癯矍铄的老人,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装着满满的书,默默走过,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如果有年轻人走到他身旁,问询专业问题,他会立即春风化雨,从《诗经》《楚辞》到治学、作文,娓娓道来。两代人远离外界的扰攘喧嚣,沉浸于学问之中,又是一景。
这位老人是赵沛霖先生,今年88岁了,健康状况虽不如前,但他每天还是雷打不动地读书、思考、写札记。外人看来,他的生活很单调,但他不以为意,始终“不改其乐”。
“学术的快乐是追求和探索的快乐,也是发现和创造的快乐。”他曾对后辈讲述读书和科研的快乐,“投身于学术研究既可享受过程带来的生命充实感,又有成果面世带来的成就感:学术研究给每一位有志于此者加以双倍的回报。”
“读书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
有人问赵沛霖,如果人生的道路能够重新选择,你还会不会从事文学研究?他答:“读书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怎么会后悔?”
在赵沛霖看来,文学研究接触的是高尚、杰出的灵魂。像《诗经》里的变雅作者,他们关心民瘼、关怀现实,把感悟和治道等形诸文字,堪称仁人志士。再如屈原,将实践理性和崇高道德完美结合起来。其他如陶渊明、郭璞、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都是他们高尚心灵的体现。研读这些文学家人生和作品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
他还说,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大都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才得以沉淀和流传下来,涉及人心灵深处的情感。因此,进行文学研究就不能只做简单概括,必须融入真切的喜怒哀乐,去切实地感受美丑善恶。这是单靠理性抽象无法做到的,也是其他学科的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从事文学研究,是幸运的事情,也是一项时时处处能被感动的事业。他对此深有体悟。
赵沛霖自幼喜欢读书。早年,他就读于天津市第三中学,积极报名成为学校的业余图书服务员,在服务同学的同时,自己也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诗词名篇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新文学作品。同时,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普及性读物以及哲学、政治理论书籍等,他也读而不倦。到了高中,他读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西方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翻阅了大量西方宗教、建筑和绘画等方面的通俗读物。
1959年考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后,赵沛霖读书更具系统性。大学四年里,他严格自律,制定规划,广泛研读有关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类书籍。他以超出常人的磅礴之力,长期浸淫在中外名家典籍中,极大地拓宽了视野,努力摆脱前人的窠臼和成见,形成了影响一生的独立思考习惯和理性批判精神。
大学毕业后,赵沛霖在中学执教17年,直到1980年,人到中年的他通过考试调入天津社科院,开始了真正的学术研究。此时,他既欣喜又惶恐:欣喜是因为自此成为专职学者,能够从事自己挚爱的科研工作;惶恐则是由于自觉“半路出家”,学养不足。对此,他经过冷静思考,深刻分析了个人的客观实际,认为治学须有长远打算,最忌急功近利,所以必须切实地从读书、问学等方面加以提升。
他又开始了新的书山攀登计划,重点选择四类书籍“攻关”。一是从基础性的字句训释入手,全面系统地重读先秦典籍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经典。二是在宏观的理论思辨方面寻求突破,结合研究课题精读有关原始宗教、原始文化、神话和美学的中外论著。三是阅读有关方法论和介绍治学经验的论著,注重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考察前人的研究成果。四是注重泛读“无用”书,主要是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哲学以及中国现当代哲学方面的著作。
很多人认为读书是件苦差事,赵沛霖却从不以此为苦。他说,优秀的书籍,就像暗夜中的灯塔,能让迷惘和碌碌的人们,获得光明正确的方向和事半功倍的路径。
1998年,赵沛霖退休了。别人退休,往往心有不舍,他却庆幸自此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研究。他在《郭璞诗赋研究》的《后记》中写道:“退休以后搞学术研究,没有诸如职称评定、量化考核等带来的压力和限制,更由于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这样的‘赔钱书’选题,自然也就没有出版合同的约束:题目任凭学术兴趣自选,进度听其自然,随兴所至,涵泳玩索,泛舟学海,优哉游哉!”
有老朋友跟他讲,年轻时因为工作繁忙,想去的地方不能去、想看的风景不能看,好不容易退休了,怎么还是困在书斋之中?言语之间都是惋惜,但赵沛霖认为,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无数,构成了另一道精神世界中的奇异景观。有生之年不多读一些、多领略一些,那岂不是更大的遗憾?所以,他在退休后反而重新条列了读书的“心愿清单”,把要突破的学术问题一一纳入日程,绘成“作战图”,毅然决然地在学术道路上勇猛精进。
“学术探索和创新的快乐持久而热烈”
学术的快乐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40多年,赵沛霖把学术研究比作探险,先后在《诗经》《楚辞》、先秦诸子、历史神话、六朝文学等方面深入探索,“获宝”良多。
他说,进入新领域,自然会产生新刺激、引发新兴趣,但是光有兴趣可不行,还得能发现新问题,寻找到突破口。能发现大问题固然好,但小问题也不能放过。一些小问题解决好了,也能形成大著作。他把发现问题比作开矿,一些小问题就像矿苗,外表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深挖下去,很可能会发现大矿藏。
赵沛霖的成名之作《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一书,就始于兴的手法这个小问题。关于《诗经》兴的手法,朱熹提出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闻一多认为兴就是“绕弯子”,就艺术审美而言,已基本形成确论。对于这个已有定论的小问题,当代学者很难再有创新突破,赵沛霖却作了更深的探索。
他将美学领域的审美心理历史积淀说与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相融合,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兴的起源进行考察,认为在原始诗歌中不存在托物寄兴、体物缘情的艺术审美,其表现方式更多的是“直言其情”和“直言其事”。在全面分析《诗经》和逸诗中的原始形象后,他进一步提出原始诗歌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诸如鸟类、鱼类、树木和虚拟性动物兴象等,是宗教观念内容通过历史积淀形成的习惯性联想并逐步外化为艺术形式的结果。这一观点提出后,很快引起学界关注。
赵沛霖经常说,搞文学研究时,开展一个新课题就好像到了一个新世界。新的作家、新的作品,最先带来的是强烈的新鲜感。而对待新领域、新问题,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允许有一点儿倦怠或松懈。
赵沛霖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推动了诗经学的发展。一方面,他从原典、文本出发,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去观照历史,审视成见,破除偏见,务求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许多令人信服的新创见;另一方面,他也有着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站在整个学科建设的高度,从面临危机、发展趋势、研究途径、宏观规划等方面,对诗经学加以系统论述。他的《诗经研究反思》最早全面提出了诗经学的学科建设规划,并呼吁学界同人从转变观念、统一组织、科学分工、搭建平台、出版刊物、交流合作、编辑索引以及成立专门机构等八个方面共同加以推进。20世纪90年代初,他有感于《诗经》在我国文学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向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夏传才建议创立中国诗经学会。1993年中国诗经学会获批成立。他参与筹备的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多达309人,其中海外学者65人,会议反响空前。
进入21世纪,赵沛霖完成了《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一书。有学者指出:“他不只是表现出高度的方法意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就是希冀透过方法论的检讨、理论的反省与学术史的回顾,从而为该学科或研究领域奠立坚实稳固的基础,并在这种基础上不断地提升与扩大既有的质与量。”
继先秦文学研究之后,他又“转战”汉魏六朝文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探险攻略”。进入这个新的领域,他首先全面系统地阅读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和相关历史文献,然后重点研读八代三朝八百年间重要作家的文集。除了司马迁的有关作品和汉代《郊祀歌》之外,他还重点研究了曹植、阮籍、郭璞、陶渊明、鲍照、庾信和南北朝乐府,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其中《论阮籍〈咏怀诗〉》和《庾信山水诗的世俗化及其意义和影响》很具代表性。
《论阮籍〈咏怀诗〉》提出,在无法确知很多诗篇的写作时间和针对什么具体事件的情况下,要根据历史背景来为《咏怀诗》划分阶段是根本不可能的。多年来,很多研究者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既然这条道路走不通,他就另辟蹊径,从诗人的主观情怀出发,去考察其内心世界的变化,也就是从其心灵历程加以考察。他以出世思想萌生和发展为线索,将《咏怀诗》分为三个阶段:“出世思想的萌生和初步形成”“出世的处世原则得以正式确立”“把出世远游认定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归宿,表现出对于神仙世界的强烈向往”。这种划分方式为解读《咏怀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庾信山水诗的世俗化及其意义和影响》提出,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庾信诗歌,特别是他的山水诗,评价并不准确。在庾信之前,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主要是追求人生解脱的心灵自由和精神超越,以达到与自然冥合为一的境界。很显然,这是逃避现实,企慕世外。而庾信则不同,他把世俗情怀和对山水自然的审美观照结合起来,把世俗性的欲求和期待融入对山水自然的具体描写中,这直接导致了山水诗的世俗化,推动山水诗彻底走出玄学的阴影而回归人间、立足现世。而山水诗的世俗化推动了山水诗创作的发展,后来唐代山水诗出现繁荣,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在研究了汉魏六朝的多位重要诗人作品和乐府诗以后,赵沛霖计划从中选择一位诗人进行重点研究,写一部专著。经过反复比较考量,他认为研究郭璞的诗赋最适合写专著,于是开始了郭璞诗赋研究和写作。
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诞生已有一千六七百年,但是学界对其主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最后几乎形成定论:《游仙诗》是由没有联系的两部分或几部分组成,根本没有完整统一的主题和结构。这个结论被写入多部文学史著作。赵沛霖曾回忆:当时,他就像小学生猜谜语那样兴趣盎然地玩味各首诗和诸多“残句”以及有关文献,力图破解这个千年谜语。破解的过程就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辛苦而有趣,紧张而新鲜,寂寞而充实。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他围绕郭璞诗赋这一课题,在《文学遗产》等六种刊物上发表了11篇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写成《郭璞诗赋研究》一书。此书总结了前人研究郭璞《游仙诗》的历史经验以及如何改进研究方法,最终解决了《游仙诗》的主题问题,指出郭璞的《游仙诗》是一篇具有统一主题和完整结构的优秀组诗。书中提出的诸多开创性观点,如今大多成为学界定论。
一位纯正的学者
了解赵沛霖的人都知道,他既不讲求吃穿,也不抽烟不喝酒,人情琐事都不挂心上。他把全部精神都贯注在了科研上,心无旁骛,定力十足。
有一次,我翻阅旧报纸,偶然发现1992年的《天津日报》有一篇题为《文人下“海”第一天》的新闻报道:时任天津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的赵沛霖,跟所内科研人员一起开办了“天津鼎鼎取名事务所”。读后有些难以置信,于是赶紧问询。
赵沛霖给我讲述了这段“下海”经历:那时鼓励“自主创收”,很多学校和研究机构都办了经济实体,他作为文学所负责人,责无旁贷开始了“下海经商”。事务所开业后,顾客很多,社会上一度流传“社科院有个正牌的起名专家赵教授”。后来,热潮逐渐降温,文学所为了集中精力做科研,停办了事务所。当时有人劝他,“你很快就要退休,接着干的话,一年能有十几万元收入,放弃了太可惜”。不过,他心里清楚,虽然自己对取名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但自己真正想要的不是发大财,而是安心做学问。后来事务所的牌子摘了,他一点也不遗憾,倒是惋惜那些年为税务、财务、编制、接待等浪费了太多时间。
赵沛霖总说,学问不是饭碗和工具,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快乐研究而不内耗,敬畏学术而不苟且,是他的人生信条。
赵沛霖反对学术“跟风”,主张脚踏实地,要有批判性思维。他曾叮嘱初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问题,必须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具体的时代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具体的研究。”这种自主意识深刻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他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时,没有采用西方神话学理论的分类原则,而是根据中华民族早期历史发展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神话的特殊性加以分类。在他看来,西方神话学理论的分类原则,适用于在自然崇拜基础上产生且有主神和内在统一的普遍神系的希腊神话,而不适用于主要是在祖先崇拜基础上产生且缺乏主神和内在统一的普遍神系的中国神话。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有了知名度以后,有些出版社主动邀请他撰写书稿。这不仅可以解决当时学者普遍面临的“出书难”问题,而且还有相当丰厚的稿酬。有出版社约他写关于《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的书,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对这些典籍是否熟悉、是否做过深入研究、是否有所创新、推动了有关研究的发展。经过认真考虑,他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便毫不犹豫地推掉了稿约。一些人认为他“死板”,渐渐与他疏远,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越底线。
学术研究中的以文会友、以友促学,是赵沛霖人生的一大乐事。他历数学术生涯中结识的诸多海内外良师益友,快乐溢于言表。正是因为这些朋友的介绍和推荐,他多次应邀到海内外参加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访问活动,一方面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也增长了见识、提高了研究水平。
赵沛霖做事认真,与人交往,也是以诚实为本。他与楚辞研究专家、淮阴师范学院教授萧兵惺惺相惜,曾就屈赋等问题往来书信数十封。萧兵曾在1978年至1985年间,发表有关《楚辞》与民俗神话、《楚辞》与美学的论文近百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对此,《文艺研究》邀请赵沛霖写一篇相关评论。于是,他又认真研读了好友的所有论著,撰成《评萧兵〈楚辞〉研究》一文,称赞了萧兵在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突出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评论发表后,两人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相遇。萧兵对他说:“你把缺点提得可够充分的。”赵沛霖顿觉尴尬,内心打鼓:自己是不是太认真了?会后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翻看那篇论文。反复研读后,他还是坚信指出萧兵研究中的那些缺点有充分的根据,对好友的评论是对的。后来,他与萧兵在一次研讨会上再度相逢。萧兵一见即喊:“老赵!你的评论是对的,我把你的文章给学校的年轻老师们看,他们也认同你的看法。”萧兵又专门致信说,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评论,“对学术研究发展大有好处”。自此之后,两人友谊更深了。
这就是赵沛霖,做学问有精深的文献功夫、强烈的批判精神、自觉的学科意识、融通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做人超然淡泊、守正不移。正如学界同人所评价的,他是“一位纯正的学者”。
学人小传
赵沛霖,1938年生,天津人。古典文学专家。1963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前身),曾在天津河北中学任教17年。1980年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副所长、研究员,曾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等。撰有《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诗经研究反思》《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屈赋研究论衡》《郭璞诗赋研究》《重读经典——上、中古文学与文化论集》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作者:罗海燕,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