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修延:讲故事的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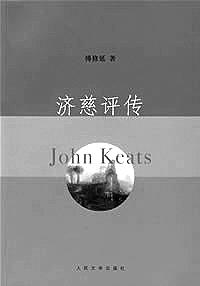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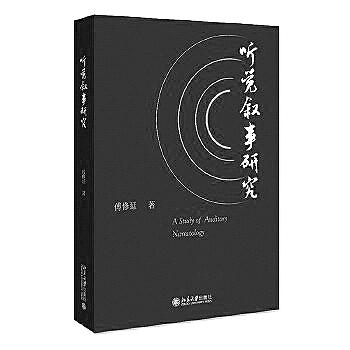

学人小传
傅修延,江西铅山人,1951年生于江西南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1977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1979年被破格录取为该校中文系研究生,后获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扬州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做访问学者。曾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著有《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中国叙事学》《听觉叙事研究》等,主编“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丛书。
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江西曾是人文昌盛之地。但是到了近代,赣鄱大地亦历尽沧桑。但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之乡,总有人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有足够的耐心又有足够的毅力,坚持不懈,奋勇向前,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硕果。傅修延便是这类江西人的代表。
提起傅修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叙事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傅修延从多伦多大学访学归来,出版了他的叙事学处女作《讲故事的奥秘》。那时候,叙事学不像今天这样热门,还被一些习惯了将“叙事”与“抒情”并列的人视为故弄玄虚。但傅修延并没有在意这些,因为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成立,最终取决于它能不能满足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今天,叙事学已经成了一种被广泛运用的跨学科理论,这显示了他的先见之明。
要全面理解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虽然年过古稀,傅修延却仍处在令人惊讶的学术生产火山喷发期(这一点他自己用“学问于人有精神滋养之功”来解释),2024年他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七卷本“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出版。他当然具备很多优秀学者的共性,比如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感受敏锐、心思专注和精力旺盛等,但他可能更有其他学者所没有的一些特异品质。比如他对世界永远有一种孩童般的强烈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让他对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有着异常强烈的探索愿望和动机,而没有这样的愿望与动机,一个人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做出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发现,因为任何发现都是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一场学术演讲后,有人问傅修延,人类精神能否在赛博空间永存?他回答,多年前自己就在想这个问题,他每年的日记少说也有十多万字,加上著述和其他文字,这些储存在电脑中的东西便成了个人记忆与经验的物化,将来人们可以凭借这些信息,与大数据中永不消逝的“我”进行互动。讲座结束后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立即发来微信:你预言人类精神将在大数据中永生,这个观点把我们都“惊到了”。事实上傅修延这种把人“惊到了”的先锋观点还有许多,例如当前人们都在努力学习使用AI,他却在《叙事的本质》中说人不能沦为机器的奴隶,“动物精神”仍然是人们做选择时的决定性因素。又如学界对“后人类”问题的讨论甚为热烈,他却在《从二分心智人到自作主宰者》中说今人尚未完全实现对自身心智的主宰,理由是许多叙事作品都提到人物能听到大脑里的另一个声音。再如人工智能的强势崛起让不少人文学者感到前景迷茫,他却在演讲中说AI对人脑的模仿处在人类早期模仿文化的历史延长线上,因此“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我们读他的学术研究著作和文章,有一种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很会讲故事。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吸引人,那些非常专门的、在局外人看来有点枯燥的专业问题,到了他的笔下,变得趣味盎然、引人入胜,例如他写过一篇名为《嗅觉叙事与中国伦理话语的形成》的论文,引发大众的兴趣。他从来都不愿“为学术而学术”,不会做“邻猫生子”之类的无聊学问,更不会以莫测高深的高头讲章来唬人。所以即使在学术研究的范畴之内,他笔下的文字也是让人感到亲切,有着令人难忘的情感温度。文品即人品,一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热潮中崭露头角的学者,到今天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都有一种难得的敞亮的“少年气”,这不仅令人羡慕,更令人深思。
二
按照傅修延自己的说法,如果没有走上治学的道路,那么他在今天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演讲和本雅明著作都用过此名)。根据我的理解,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戏言。有人看到他分析刀郎歌词艺术的随笔,感叹说此人在文学创作上有极高的天赋和才能,如果不是被学问“耽误”了,他该会创作出多么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啊!可能他自己内心深处有时候也会有某种遗憾吧,毕竟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你选择了一条道路,就会错过另一条道路上的诸多美景。
这样来看待他的学术研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其中既有思想的真知,又有情感的温度。他是一位特别有“现实感”的学者。对于书斋中工作的学者来说,如果缺乏“现实感”,他的所有研究就可能变成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空转,无法与这个世界及他人生活发生有意义的关联。傅修延与历史上那些富于现实关怀的赣地先贤一样,对自己的生身立命之地怀有深厚的情感,著文发声更接地气更有担当,这是他特别令人敬重和佩服的地方。
他本科就读的是外语系,只读了不到两年,便被破格录取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允许这样做)。虽然学的是外国文学,但他首先是一位脚踏华夏大地的学者,外国文学研究在他那里一直被定位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就是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不能简单重复外国人自己的研究——他的原话是“如果我们这边说出来的话,和人家那边说出来的话一模一样,那就不是中国的或者说不是中国人的外国文学研究”。具体到叙事学领域,他之所以举起“中国叙事学”这面旗帜,是因为看到一些西方学者罔顾华夏为故事大国、中华民族有数千年叙事经验之事实,试图在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下总结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当年在归纳“叙事语法”上陷于困境,视野狭窄便是一个重要原因。
处于后发位置的中国学者确实应当虚心向先行一步的西方学者学习,但西方叙事学主要植根于西方的叙事实践,其理论依据很少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围,在此情况下,中国学者应当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叙事传统,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描述中西叙事传统各自的形成轨迹,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与激荡,如此叙事学方能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同行表现出对此观点的认可。
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很多年以来,傅修延为什么要那样着力培养和扶持一大批后起学人的原因。他身边围绕着一批性格不同才能各异的中青年学者,他首先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学术实践,成了他们的示范者和引领者。2012年,卸下了行政职务的傅修延,每周四晚上,都会在江西师范大学那幢名为“王字楼”的木结构老房子里主持叙事学读书会,时长达两个半小时,参加人数通常都在30来人。这个读书会雷打不动地坚持了十多年,有位读书会成员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每周四与师友围坐一桌,言笑晏晏,长了见识,增了知识,真乃凡尘中桃花源。”
学界有个说法,一个科研团队既要有人“指兔子”,又要有人“打兔子”和“捡兔子”,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成功。2022年江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叙事学研究院,毫无疑问,研究院的首席专家傅修延就是“指兔子”的人,但他又要求团队成员不能总在自己的舒适区“打兔子”,而是要满世界去“找兔子”。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受过系统的外语训练,有相当娴熟的中外文献检索功夫,一些人还有在欧美学习工作的经历,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有一种既“知己”又“知彼”的优势。在与年轻学者的交流中,他经常引述王国维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还说要向珠江入海口的基围虾学习——这种虾涨潮时喝咸水,退潮时喝淡水,做学问也应该这样“咸淡水通吃”,也就是拥有开放的胸襟,既懂中国的学问,也能消化外国的知识。国际叙事学研究会会长马可·卡拉乔洛在最近一次与傅修延的学术对谈中,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基围虾之喻:“我们都应该暂时拥抱自己内心的‘基围虾’,通过成为‘他者’(甚至是非人的存在),以更全面地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世界。”
三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傅修延为这项研究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得出了许多富于创见的结论。然而,不应该仅仅将他的研究看作是对本民族叙事传统的捍卫,而应该理解为他对真理和真知的执着追求。知识让人靠近真理,只有和真理站在一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说傅修延的学术研究有着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格局和境界,原因应当向此处寻找。
让我们来看看他对叙事传统的中西差异是怎么解释的吧。他倡导听觉叙事研究,是因为他发现中国文化以听觉来统摄包括视觉在内的各种感知,而西方文化强调“以视为知”(看到才是知道),也就是说中西文化在视觉和听觉上各有倚重。以叙事学家最为关注的事件展开方式为例,趋向明朗的西式结构观(源自亚里士多德)要求保持事件之间显性和紧密的连接,顺次展开的事件序列之中不能有任何不相连续的地方;而趋向隐晦的中式结构观则允许事件之间的连接可以像“草蛇灰线”那样虚虚实实断断续续。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叙事并不新鲜,像傅修延这样从感觉倚重角度入手却是首次。中国叙事经典的“尚简”“趋晦”和“从散”等特征,只有与听觉的模糊性联系起来,才能理得顺并说得通,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感知途径影响信息传播)这一思路引入研究,一些与中西叙事传统有关的问题因此获得了更加贯通周详、更具理论深度的解答。
叙事学领域内像中西差异这样的重要问题还有不少。以叙事的本质为例,西方叙事学家对此虽有涉及但只作了迂回式的侧面探索,他却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正面强攻,以一篇五万字的长文《叙事的本质》对此展开了全方位论述,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学界重视。他的《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元叙事与太阳神话》《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和《人类是“叙事人”吗》等论文,光从题目上也可看出“其志不在小”。他总是以自己的敏锐、睿智和担当,直面那些他认为不能留给后人去解答的大问题,同时结合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生命体悟,调动起自己所有的思想资源,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努力给出自己这一代学人所能给出的最优答案。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傅修延的著述中只有难啃的硬邦邦理论,读者大多认为他的文字读来亲切感人,其行文能将深奥的专业探讨化为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的“拉家常”。虽然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但他从来不会板起面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善于从衣食住行等生活日常出发,对人们天天看到但又未去细想的现象去做深入发掘。让一些循规蹈矩者难以想象的是,他竟把面容作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论作为能指的面容》),又从丝巾追溯到体现中国审美特质的飘带精神(《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还试图用耳朵去感知敦煌壁画(《从“听感视觉”角度认识敦煌壁画》)。由于这些探讨充满妙趣,他后来干脆出版了一部《趣味叙事学》。前面提到他称学术于人有精神滋养之功,至此我们明白,为什么一些人觉得苦不堪言的学术研究,在他那里竟像是孩童在沙滩上玩自己的游戏。
傅修延的女儿傅真是一位作家,她在文章中称父亲为“一个很妙的人”,并列举了这个“妙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异想天开的举动。借用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说只有像他这样的“妙人”,才能写出上述那些“妙文”,而“妙文”之中又不能缺少“妙语”和“金句”。我看到有同行引用他谈面容中的话:“人之为人在于有一张被内在精神‘照耀’的脸。人类可以用无数创造物来证明自己的优秀,但最好的证明还是自己这副经历了漫长演化过程的面容。”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则是丝巾文章里的一节文字:“丝巾是可收可放、可挥可甩和可执可舞的,又是可系可解、可折可叠和可包裹又可被收纳的,人们无法想象这小小的织物,居然拥有如此之多的可能性,而正是这些可能性赋予其灵性、自足和超脱等形而上特质。”
如今,在短视频和语音信息的反复“投喂”之下,文字驾驭能力成了一种“稀缺物质”,许多人已经不会组织清晰流畅的文句了,傅修延那些行云流水般的精妙表达显得特别可贵。如果要问这样的能力从何而来,除了大量的书写实践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对祖国文化与民族语言的热爱。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外国文学学者还拥有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先秦叙事研究》后记中有这样一番话:“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趋向本民族的文化,内心深处‘我是中国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用拉丁字母表达的一切,对我来说远远不如用方块汉字叙述的东西来得亲切有味。”
话虽这般说,为了让中国学界的声音传到西方,他还是会用拉丁字母来与国际同行互动。中文系文学专业的人,大都想把文章发在国内的顶级期刊上,而他不仅做到了这些,还在《文体》(Style)、《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Neohelicon)等著名国际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文体》及《叙事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语言与文学》(Language and Literature)等国际期刊还有对其研究的评论与访谈。他的《中国叙事学》(英译本)在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入选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听觉叙事研究》不久后也将由这家出版社推出。
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同行常常显得拘谨,傅修延却不在此列。Neohelicon的主编匈牙利学者彼得·海居请他给自己的叙事学著作写序,傅修延在序言中直言,不能把中国叙事传统视为另类,否则就有滑向“欧洲中心论”之嫌。不过他又说,自己和对方是有多年学术交往的“好兄弟”,“好兄弟”之间就是要这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从1983年发表《〈项链〉的链形结构》算起,傅修延深耕叙事学已有四十年之久,今天称他为叙事学家似不为过,但我更想说他的身体里面还住着一名诗人,或者说他因早年研究《夜莺颂》作者济慈而拥有一颗诗心。他为这位早夭的浪漫天才奉献了三本书:翻译了40万字的济慈书信,写出了国内第一部济慈评传(为此遍访诗人足迹所及之地),研究济慈的专著《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济慈书信集》的译序中,他称“爱是不能忘记的,学术研究上的‘初恋’同样铭心刻骨”。他的女儿名字中有一个“真”字(来自济慈《希腊古瓮颂》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也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带领妻儿去罗马的济慈墓前献花。诗人在天之灵仿佛感应到了异国知音的到来,《济慈评传》后记如此描述:“去新教公墓的路上细雨如丝,走进公墓后雨丝如同被突然剪断,一道阳光从云层里射出,照亮了墓地与其后的古城墙与金字塔,走出公墓后雨珠又开始滴落。”
傅修延对济慈的情有独钟,可能缘于这位诗人不像拜伦、雪莱那样出身贵族,也不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上过剑桥牛津,当时一些批评家势利眼,把他视作地位低贱的“伦敦佬”。傅修延小学二年级时便随父母到江西弋阳县农村生活,1968年初中未毕业的他到新建县的朱港农场工作,在血吸虫肆虐的鄱阳湖水域开过三年船,从船工转到新余冶金机修厂当起重搬运工后,还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工伤事故:他从15米高的车间屋顶跌下,导致严重脑震荡、内脏大出血和左股骨粉碎性骨折。大难不死的经历让他对命途多舛的济慈怀有强烈共情,但诗人对他影响最大之处,还在于“在人世间这个‘泪之谷’中始终绽开灿烂的笑颜”。在探究济慈内心时,人们深感钦佩而又为之伤痛的就是这种情怀,它有一种巨大的感染力,使人更加热爱生活,更加努力去追求生命中一切有价值的事物。
傅修延和济慈一样,不管命运如何亏负自己,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失去那种追求人间美好事物的激情。我们在其妙趣横生的文字中感受到的一切,归根结底都可以追踪到济慈对他的这种影响。蒋勋有句话放在这里可能比较合适:一个人心里有青春,那他就可以一直处在青春期。正是因为胸中一直怀有这样的青春激情,他才会在农场和工厂中一直坚持自学英语、刻苦写作,几乎没有半点懈怠,所以1977年高考制度甫一恢复,他便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江西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江西师范大学,当时他这样的“大龄”考生只能报考省内高校,而该年江西招收英语本科的只有这所学校);也是因为前期基础相当扎实,他才能在进大学不到两年后又考上本校的研究生。
四
行文至此要说点文学之外但又离得不太远的话。傅修延是最早提出“赣文化”这一概念的江西学者之一,后来他又觉得“赣鄱文化”这一名称更为合适,因为国内其他地域文化(巴蜀、齐鲁和燕赵文化等)也是采用这种双子星座式的表达,“赣”与“鄱”的激荡汇合反映出江西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气。他在省社科院院长任上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倡议,这个倡议后来被采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在已成为国家级经济区。他提议过在南昌建利玛窦广场,理由是利玛窦在这里待过三年,与江西读书人多有交往,这可以显示豫章城是中西文化碰撞并溅击出明亮火花的地方。许多朋友还记得,他曾大声疾呼在南昌闹市原址恢复万寿宫,如今重建的万寿宫及相邻街区已成为游客必来打卡的观光胜地。他在本世纪初提出以白鹤为江西省的省鸟,20年后得到省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需要说明,他关注白鹤,是因为凭借自己的比较文学知识背景,看出南昌地方文献上记载的浴仙池故事(女主人公为白鹤仙女)实际上属于全球广泛传播的羽衣仙女传说,文化部门因此认定他为该传说的“非遗”传承人。还有他对赣菜过辣过咸的批评,以及“重口味”可能导致地域文化粗鄙化的思考,引起过赣地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他带的两名博士生曾经不理解导师为什么硬要自己“改行”做景德镇瓷绘研究,如今在陶瓷叙事领域中收获满满的她们,说起当年的“被逼迫”来,充满了感激。
最后要提到他为打造江西师大瑶湖新校区倾注的心血。2009年省里把他从社科院调回江西师大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这种“一肩挑”的安排意味着他要承担起偿还基建贷款以及为工程扫尾的全部责任。在此过程中,他以文化人独有的艺术想象力,为校园增添了一系列景观亮点。来到这里,人们会惊喜地发现,校园没有围墙,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国内独一无二、环绕三千亩校区的护校河,沿着护校河还铺有一条长逾5公里的健康小道,此外还有钟楼、桃李鼎和一幢古色古香的书院建筑。当人们表示赞赏此类举措时,他却说要感谢时代把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给予了自己:作为高等教育中人,能够亲身经历中国大学这种跨越式发展,这让自己在回顾往事时有一种不枉此生之感。
前面提到,傅修延说在治学上要像基围虾那样“咸淡水通吃”,这里我们看到他对学问和事功也取一种兼顾态度。不过我想他可能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来鄱阳湖越冬的白鹤,这种鸟儿既会在湿地的泥浆里埋头啄食,又能飞上蓝天发出“声闻九皋”的清越鸣声。
(作者:陈离,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