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汉律摭遗》与程树德《汉律考》等著作,使得亡佚近2000年的汉律,在百余年前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一些汉律辑佚,则未必如此知名,如杜贵墀的《汉律辑证》、张鹏一的《汉律类纂》等。有些书,则可用“命运多舛”来形容。薛允升的《汉律辑存》(以下简称《辑存》),即如此。
近日,笔者据相关文献记载梳理稿钞本源流、展开合校的《汉律辑存合校》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借此时机,简单叙述薛允升其人与《辑存》,以及《辑存》所录汉律之价值。
薛允升其人
薛允升(1820年—1901年),字克猷,号云阶,陕西长安县马务村(今陕西西安长安区马务村)人。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任职刑部主事,光绪十九年(1893年)任刑部尚书,前后典谳法近四十年。
自任职刑部以来,允升以为,刑名关乎生民性命,与其他官曹迥异。律例规定多如牛毛,若不熟悉条文、洞悉律意,不便决狱定罪。于是,他“研究律例,晰及毫芒,心存哀矜,期天下无冤民”。朝夕手钞,搜罗巨细靡遗,“老病闲居,不废精勤,实数十年如一日”。久而久之,触类旁通。有询问者,允升随口应对无疑。因备受上官倚重,故经手众多狱讼事务,终岁无片刻闲余,以清廉勤事著称。
允升形貌清癯,生性温和。治狱每至夜半,一灯荧荧。差役或困倦退下,允升仍平心静气,从无疾言厉色。“与囚犯絮絮对语,囚忘公为官,公亦若忘其与囚语也。”他在刑部平反冤案甚多,啧啧为人称道的王宏罄案即是一例。当时,诸人不日将被处死,允升复审,为其雪冤,保全性命甚多。凡允升经手之案牍,他人不能增损一字;囚犯叹服其公允,或虽死仍感激之。遇到疑难案件,必万分审慎,有冤情者为之洗刷,虽触犯权贵而在所不惜。
《辑存》撰辑缘起
允升之生平业绩在于决狱定罪,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他对传统律学投入了大量精力。《读例存疑》《唐明律合编》是其殁后陆续刊行的著作,前者是其半生心血所系,后者是唐、明律比较研究。《汉律辑存》则较少受关注,无他,因此书亡佚于庚子之年。在此,需赘述一句,上述诸书著作权虽归于允升,实际情况是刑部不少官吏如沈家本、沈曾植等人亦参与其中。
“薛公墓志铭”对《辑存》叙述较详:
尝谓近人说经多搜存汉学。汉儒以董子为醇,郑康成为大;董以春秋决狱,郑以律令注礼。汉制试士,讽诵尉律籀文九千字,则汉儒无不习律者。汉律在今亦汉学也,而散失殆尽。学者何以忽诸?因广加搜剔,缀录成编,名曰《汉律辑存》若干卷。盖汉律九章,定于萧何;何自造三章,余六章即李悝《法经》。《汉书·艺文志》不载《法经》,以并于汉律也。存汉律,《法经》亦赖以存矣。
简言之,汉律是汉学的组成部分,但未受到学者足够的关注,故允升有撰述之心。而且,汉律多源自《法经》,辑录汉律,《法经》亦因之留存。
清代辑佚之风虽盛,除孙志祖外,罕有辑佚汉律者。清中后期以来的汉律辑佚者,除上面提到的诸人外,尚有胡玉缙、王仁俊等人(主要辑录《说文解字》所见汉律令佚文),另有近年新发现陈庆年的《汉律逸文疏证》稿本。可将诸人之辑佚视为广义的汉学成就,有“广备佚文,博洽闻见”之功。
笔者以为,在“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之世风浸淫下,薛允升、沈家本乃至张鹏一极力强调律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更值得留意。通览《唐明律合编》可知,该书不时称引汉律佚文或两汉文献,如此一来,不仅唐明律可以合而观之,汉律辑佚亦可水到渠成。实际上,薛允升以唐律为枢轴,上溯源秦汉律令,下考察明清律例,有会通古今之意。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张鹏一从中西法律比较入手,以“阐扬国粹”之心,提出“法律大用,不外尊重人格,保卫权利”,还提出“吾国研究法律,将以溥权利思想于人民。窃愿输入新法者,究心古律之佚说,庶旧学发明,相得益彰”。这些论说,无疑是中西碰撞、古今转变之产物。类似提法,在《寄簃文存》中,亦屡见之。在沈家本看来,提倡“法学”,世局亦可转移:
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是在提倡宗风,俾法学由衰而盛,庶几天下之士,群知讨论,将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
明乎此,则薛、沈与孙、杜之汉律辑佚,可谓名同而实异。
研究传统律学,是否可为新法确立乃至修订提供借鉴,难以一概而论。若援引杜牧“丸之走盘”的譬喻看,当“丸始终不能出于盘”时,回望、借鉴过往或许有效。当“丸已出盘”时,新旧法律间的矛盾,大概是无法调和的,借鉴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辑存》亡佚与再现
《辑存》草于同治、光绪间,庚子年(1900年),稿本被某舍人藏匿,作为薛氏遗作的整理者之一,沈家本如是言。参与允升著作撰述及编辑的陈浏,援引允升自述写道,稿本为门生徐某“遗失”。藏匿还是遗失,性质完全有别。或主前者,如孙家红据此并参阅相关资料定为“徐谦”;或主后说,从《厉廉隅室读律记》看,参与《辑存》撰辑的“徐博泉”,最有可能是当事人,朱颐年就认为此书“确在徐处遗失”,暂从。
1935年,顾廷龙在书肆中发现标为“汉律稿本”的丛残一束,据稿中所见“唐明律合刻”“长安薛”等字样及内容,判定为薛允升《唐明律合编》稿本,与服制相关者为《服制备考》稿本,但均与汉律无关。当顾氏向李祖荫提及此事时,李氏说道,“尚有《汉律辑存》稿本,近亦知其所在,盖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得”。李祖荫算是当时知名法学教授之一,受聘于燕京大学,对《辑存》似不陌生,此时距稿本亡佚已30余年。
《辑存》稿本昙花一现,瞬间又石沉大海,再无任何消息了。庆幸的是,就在这一瞬间,产生了两份钞本,成为公私庋藏物。
先说“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获稿本,今藏傅斯年图书馆。
稿本正文首页,钤有白文“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可知确为该机构购得,约在1935年。抗战胜利后,此单位及“近代科学图书馆”所藏图书拨交史语所,后又运往南京。藏书以明刊本、明钞本及稿本为主,《辑存》稿本也在其中。
稿本红格,单鱼尾,白口,四周双栏,版心下镌“青云斋”,半页九行,无撰者姓名。部分文字系剪贴而来,多数情况下行款不定。《辑存》稿本贴纸、附笺极多,加以涂抹增删,整理不易。
接着来看钞本之一,即北京大学图书馆本。
钞本黑格,单鱼尾,白口,四周单栏,半页十行。目录页及正文首页,均钤朱文“国立北京大学藏书”印。抄写工整,以墨笔校订文字;另见铅笔签条十余条,或粘或夹于相关位置,多是迻录傅图本眉批文字,或提示相关资料应调整之顺序。
对此钞本之由来,朱氏在《厉廉隅室读律记》中写道,“始悉事变前,甫经前北大某教授转借手稿抄存,现在某业已离京,无从寻其究竟。”当他向董康提及此钞本时,董康提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曾获是书稿本”,朱氏遂“系一素纸本黏签,北大图书室转钞于此”。
不仅如此,朱氏还广搜穷寻文献,考察允升著述情况,并对稿本署名问题有所阐发。铅笔书写的签条,顺序虽早已打乱,可能是朱氏对校稿本、钞本时所留。后来,吴荣曾、张传玺等学人陆续借阅该书。钞本未著录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较少受人关注,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接着看钞本之二,即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本。
钞本红格,四周双栏,半页十二行。无撰者姓名,封内钤有朱文“内藤乾藏书”印,系内藤乾吉所藏。抄写工整,以墨笔或朱笔校订,或径改钞本,或见于眉批。钞本从何而来,目前尚不清楚。
从稿钞本看,《辑存》应非定稿,与沈曾植代笔《汉律辑存凡例》一文,自然无法对应起来。作为未定稿,此书虽无法与沈家本、程树德之书相提并论,但也具有沈、程书所不具备的显著特征——
除辑佚《汉书》《史记》《后汉书》所载律令文字外,对《说文》及经书记载,如《公羊传》《周礼》《礼记》《尚书》等,亦给予较多关注。除汉唐注疏外,又多采惠士奇的《礼说》、惠栋的《九经古义》、孔广森的《经学卮言》与《礼学卮言》等论著,这是薛辑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从这个角度看,薛辑自有其不可取代之价值。
学界或以为考古出土的秦汉法律资料甚多,故清代以来的汉律辑佚之作价值不大。笔者则认为,辑佚将传世的记载网罗殆尽——今日研究秦汉法律问题的传世文献例证,在辑佚之作中几乎都被罗列出来了。新旧结合而非厚此薄彼,方是正道。
整理《辑存》稿钞本,完全是意外之事。稿本流落人间120年后,参照稿本及两份钞本,推出合校新本,使心血之作得以化身万千,在进一步呈现该书价值之同时,似可告慰前贤时哲之辛苦付出,此其时也。
(作者:张忠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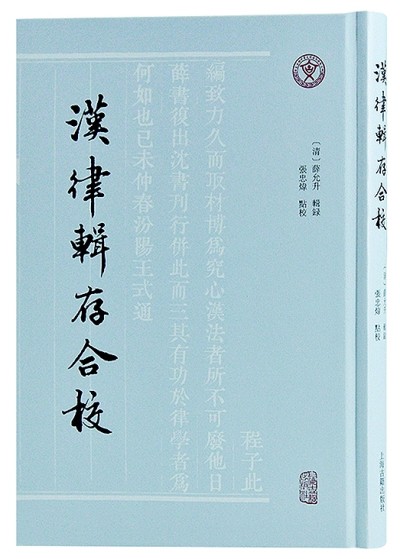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