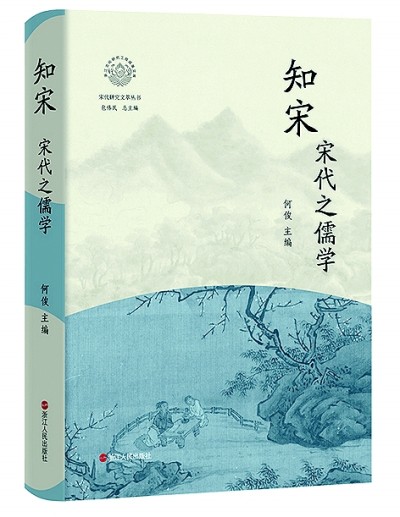【编书者说】
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知宋”丛书,由包伟民教授主持,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两宋历史的门径。其中儒学一册,嘱我选编。
这册最终定名为《知宋:宋代之儒学》的文萃选编,上编依年齿选邓广铭、徐规、陈植锷先生与陈来、王瑞来教授共七篇文章。下编收入笔者近年分析宋学初兴时胡瑗湖学与宋学完型时朱子理学、象山心学、水心事功学等四篇文章。现应约,谈一谈宋代儒学之气象与精神。
一
宋代儒学观其风貌,可谓气象万千;论其精神,则可概之以人文与理性辉映。
既为儒学,宋代儒学自然是远承孔孟,甚至上溯尧舜,这是宋代儒学的共识。宋儒自我标举为儒学“再辟”,但考诸学术思想的直接由来,这一因其呈现出新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形态,从而被今人称作“新儒学”的宋代儒学,其滥觞实在中唐韩愈启动的古文运动及其对儒家之道的阐扬,以及啖助新《春秋》学派舍传求经的新经学。入宋以后,在结束了晚唐五代的连续动荡、承平八十年的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胡瑗湖学为代表、以明体达用为宗旨的推崇儒家师道的讲学运动兴起,进一步与古文运动、新经学叠相激荡,在欧阳修、范仲淹等士大夫引领下,人才以一种共生效应成群出现,催动了宋代儒学的勃兴。
古文运动、新经学、讲学运动虽然路径不一,但志趣同在儒家之道的重建。只是儒家之道的根本内涵是什么?如何明体?如何达用?如何才能真正以儒家之道来整合世道人心?凡此具体问题,儒家学者们都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在各自的社群空间中彼此切磋,尝试着从儒家的传世经典与史传文籍中去获取智识。因此,宋代儒学自始便以一种“学统四起”的方式,呈现出自身的丰富多样性。
二
宋代儒学“学统四起”,然万千气象终难掩日月之光华。
北宋中后期的儒学,渐以王安石的新学、程颢与程颐兄弟的洛学以及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为重。蜀、洛二学系以地理位置命名,新学则是相较于旧学而言来命名。旧学,指的是以汉唐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思想。照理,蜀、洛二学也是决不同于汉唐旧学的,但独标王安石之学为“新学”,除了有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的因果,实亦表征王安石新学执北宋儒学之牛耳,主导了北宋中后期直至南宋初期的学术思想。
三家学说各是其是,自洽其说。论其要,新学重在制度,洛学重在道理,蜀学重在权变。制度与道理本为表、里,只是制度重在效益,道理更重原则;虽然效益不可能违背原则,原则亦终要体现于效益。因此,在根本上新学与洛学二者似乎不应有冲突。但于现实境遇中却因各自着眼不同,进而思考与举措不同,更因参之以人事,结果势同水火。蜀学因其重权变,“无复实理”,本来与王学、洛学都不至于构成紧张,但二程尤其是程颐,与王安石,为人为学都很较真,而蜀学代表苏轼“烂漫放逸”,连带着在为学上彼此不融。
三家学说又与时局深度关联。蜀、洛二学在北宋因新学得势先受压制,新学则又因靖康之难、在宋室南迁后渐遭摈弃而竟消沉,蜀学本不应与新学同贬,但文人气重,喜怒哀乐发之以嬉笑怒骂,以文为论,而文章又于事不求其实,于理不求其正,因此不足以承担厚风俗、存纲纪的世道重任。随着政治上的放逐弃用,加之在当时的知识世界中新学被认为是“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蜀学是“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都属儒学所要排斥的对象,故洛学在南宋便渐成为主流。
三
洛学在两宋之际的程门传衍过程中,以道南与湖湘为主,但于学术思想上也是人各其说,莫衷一是。等到宋高宗建炎年间政局稳定以后,在后续的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宋代儒学始逐渐步入完型时期。
乾淳时期的儒学完型,大致可以分为相续的前后期。前期是由乾淳诸儒并起,在政治上同进退,在学术上共商讨,到逐渐形成以朱熹、张栻、吕祖谦为代表的东南之学。他们一方面通过整理二程的著作继承与阐扬洛学,对人各其说的思想现状进行梳理,同时以二程洛学为主,统摄周敦颐、张载,旁及邵雍,对北宋儒学进行正统化的思想建构,代表性的成果是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以及朱熹编撰的《伊洛渊源录》;相对而言,吕祖谦奉宋孝宗之命编辑《皇朝文鉴》,对北宋学术思想的保存别具全面的性质,即所谓“得中原文献之传”。另一方面,他们上溯孔孟,使建构中的宋代儒学上承孔孟儒学,努力实现他们的创新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后期随着张栻、吕祖谦的去世,朱熹理学趋于成熟而使得整个宋代儒学得以完型;但朱熹理学并未形成此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垄断,因为江西陆九渊心学于此时崛起,加之接续吕祖谦婺学而起的永康陈亮,都对朱熹形成了强劲挑战,稍后集永嘉事功学大成的叶适,在陈亮逝后,又与朱、陆两家构成了鼎足而立的思想局面。
朱、陆、叶三家在学术思想交锋的同时,在政治上基本属于共同的阵营,与官僚集团形成复杂的对抗,只是他们终其一生在政治上都没有实现各自的抱负。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而自甘沉沦,而是秉持自己的学术思想理念,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阐扬与践行儒学。其中,尤以朱熹的成就最为广大,不仅在学术思想上致广大而尽精微,集汉唐以来儒学之大成,确立《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将先秦偏重经验性的儒学发展成富有理论性的儒学,极大地推进了儒学在学术思想上的发展,而且使儒学融入日常生活,为整合社会与引领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形塑起相应的社会规范与文化系统。在南宋的后朱熹时代,经过学术化、意识形态化、日常生活化三方面的持续推进,朱子学最终成为主导此后数百年近世中国社会前行的精神主流,成为中国迈向近代乃至现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基础,并传播与影响到整个东亚,形成以朱子学为主导的东亚儒学文化圈。
四
宋代儒学从兴起伊始,即与士人群体的意识觉醒相伴。在晚唐五代政治动荡,佛教在公私生活都形成了巨大影响的历史境遇中,宋儒自觉担当起了时代与社会的责任,以回向尧舜禹三代为理想,上承孔孟之道,直面现实,以复兴儒学的方式重建社会的主流意识与社会形态,要为人类社会谋得恒久的安宁与繁荣。张载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整而又充分地表达了整个宋代儒学的共同使命。两宋各个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学派、不同儒者,无论其学术思想异同,都关注世俗社会的建设,一切以人为中心。概言之,人文性是宋代儒学的根本精神之一。正是在这一根本精神的主导下,宋代儒学发展出了丰富的精神面相;同时,儒学作为文化的核心,参与并促成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与人文性这一根本精神相应,宋代儒学所形成与彰显的另一根本精神是理性。从学术思想上讲,宋代儒学一方面是对汉唐经学的突破,另一方面是对佛道二教的排斥,而后者更渗透在文化习俗中。作为宗教,佛道二教无论在教义上具有怎样的精思妙想,全部论说的中心也不是世俗人间,而是往生乐土与长生仙境。汉唐经学虽然不具有宗教的信仰特质,与宋代儒学同属于学术思想范畴,但中古时期的知识观念是权威尊崇下的认知。因此,作为对汉唐经学之突破与佛道二教之排斥的宋代儒学,无论是在基本知识方法上,还是在希望建构的知识体系上,都必然摈弃虚妄与迷信,建立于理性的基石上。换言之,理性构成了整个宋代儒学的根本精神,宋代儒学以理学为自己的标识既是事实的反映,更是这一根本精神的充分表征。
宋代儒学的理性精神,起于怀疑与批判,转进为分析与辨析,最终落于经验世界的践履。这意味着宋代儒学的理性精神统摄了从认知理性到实践理性的各种形态,这为宋代儒学不同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儒者与学派提供了足够宽阔的理性应用空间,或一环贯彻,或交相叠用,路径不同,思想各异。宋代儒学之所以呈现出万千气象,实与此理性应用空间的足够宽阔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由于理学成为宋代儒学的主流,理性精神也因此构成整个宋代文化的底色;同时,宋代儒学的理性精神统摄了从认知理性到实践理性的各种形态,因此在理性的底色上不仅没有抹去经验的丰富性,而且使得这种丰富性寄身于理性而得到充分的彰显。
可以说,正是宋代儒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交相辉映,才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极度繁荣。
(作者:何俊,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