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治鲁迅学研究三十余年的孙郁教授最近出版了其新著《鲁迅与国学》,书中以十五个专章考察了于新知国故间“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鲁迅。孙郁在“写作缘起”中提到:“大约二十年前,《光明日报》的一位朋友找到我,想谈谈鲁迅与国学的话题。我心里没有底,便找来顾农先生,三人作了一次对话。顾先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对于鲁迅的学问根底有较深的心得。那一次对话,顾先生的话,都说在点子上,我的表述,有时候是隔靴搔痒,并没有指向核心之处。这也刺激我后来多留意此类话题。”在《光明日报》那次提议下,“鲁迅与国学”的话题开始纳入其研究视野,孙郁至今对那场三人谈记忆犹新。
孙郁一直以来关注聚焦鲁迅传统,无论是在大学校园的日常授课研习,还是走向海外的寻访演讲,思辨演绎中他深入寻解,文本直面时他体味感应,理性的力量,科学的判断,聚合升华了这部集大成之作。讲述故实,博赡贯通,达意妙得,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鲁迅伟大形象中的底色铺陈与基调渲染之功。
二十世纪初期,国学旧学,国故学国粹学,经史之学文献之学,一般语境下是彼此可以通用的。落笔《不懂的音译》,鲁迅推重《流沙坠简》,“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孙郁书中第一章即开宗明义,于认识论、知识论和审美论三重审视中拾取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做法。鲁迅勘测珍贵的遗产,重新寻找精神的原态,在双向互动中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然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他不满于将古代经典作为凝固的存在接受过来,要从古人世界里发现当下精神,穿越,攀缘,他强调的是如何在文脉里梳理出思想的创造性。
鲁迅学有根底,整理《嵇康集》长达23年之久即是明证。校勘、考证、辑佚,他为之作序跋,并选逸文考、著录考各一卷。说理、发议论,“思想新颖,往往和古时古说反对”。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鲁迅说,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师心”和“使气”的嵇康、阮籍,确乎和鲁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考古知今,考古验今,考古证今,北魏郦道元、宋人陈亮、明末清初顾炎武一直沿袭着如此文化理念。孙郁发现鲁迅思想逻辑由章太炎而来,活用老师的学问,又透出老师没有的气息,文章风格也受了老师影响,既深刻警辟,也复杂多变。“章太炎由古逆今,鲁迅则今中含古,各自有创造性的表达。”如此开启了思考的雄浑、想法的跳跃等许多方面,古今互证,念之又念。正如鲁迅《忽然想到》一文的点睛之笔:“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自称是“学匪派考古学”的鲁迅建立在史学基础上的野性思考,偏好从“涂饰太厚,废话太多”的正史之外去寻找另一种可能,他于乡邦文献、无名者文字乃至禁书背后窥见生命真迹,又能发现破绽盲点,打开新领域,破除集体遗忘中的虚伪躲闪,让久被压抑的精神蠕活。1933年《经验》一文里,他不无感慨:“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鲁迅在1933年致曹聚仁信中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1934年《病后杂谈》中他更是直抒胸臆:“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今古、正野话题之余,《鲁迅与国学》第五章《非儒非孔的理由》中,孙郁从文化史角度观鲁迅与孔子,道出两人境界的相似。两人最大接近点是在一个传统失范的年代,选择了与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径。他们“不因苦而退,不因乐而休,超俗的人间情怀与思想境界,值得我们连声赞佩,赞佩”。孙郁主张摆脱对儒学思想的实用目的和负面看法,打破俗儒暮气,回复其有趣、自然、人道的温度,立高洁辞章,以古典学研究的精神“得其妙意而用之”。孔子和鲁迅同也不同,前贤希望克己复礼,而鲁迅思想的最核心之处乃战士精神。
《鲁迅与国学》立足近代思想源流来阐释鲁迅精神,墨学复兴中梁启超慷慨疾呼:“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底层意识,平民之态,关注大众,扶持青年,该书最后一章大书鲁迅钟情、弘扬的墨学精神,苦行隐忍,忘我牺牲,振世救弊,为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之目标提供了正面、切实的答案和题解。鲁迅从墨子传统、墨家价值中打捞出殊为可贵的遗绪,以道德完整性与社会责任感,做果敢的行动者,朗健的英雄者,古老精神成为现代思想的一部分。而鲁迅反感的是古代遗产使一些文人掉进自欺自恋中。他忧心的是读书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走不出暗处盲区,无法于广学博征中求得真义。
孙郁认为,鲁迅在杂感中自创出许多调式,以杂文观念代替文章的观念,在多样旋转的笔致里直逼现象的本然。中外参照,文章新命,于传统有吸收继承,又有打破冲决。“曲笔、冷笔、诗笔等手法,使表达获得了新的活力。”鲁迅重新延续旧文化最为有活力的部分,摄取旧遗产的精华而创造新文化,激活古老的文脉。孙郁以鲁迅作为典范样本来照亮当时的语境,“文除百代之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鲁迅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一起在“五四”前后的探索,是“现代知识人自我解放的一次疾走,他们也因此影响了后来的学术、艺术之路”。宋云彬曾在纪念鲁迅逝世十二周年时撰写《我所理想的〈鲁迅传〉》,文中不满于知识界对鲁迅学术思想的不够了解,呼吁认识鲁迅时代的重要性,“认识了鲁迅的时代,才能看清楚中国的前途,鼓起勇气前进”。
《鲁迅与国学》的深思与洞悉,让我们想起了近百年前茅盾《鲁迅论》中的一句话,鲁迅不肯自认为“战士”或青年的“导师”,“你大概不会反对我称他为‘老孩子’”。民族魂,中国的脊梁,承传择取中保存、开拓、建设,众议自说,他当之无愧。茅盾、宋云彬、徐梵澄先生以往的剀切推断,与新时代孙郁的高妙结论恰似合奏,收归一处,基调一致,堪称共鸣。
(作者:张洪,系辽宁出版集团编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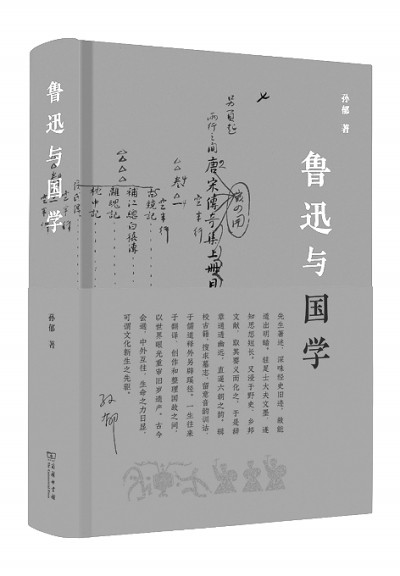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