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平、孟宪实合著的《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以下简称“《寻梦》”),近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继《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以下简称“《百年》”)问世之后,两位作者的再次合作。作为《寻梦》的底本,《百年》以讲述故事的手法,“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敦煌文物流散的历史,以及几代学人呕心沥血,追寻国宝,研究国宝,最终使‘敦煌学’回归故土的历程”。这本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展现的是“敦煌学”的当年面貌。时至今日,不少旧题有了新解,一些空白已获填补,多方领域得以推进。《寻梦》沿用《百年》的基本框架,并汇入大量新见史料和前沿学术成果,重新回忆敦煌文物发现、流散经过,梳理敦煌学人追寻国宝、研究国宝的历史,展望“敦煌学”发展前景,将“敦煌学”120余年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成就记述详备,被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盛赞为“一部真正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
传介学术成果,前沿且严谨
学术史研究的核心,是全面总结该学科某一时间段内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成就。因此,从《百年》到《寻梦》,增版扩容并非难事,两位作者只要搜集、补充近20年来的学界最新成果,便可续写敦煌学学术史,完成新著。但显然,《寻梦》所呈现的这部历史,在时间跨度和学术厚度上都远远超过《百年》,不仅有接续,更有改写。
仔细对读不难发现,《寻梦》保留了《百年》的基本框架,但对内部章节数量、题目、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修改。比如,《百年》三编所设章节数量不一,第一编“伤心敦煌”最多,有11章,第二编“四海寻梦”9章次之,第三编“魂兮归来”最少,仅6章;《寻梦》通过合并、增设,统一为每编10章。调整旧结构并不单纯出于形式美学的考量,也为了突出前沿成果和主要脉络。下编“魂兮归来”,展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中国“敦煌学”日益蓬勃的发展史,《百年》之后20多年来学术成果的纳入,自然需要增设章节和篇幅;而将第一编原有独立章节——“以德报怨的中国学者”并入“伯希和洞中挑宝”之下,则符合“伤心敦煌”这个特殊时段的历史脉络。“敦煌学”诞生头30年,“敦煌文物在乱世中发现,也在乱世中流离”,不仅从敦煌到北京,更从中国到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美国。对敦煌和“敦煌学”而言,多一方劫掠,便多一重苦难,全面深入揭示各国探险家的攫取经过,终究是“敦煌学”学术史绕不过去的一关。
得益于近年新见的日记、档案,学界获得了愈发详细的文字记载,因而对早年“敦煌学”历史的认知不断清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每一步推进,每一份学术成果,经过《寻梦》进入敦煌学术史,同时向大众读者传播。
不仅如此,为了尽可能还历史原貌,《百年》中许多人物姓名、机构名称、专著题名的中文翻译,以及宗教用语,在《寻梦》里发生了变化。甚至连日记、档案文献等原始文献的引用,《寻梦与归来》也依原格式转录。
述说学者心境,平和更自信
实际上,不论是普及性读物《百年》,还是学术史专著《寻梦》,都在梳理敦煌学学术史的同时,表达着鲜明的学术观点,传递着深厚的治学感情。学术史在续写,学术观点有更新,学者的感情和心境也发生着变化。
《百年》的出版是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彼时中国“敦煌学”虽已起步,在国际范围内却称不上领先。因此,以“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作为副标题,足以投射出学界自近代以来落后于人的心理状态。从清朝末年“朝野动荡,人心惶惶”的渲染,到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前“忍受着最后的寂寞”的千年莫高窟,《百年》讲述的不仅是藏经洞的悲剧命运,也是藏经洞故土的苦难历史。
而如今,《寻梦》的副标题改为“敦煌宝藏离合史”,一方面更加符合大众读者的趣味,另一方面也试图表达当今学界平和、自信的心境。长期以来,国人倾向将敦煌文献的流失归罪于王道士的愚昧无知和各级官员的贪婪无能。而通过《寻梦》的反思,文物主权、学术主权旁落他人,更应归结于学界的冷漠迟钝。于是,在“伯希和洞中挑宝”的末尾,在赞扬了中国学者以德报怨之后,《寻梦》新增“叶昌炽的愧疚”一节,其用意即正视学者之责。“抛开官僚的庸政懒政乃至腐败不说,抛开当时国人基本没有文物所有权概念不论,单就同样是一流的中西学者而言,一方(斯坦因、伯希和等)是不远万里四处考察、有着考古学等现代知识武装的西方学者,一方(叶昌炽等)是在自己的辖域内停下脚步、坐在书斋中收集探求金石之学的中国学者,两相比较,令人感叹。”敢于直面差距,是充满自信的表现。
厘清责任,才能更主动地扛起重担。“北京的学者除了一件一件地抄写,还有哪些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答案不言而喻。自此,中国学者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敦煌文物的主权,开始真正成为中国“敦煌学”发展的中坚力量。最令人振奋的是黄文弼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与考察,它标志着民族的觉醒,代表着学者的担当。勇担重任,是充满自信的表现。
而对发现藏经洞的小人物王道士,《寻梦》更不惜笔墨和篇幅,讲完他的一生。由此我们知道,道士打理破败了的佛教石窟寺,在清末河西一带并不少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藏经洞与王道士冥冥之中的命运。王道士因发现藏经洞被历史记载,但他不只是一个发现者,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虔诚、无知而又执着”的道士,他对藏经洞所做的一切,都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于是,面对斯坦因假托玄奘授命保管佛经,他会在意“上天的安排”;面对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的耍赖强取,他会因为不给足银两影响缮款愤懑不已;面对敦煌文物流散后民众的唾骂、官府的追查,他会颜面尽失,惶惶不可终日。《寻梦》借“三个女基督徒”所见所写,让这个用生命“守卫”佛窟的道士在信仰层面获得同情式的理解,这也是当今学者自信的表现。
近40年来,敦煌学人终于不再执念于曾经那段“黑夜连着黑夜”的日子,终于可以卸掉沉重的“囚徒”包袱,安心治学。从“敦煌学在日本”到“敦煌学在世界”的转变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神”为争取中国“敦煌学”的领先地位呕心沥血。泰然处之,奋勇直追,更是自信的表现。平和、自信的心境,离不开中国“敦煌学”的发展,更离不开国家的强盛。
展望学科未来,历久而弥新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所有未来,皆是可期。
从《百年》到《寻梦》,册数增加,开本变大,字数翻倍,章节扩充,配图丰富……种种变化无不折射出“敦煌学”的蓬勃发展。“敦煌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学科;而最初文献编目、文字识读阶段,便已呈现出跨学科的魅力。如文学方面,“刘半农辑录《敦煌掇琐》”为民间文学、社会生活、语言文学等领域提供材料,“逃往欧洲的郑振铎”意外查阅敦煌变文,得以引领中国俗文学研究;美术领域,日本学者泷精一、松本荣一师徒二人先后开展敦煌画调查研究;宗教方面,中国有“胡适追查禅宗资料”,日本有矢吹庆辉对古佚未传的佛典文献调查、羽田亨翻译《安慧俱舍论实义疏》回鹘文译本,等等。不仅如此,“敦煌学”研究形式还走出文字文献的天地,通过石窟、造像、绘画、摄影等领域得以展现,张大千临摹莫高窟壁画,罗寄梅拍摄数百张照片,无一例外。
而在两个甲子年后的今天,“敦煌学”非但没有衰微,反而绽放出愈发耀眼的光芒。“敦煌学”涉足的学科领域进一步扩大,除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社会等人文社会学者外,物理、化学、地理、气象等诸多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也投身其中。“敦煌学”文献的展示,从手抄录文到图文并录,从黑白胶卷到高清原大彩图,从纸版图录到电子数据库,与学界乃至大众的距离一步步拉近。“敦煌学”研究者,从最初单打独斗,到互相较劲争先,再到集团式合作。与此同时,“吐鲁番学”“于阗学”研究力量的注入,也使“敦煌学”更具活力。
因此我们坚信,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历经沧桑的“敦煌学”,归来恰少年,整装又出发。
(作者:段真子,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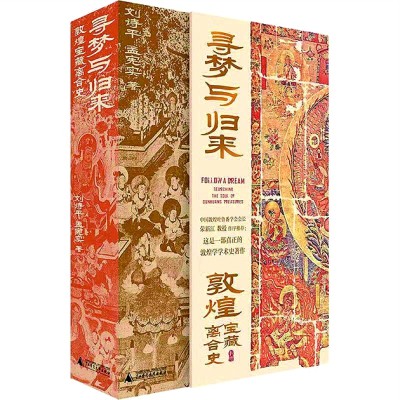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