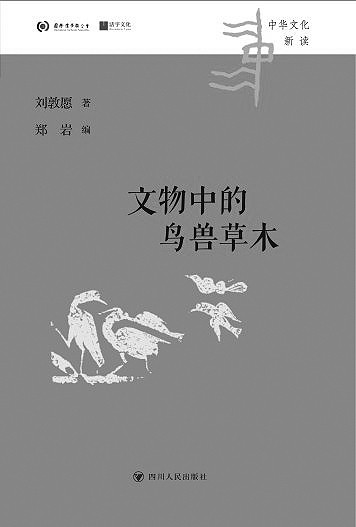【大家】
追溯山东大学考古学科的发端,自然会追溯到1933年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刘咸率学生参加董作宾主持的滕县安上遗址的考古发掘,甚至提前到1928年时任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发现龙山镇城子崖遗址。齐鲁大学是山东大学的前身之一,这样的学科溯源也自有其道理。不过,山东大学考古学科尤其是考古专业的全面发展还是始于刘敦愿先生20世纪50年代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又于1972年创办山东大学考古学本科专业。他重视田野考古的办学思想也一直引导着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发展。因此,刘敦愿先生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刘先生晚年致力于美术考古研究,在史前陶器艺术、商周青铜艺术与汉代绘画艺术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是我国美术考古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一
刘敦愿先生出身于书香之家,高祖父刘传莹为晚清举人、国子监学正,是一位经学家。祖父刘少淮为铁路高级职员,青年时期曾参加同盟会,精通法语、英语,兼通日语和俄语,晚年埋头于法文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刘先生年幼时就跟随祖父走南闯北,20世纪30年代初在郑州先后上了扶轮小学和扶轮中学,学校办学条件较好,他因而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1934年到1937年,他游历了河南省内不少古迹名胜,并到山东登泰山、游曲阜,去北京逛故宫、爬长城,尤其是1937年南京之行,参观了南京的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玄武湖和雨花台,更有机会参观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和即将赴英参加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预展的全部作品,包括许多传世的历代名画、书法、古籍版本、工艺品等国宝,还有安阳出土的甲骨、玉器、青铜器等考古新发现。这些经历对于酷爱艺术的刘敦愿先生的职业选择产生一定影响,以至于在就读大学这件事上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
1939年,刘先生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方画专业。抗战期间,国立艺专和中央大学都内迁到重庆,刘先生经常乘坐轮渡过嘉陵江到对岸的中央大学去旁听古代史课程,并深深为丁山先生讲授的《商周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两门课程所打动。丁山先生很赏识他,还专门为他“开小灶”。我曾经见过刘先生手抄本《春秋左传》,厚厚一摞,都是用毛笔誊抄的小楷,一丝不苟。刘先生笑着说,这都是当年丁山先生要求的“童子功”。数年的坚持,使得刘先生逐渐领悟到治学的甘苦与得失,也初步具备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1947年,经丁山先生的举荐,在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资助之下,刘先生辗转来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作丁山先生的助教,从而开始步入学术殿堂。丁山先生长达6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年龙门书局出版)都是刘先生一笔一画誊抄而成,此书“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与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涉及题材之广、考证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极具学术价值。这样的学习经历,使得刘先生在古文献、古文字方面打下坚实基础。1952年丁山先生因病去世,刘先生顿失名师,不胜悲痛。20世纪80年代,刘先生先后在《文史哲》发表《释“齐”》和《博学的古文字学古史学家丁山教授》两文,前者介绍了丁山先生曾在课堂上提到的对甲骨金文“齐”字的释读意见,后者则是对丁山先生生平和学术的介绍,以此感恩老师的栽培。
二
新中国成立后,刘敦愿先生便一直筹划创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为了积累经验,1953年经裴文中先生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洛阳烧沟汉墓发掘。1954年,开始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据《夏鼐日记》记载,夏鼐先生与刘敦愿先生在北京、青岛和济南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所谈话题均离不开山大考古专业创建事宜。为了满足开办考古专业的需要,刘先生同沈从文先生从北京琉璃厂购买了一批包括唐三彩在内的陶瓷文物标本,建立起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当时山东大学先后在青岛、济南两地办学,刘先生率领历史系师生在省内多地进行考古调查,其中尤以青岛、济南、日照、临沂、济宁等地为主,发现了一系列考古遗址。如1952年5月与青岛市文管会共同调查即墨县李家宅头村出土陶器,1955年春第一次调查日照两城镇遗址,1956年11月带领部分学生调查青岛市郊区东古镇遗址,1957年5月带4名学生调查两城镇、五莲丹土遗址,1959年4月调查山东临沂土城子、毛官庄、援驾墩、重沟、护台、石埠等遗址。1961年11月,以历史系韩连琪教授所收藏的清代画家高凤翰一幅画作的摹本为线索,刘先生等按图索骥,前往画家故乡胶县调查,发现了三里河遗址,并专门以《根据一张古画寻找到的龙山文化遗址》为题在1963年第2期《文史哲》撰文介绍这一发现,被学术界传为佳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74年、1975年连续两次对三里河遗址进行发掘,于1988年出版《胶县三里河》一书,大大丰富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2006年该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先生和同事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972年3月,山东大学获得批准设立考古专业,成为较早设立考古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办学之初,只有刘敦愿、蔡凤书、李肇年三位教师,刘敦愿任教研室主任。当年4月,第一届考古班10名学生入校。为了缓解师资不足的压力,刘敦愿先生先后聘请北京大学李伯谦、山东省博物馆王恩田、徐州师范学院阎孝慈讲授《商周考古》。接下来的两三年,除了以上三人之外,他又先后聘请北京图书馆徐自强,山东省博物馆张学海、朱活,故宫博物院李知宴等前来授课。1973年春,刘敦愿、蔡凤书等带领考古专业学生对泗水尹家城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实习,李伯谦、阎孝慈等参与指导。此时的刘敦愿先生已经55岁了,田野考古对他来说越来越力不从心,但他深知田野考古对于学科、专业发展的基础作用,因此一直十分重视田野考古。他经常拿飞行员飞行时间与飞行技术成正比来教导、鼓励新入职的年轻教师潜心田野考古,每个人都得过田野发掘这一关。重视田野发掘已经成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传统,即使在科技考古快速发展的今天,独立自主开展田野发掘实习仍然作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执行。
三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的春天。刘先生在大力倡导田野考古的同时,他个人的学术兴趣也开始转向美术史、美术考古,这自然与刘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密切相关。
对古代美术作品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刘先生做学问的初心。据他回忆,早在重庆跟丁山先生学习期间,“我对中国古代青铜器装饰艺术很感兴趣,请问是否需要研究,是否已经有人从事研究。先生说这还是个空白,目前自然没有条件,‘我正在全面整理金文资料,做重点器物的铭辞断代,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做系统的艺术研究了’。”以年代学为基础,在考古学框架内做美术史研究,这样的研究旨趣决定了刘先生的考古研究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
20世纪80年代之后,刘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青铜器装饰艺术的论文,就是在断代基础上进行的美术史、美术考古研究,是自己初心的回归。而在此之前的六七十年代,刘先生对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陶器工艺与装饰艺术的研究,既是以对常年考古调查发现陶器标本所做观察为基础,又何尝不是初心的体现呢?刘先生1959年发表的《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一文(《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就是一篇集考古、美术史和制陶手工业三方面知识于一体的大作。这篇文章的素材大多来自他亲身考古调查获得的陶片标本,其中有关制陶技术部分,大多基于他对山东农村制陶作坊所作考察的分析,而关于艺术部分,则有赖于他的美术功底。刘先生指出,龙山文化陶器的装饰工作往往是同陶器本身的塑造与烧制结合;龙山陶器的器形比例匀称和谐,质地轻巧,与轮制技术的精湛有着密切的关系;龙山陶器都是单色的,爱好单纯的颜色是其特点;至于在陶器上运用划纹、压纹、印纹、镂孔、附加堆纹与塑造动物形象等具体的装饰方法也都是在不破坏上述特点的原则下进行的。因此,龙山陶器的装饰方法是非常经济而纹样母题又是非常简单的。此前有关龙山文化陶器纹饰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如此细致的观察、认识则不多见。该文最大的贡献,是指出了龙山陶器纹样也有相当复杂的,这就是日照两城镇遗址“一再发现有类似铜器的花纹”,这种纹样是曲线与直线的结合,刻画比较细弱、潦草、稚拙,很像从什么东西上临摹下来的,并推测“是不是这时已经有了铜器,陶器仿自铜器,还是两者都是从某种工艺品上仿效而来(例如织物或刻骨之类的图案)”。待到20世纪70年代刘先生从两城镇征集到那件著名的带有兽面纹的玉器之后,才得识此类纹样母题的真面目,也证明刘先生当年的推测确有道理。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与竹编艺术》一文,则显示出刘先生对史前陶器装饰持续的关注。从文章题目中不难猜测该文的研究内容,大汶口文化流行的镂空陶器直接模仿自竹编艺术,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但在陶器上采用这种违反陶土性能的“超前”做法,一定是有着技术前提和艺术设计基础,刘先生认为:“装饰艺术与器形结合起来考察,与其称之为图案移植,还不如说是陶器对编织物的直接模仿。”若这样的讨论仅限于史前资料,该观点的立论基础显然具有很大的推测性质,而该文的精妙之处还在于结合商周青铜器和古文字资料,寻找到不同材质器物之间的关联性,又从先秦文献中寻得上古北方盛产竹子的若干记载,从而论证陶器模仿编织物观点的可信性,正可谓左右逢源,相得益彰。刘先生这种贯通史前与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在分科日益专业化的当下愈益显得难能可贵。
刘敦愿先生学术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还是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的解读。这些论文大多发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他的学术活跃期。其学术观点之所以至今深受学界重视,与刘先生一生的求学和治学经历密切相关。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刘先生比较早地扬弃了流行已久的“图腾说”,将商周青铜器或三代艺术品纳入“历史”与“考古”场景加以考察,他对多种青铜器纹样意义的解读,即使对于信从近三十年来影响甚广的三代礼器动物纹样“通天说”“媒介说”的学者而言,读起来也丝毫不会有不合时宜的感觉。如对饕餮(兽面)纹的起源与含义问题的探讨,从良渚、龙山玉器纹样,到二里头铜牌饰、商周青铜器纹饰,再到汉画像石、后世民间艺术乃至希腊瓶绘,从《春秋左传》到《吕氏春秋》再到《隋书·东夷传》,论证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样不过是安置在门户上的“兽头骨角”的复杂化与艺术化,“应是象征威猛、勇敢、公正等等,用意明确简单,未必含有《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云云的那么一套神秘复杂的故事”。又如《夜与梦之神的鸱鸮》是一篇对商周青铜器常见的猫头鹰题材进行解读的论文,刘先生在广泛收集史前、商周以至汉代有关猫头鹰题材文物和纹样的基础上,结合古文字和历史文献中关于猛禽、夜禽的描述,勾勒出商周时期有关鸱鸮崇拜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国人对于猫头鹰好恶观的变化过程,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其中对于晚商时期鸮类题材的美术史观察,从立体雕塑品重心的处理方式,到平面镂刻中头部与身体正面透视法的运用,分析十分精确,配以刘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读来让人兴趣盎然,尤其是对于习惯于阅读考古报告中单调的器物形制纹饰描述的人来说,常常会产生恍然大悟的感觉。在一篇讨论中外猛禽崇拜的文章中,刘先生从古埃及和古希腊艺术品中的猛禽入手,反观中国古代猛禽不那么突出的史实,因此文章取名为《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的鹰崇拜》。虽然当时考古发现的这类例子有限,但刘先生仍然寻找或辨识出数十件相关题材的文物,其中有见于史前时期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者,而尤以山东龙山文化数量最多,个中原因自然与东夷族群鸟崇拜有关,尤其与少昊氏“高祖鸷”有关。商和西周鹰类题材很少,与鸱鸮形成鲜明反差。刘先生还敏锐地观察到,春秋战国见到的鹰攫蛇或鹰蛇相斗的题材,蛇为一首双身,显然具有吉与凶、祸与福相克之类的含义,这类的鹰应具有神性。笔者注意到,刘先生所举这类题材青铜器的例子,有一件出土于安徽寿县楚墓的青铜盖饰,老鹰作展翅飞翔状,双爪攫获一首双身的蛇,巍然屹立在器盖上,这样的造型几乎与近年来陕西石峁出土的陶鹰如出一辙。石峁所见这类陶鹰身体壮硕,发掘者推测是一种在祭祀或礼仪场合使用的具有神性的陈设品,只是因为足端残损,不知道当初是否也在鹰爪之下塑造有这种一首双身的蛇?
刘先生讨论过的动物题材十分广泛,仅从下面所列题目就可窥见一斑,如《含义复杂的中国古代虎崇拜》《作为财富象征的牛纹与牛尊》《湘潭豕尊与古代祭祀用豭》《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鹿类描写》《神圣的昆虫——蝉纹研究》《貘尊与鸡卣》,几乎涵盖了商周青铜器纹样中所见的所有动物题材。动物纹样之外,刘先生的关注范围还包括其他常见纹样,如《青铜器勾连纹探源》《圆涡纹与〈考工记〉的“火以圜”》等,这类纹饰常以所谓“底纹”或辅助形式存在,但也各有源流,如认为勾连纹原是竹席所用,然后移植到青铜礼器之上,并引用《礼记·檀弓》所载曾子临终“易箦”的故事,指出看似普通的竹席也有等级之别,而竹席上的图案则是区分贵贱的主要标准之一。这些观点逐渐被近年来湖湘地区楚国的竹席实物所证实。刘先生的大作往往就是这样,从小处着眼,解决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除了这些长篇大论,刘先生还经常写一些类似随笔的短文,一般是一两千字,如《给动物系环带牌的故事》《甘肃黑山岩画狩猎图像中的飞鸟》等。无论篇幅长短,文章均言之有物,一般都是从某一题材的造型和纹样出发,结合先秦文献以及后世笔记野史,寻绎解读其原本含义,其结论往往是发人所未发,给人以深刻启示。这就是刘敦愿先生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最近,郑岩教授将刘先生的部分论文以《文物中的鸟兽草木》为题结集出版,让对刘先生美术史、美术考古感兴趣的读者免于搜寻之苦,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四
刘先生经常慨叹晚年有幸赶上了学术昌明的好时代,因此愈发珍惜点滴时光,勤于笔耕,与时间赛跑。在病重期间,他躺在病床上数次说起自己能在有生之年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感到比较满意,但同时又能明显感觉到他对人生的留恋。2018年是刘敦愿先生百年诞辰,有媒体在采访了郑岩教授和我之后,用“一位错时的考古学家”来概括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心目中的刘敦愿先生,我想刘先生本人对这一概括也会表示认同的。
刘先生非常热爱田野考古。1958年,从野外调查归来、口袋中装满陶片的刘先生给刚刚出生的三儿子取名为刘陶,以此纪念野外考古调查的新收获。他对考古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改革开放后,年届六旬的刘先生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人才培养上,对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培养尤其强调田野考古。他总共培养了4位研究生,除了亲自讲授商周考古之外,特别强调考古实习,为研究生的调查、发掘实习尽可能提供方便条件。而在毕业论文的选题方面,他也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入手,做最基础性的研究,当时的基础研究就是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的陶器编年。第一届研究生倪志云师兄写的论文是济南大辛庄遗址陶器编年,以此为基础讨论商史问题。第二届的栾丰实和我,分别选择了泗水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陶器分期,兼涉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第三届许宏也是以大辛庄陶器编年为基础讨论鲁北地区商文化的性质等问题。实际上,倪志云师兄的美术功底相当好,读书期间就发表过有关史前彩陶研究的文章,但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研究都是以年代学为主的大背景之下,陶器编年无疑是最具前沿性的问题,这样的选题显然也最容易获得专家认可。
记得1984年秋,刚刚步入研究生一年级的我陪同刘先生前往河南安阳参加首届商史讨论会,夏鼐、胡厚宣、张政烺、田昌五、李学勤、邹衡、安金槐等著名学者都参加了,可谓大家云集。刘先生提交大会的论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关于鸱鸮的大作。因为此前不久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体积最大、形制最为精致的一件商代青铜鸮尊,这篇论文是非常适合在安阳商史会议发表的。不过在会议分组时,这篇论文究竟应该放到商史组、商代考古组还是古文字组?似乎都不合适,而且会议上就没有类似的美术考古论文,最后好像是放在考古组发言讨论。后来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并没有将该文收录其中,大概小开本的论文集不大适合刊登满是线图的文章吧。不过,这篇大作在会下还是受到不少学者的好评。陕西师范大学的斯维至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徐锡台先生都跟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徐先生还特别嘱咐我要好好跟刘先生学习美术考古,还说到这个领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目前国内研究者很少,但在国外美术考古一直是考古的大热门,将来我国也会重视云云。我虽然不能全都理解,但感觉他们说的是对的。因为在此之前,刘先生关于美术考古的大作已经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教授、艾兰教授,美国学者张光直教授都曾来山大拜会过刘先生,并以他们的大作相赠,一些影响很大的美术史乃至美学类图书也征引过刘先生有关青铜器纹样解读的观点。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美欧学界关于三代青铜器美术考古研究的论著被大量译介到国内,其中尤其以张光直先生的祭祀美术、萨满说、动物通天媒介说等影响最大。这些观点一般是把青铜器动物纹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与之相比较,刘先生对不同器物造型、不同纹样母题的系列解读真正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研究的范围也不仅仅限于动物主题。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反而愈加显示出独特的学术魅力和价值,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从这一点来说,昔日的“错时”不正可作为今日的应时、适时吗?
(作者:方辉,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