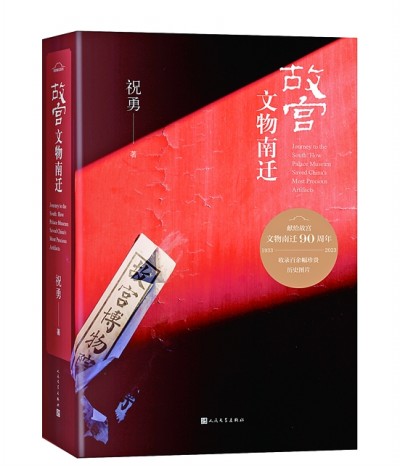编者按
在故宫600年、故宫博物院近100年的历史上,文物南迁是至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那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故宫文物南迁的壮举,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90年前的那一段壮举,非常值得且有必要去专门书写。
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日前,一部聚焦故宫历史上那段最为惊心动魄的南迁历程的《故宫文物南迁》,付梓成书。长期以故宫为书写对象的祝勇先生,以丰赡的细节还原了历史的原貌,以翔实的考证重建了南迁之路。《故宫文物南迁》甫一问世,即入选五月光明书榜。本期光明书榜版,诚邀作者撰文,与读者一同感受祝勇眼中的故宫文物南迁之旅。
在连天炮火中,保护中华文明史上的无上珍品
1933年,新年刚过,故宫及其所在的北平城便岌岌可危。为了躲避战乱,保护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珍品免于损毁劫掠,故宫人带着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开紫禁城,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旅。除了故宫博物院文物以外,故宫人还带着古物陈列所文物5414箱、颐和园文物640箱8包零8件、先农坛文物88箱、中央研究院文物37箱、国子监文物11箱、内政部文物4箱,共计19621箱72包零8件文物奔赴中国南方。从这一天开始,故宫前辈们筚路蓝缕,负重远行,克服了九九八十一难,终把文物护送到远离硝烟的大后方。又在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带着大部分文物平安归来(一小部分运至中国台湾),从而完成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最伟大的壮举。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都已经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则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缘何能够携带着将近两万箱文物奔走于道途,在连天的炮火中,保护了中国文明史上的无上珍品,使中华文明的长河不被战争截断?
故宫文物件件堪比金枝玉叶,加之19000多箱的天文数字,纵然在和平岁月,安全运输如此巨量的文物也并非轻而易举。在这些文物中,有总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8亿字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佛学大百科全书、清朝第一部泥金写本、共收集1000余部佛教经典的《龙藏经》,有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更有瓷胎薄如蛋壳、胎体厚度大多在一毫米以内、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的填白脱胎瓷器……任意一件,都有无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它们又属于“易碎物品”,运输过程中必须轻拿轻放,稍有不慎就会玉毁椟中,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随《四库全书》一起南迁的,那十件先秦石鼓体型庞大。它们每件高三尺上下,浑身肌肉浑圆,上窄下大,中间微凸,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神秘文字,人称“石鼓文”(大篆),文字笔法奇异,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真正的“石头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有人说一字可抵万金。这些石鼓在地下埋藏了千余年,上面镌刻的文字在唐代出土时已无人能识,挖掘出它们的人们(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人)于是焚香跪拜,惊为天赐神物。自唐至宋,自宋至清,一代代学者(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韦应物、韩愈、杜甫、欧阳修、苏轼等),一代代君王(唐肃宗、宋仁宗、宋徽宗等),都曾垂青于它,邓石如流连过,吴昌硕摹写过,康有为更是称它为“中华第一古物”。到民国,一位名叫马衡的学者认真地打量它们,写下一部名垂考古学界的专著《石鼓为秦刻石考》,宣告了旧金石学时代的结束和现代考古学的兴起。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有具体而细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我的写作,就为了让那段历史不被时光湮灭
90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让那段岁月显得有些陌生。我知道我的写作,实际上就是一次抵抗遗忘的行动,让那段珍贵的历史记忆,不被时光湮没,历史主题写作的强大意义正是蕴含于此。
在动笔之前,我对那段历史的追踪主要通过三个渠道——重访历史现场、收集相关档案文献、采访亲历者。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我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在新冠疫情的间隙里,我在上海市图书馆查看当年沪上的报纸,哪怕有关故宫文物的一则火柴盒大小的报道,都会令我兴奋不已。在发黄的纸页中,我看到上海《申报》1933年4月28日对第四批文物到达上海的报道是这样的:“故宫四批古物,六千二百六十七箱,由故宫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押运,于二十三日,载三列车运抵浦口后,即卸装建国轮,于二十六日午二时起碇驶沪,昨(27日——引者注)午十一时抵埠,泊金利源码头,午后起卸,仍存天主堂街二十六号大厦。闻至二十九日始可卸完,至第五批古物约在一周后亦将运到,兹将各情探志如后……”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火绵延到存放故宫文物的上海和南京,已于1936年由上海转运至南京朝天宫库房的文物又要悉数转移,分北、中、南三路运往西部的大后方。几年中,我先后抵达南京、上海、西安、宝鸡、重庆、成都、乐山、峨眉、桂林、贵阳、安顺等地,追寻故宫先辈的脚步,寻找当年的历史痕迹。值得庆幸的是,当我出现在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现场,我发现当年的许多遗迹依然屹立在原处,捍卫着曾有的记忆。每一次发现,都令我无比激动和欣喜,让我对下一次的寻找充满期待,进而不断累积着我对于此番写作的信心。
在重庆,我第一次走进川康平民银行仓库旧址。1938年1月,故宫文物抵达重庆后最初的存放地之一。这座旧址,位于今天重庆市渝中区打铜街上。它庞大的体量、复杂的内部结构,以及坚固的主体构造,都令我深感惊异。从大楼侧面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走进去,踏着布满尘灰的木板楼梯拾级而上,发现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仿巴洛克式砖木结构建筑楼共有五层,由于大楼前后有高差,局部为六层。巨大的厅堂,如今空空如也。那空荡荡的地方,正是当年摞满文物箱的所在,我甚至听见了前辈们负重行走时发出的急促呼吸声。尤其令我震惊的是,最下一层是一间巨大的地下金库,有一道铁门,是一道密码门,德国制造,钢板厚实,据说一发炮弹打不透。这间金库原本由银行用于存放黄金,80多年前,故宫文物箱密密麻麻,叠摞到接近房顶,最下的一层,垫了很高的枕木,让文物箱与地面保持一定空隙,以便防潮。在库房的高处,朝街的一面,有一排通气孔,以保持仓库的空气流通。故宫文物放在这里,不仅安全,而且干燥,即使在今天,也叹为观止。
这几乎是当时重庆市区最宏伟的建筑了。然而即使这样一座体量巨大的大楼,也只能容纳3000余箱文物。那么,剩下的巨量文物在哪里存放呢?不得已,故宫博物院又租用了慈云寺边的安达森洋行等处。在安达森洋行,又存进了3694箱。这家瑞典人开的洋行主要经营鬃毛、腊肉和百货生意,有六栋依山而建的巨大仓库,全部是大梁穿斗结构,石质基座,筑土为墙,背靠青山,面对大江,故宫博物院租下了其中四栋。此后便开始按照故宫规范标准,清点、核对、编号、一箱箱登记入库。这批文物包含了青铜器、瓷器、书画和玉器,其中不乏苏轼、黄庭坚、米芾、唐寅等大家的传世之作。为了给文物腾出空间,洋行的老板安达森先生用标准的四川普通话命令:把仓库里的腊肉全都甩了(“甩了”是四川话,意为“丢掉”“不要了”)。
后来为了躲避日军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故宫文物再度启程,踏上西去的路程,几经辗转,最终落脚在乐山安谷乡,是为西迁中路。西迁北路文物,1937年由南京出发,经铁路运至西安、宝鸡,后由汽车运输,在大雪中翻越秦岭,进入四川,在峨眉山脚下落户。西迁南路的文物,经过桂林运至贵阳,又为躲避日机轰炸而转至安顺。
在考察了西迁北路、中路的一些遗迹后,我又踏上当年的西迁南路,远上云贵高原。在贵阳城,我找到了当年的文物存放地——滇黔绥靖公署官邸,俗称“毛公馆”。那一刻的兴奋之情,无以言表。尽管我在文献档案上无数次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当我穿过高楼林立的闹市区,找到这座被围困在建筑工地中的老洋房时,依然惊讶于它的宏大壮观。这座建筑由主楼、跨楼、厢楼等几部分组成,砖木结构,宽檐环廊,圆拱门窗,极为华美考究,只是历经数十载风雨,已经剥蚀残破。所幸它还没被拆除,依然顽强地守护着属于故宫,也属于我们民族的那一段记忆。
一方面,我为自己能目睹这些故宫文物抵达的地方而深感庆幸,文献档案中那些枯燥、陌生的地名,变成铁路、公路、河流、房屋、田野,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让历史变得立体、饱满和生动;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这些宝贵遗址在某一天会被全新的城市规划从大地上抹掉。我突然想起自己曾在重庆安达森洋行旧址的夯土墙上见到的两个字:“不拆”。令我怦然心动的两个字,也令我热血沸腾。因为这些建筑本身,就是历史的纪念碑。
书生报国,体现为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除了田野考察和搜集史料,我其余时间几乎都用于本书的写作,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中。自从在电脑上敲下第一个汉字,我便随着那些逐渐增多的一行行,进入到那个不寻常的时空中。
故宫文物南迁,这本身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包裹在这个大事件中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平常而艰涩的日子。写作越是深入,我就越能体会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书生报国与军人报国,本质相同而方式不同。书生报国,不体现为轰轰烈烈的出生入死,而体现为长期而艰辛的坚守与付出,体现为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体现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进取精神。
在日军炮火的追击下,筹集交通工具无比艰难,他们却从没有丢下过责任,一日复一日、一站接一站地转运文物,每到一地,都要以极大的耐心与小心,进行防虫、防潮、防火和防盗处理。无论在南京朝天宫库房,在重庆安达森洋行,还是在乐山安谷乡,为了防潮,故宫人用木条钉成屉子,把文物箱放在上面;峨眉办事处更是发明了一个新办法:把木墩做成“凹”字形,缺口向上,排成一行,架上木杠,再放文物箱。这样一来,文物箱就通风了,也方便检查白蚁。然后,就是漫无止境的整理、索引和编目。在乐山、峨眉,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按照文物所在的箱、行、列、库一一编入目录。当马衡院长和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前来视察时,抽查几箱文物,他们说出箱号,不出5分钟,工作人员便都找到了箱件。
1946年,故宫文物东归。1947年3月,原存乐山的文物运抵重庆向家坡山腰,存入原贸易委员会仓库。向家坡坟墓很多,滋生大量白蚁。白蚁非常厉害,一天之内,能把一箱的东西吃个精光。空房原来都有地板,故宫人员把地板拆开,发现地板的龙骨已经被白蚂蚁吃空了。为了防止白蚁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入箱中,据故宫学者那志良先生回忆,工作人员在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白蚁要想进入箱件之中,必须爬过鹅卵石,它们必须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才能抵达箱子。只要安排人员定时观察,就可以知道白蚁是否爬上木箱。
即便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他们也像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忍受着时世艰困、岁月清寒,却没有一天放弃过学术事业。在峨眉武庙,存放着西迁北路文物共7286箱。那十件先秦石鼓,就存放在武庙西配店库房里。那志良先生在武庙西配殿隔出一个小房间,作为自己的宿舍,从此与石鼓为邻。每天早上起床,他就到大佛寺去,在那里办完一天公事,晚间回到武庙。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石鼓通考》。
在西迁南路,云贵高原上的边塞小城安顺,庄尚严先生一家忍受着生活的窘困,内心却无比从容。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回忆说,尽管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而晚上全家人其乐融融,看书和做功课,全家人的心与桌上那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一直亮着。
每次目睹他们的照片,我都丝毫不曾感觉他们是离乱的书生。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他们的内心那么笃实坚定,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坚不可摧的。
我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了人的选择,又从人的选择中看到了未来。
“位卑不敢忘忧国”,故宫人如此,村野匹夫亦如此
南迁路上,也曾有许多意外发生。1943年6月8日,峨眉县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危及故宫文物。《峨眉县志》记载:“6月8日,下午1时40分,峨眉城区发生一次特大火灾。人们称‘六·八火灾’。据一份官方资料称:烧死9人,警察失踪2人。烧毁房屋1363幢,受灾人数6778人,估计损失折合法币73047.123万元。”我曾经不止一次到峨眉考察,今天的峨眉县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一条青石板砌成的主街两边,全是木构的房屋。那时的峨眉,还没有自来水,更没有自来水枪,人们从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灭火,却是杯水车薪。大火一旦烧出西门,故宫文物将遭受灭顶之灾。峨眉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纷纷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庙库房周围拆出了一片“隔离带”。终于,库房里的文物躲过了这场大火,安然无恙。
这是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感人至深的一幕,这样的场景,在南迁岁月中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些历史的细节让我容动,让我笔下有神。我并非只想在纸上复现那段历史,更希望通过我的笔,重现那代人的精气神。故宫文物在整个南迁过程中基本无损,靠的不全是故宫人的神勇与智慧,还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所谓“位卑不敢忘忧国”,故宫人如此,村野匹夫亦是如此。这正是全民抗战的真谛所在,是抗战之所以胜利、故宫文物南迁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故宫文物南迁,让故宫人与途经地区的乡土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仍存留在乐山安谷乡的“功侔鲁壁”牌匾,见证着这样的血肉联系。离开驻留了将近8年的乐山、峨眉之前,马衡院长亲笔书写了“功侔鲁壁”牌匾,向存放过故宫文物的安谷“一寺六祠”,以及峨眉的武庙、大佛寺、土主祠、许祠表达谢意。2000多年前的秦代,孔子第九代孙孔鲋得知秦始皇即将焚书的消息后,将家中祖传的《论语》《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封藏在孔子故宅的墙壁内,躲过了秦火,也躲过了楚汉相争的战火。“鲁壁”(孔子故宅的墙壁)的传奇,让中华文脉经过焚书坑儒这个路口,延续了下来。故宫文物南迁,亦是在文明的传续受到威胁之际,承担起延续文化命脉的责任。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如果缺少了全体国民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写作《故宫文物南迁》一书的同时,故宫博物院还拍摄了一部同名纪录片,由我作总导演。2020年是紫禁城肇建600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这一年年底,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的先导宣传片在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上发布。在气势磅礴的音乐里,先导宣传片映现出这样的字幕:“故宫文物南迁,离不开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是抗日战争中振奋人心的一幕,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故宫文物南迁出发之地,是他一生魂牵梦萦之所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2972箱文物(归属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分三批运往台湾,在全部故宫南迁文物19816箱72包15件13扎(其中有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南迁文物,其他为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中,占比不足15%。
庄尚严先生随第一批运台文物赴台。上船时,孩子们问他:“台湾,是什么地方啊?”庄尚严先生说:台湾就是一个海岛,自古都是中国的土地,后来被日本占据了,现在又是我们的了。
这是一次不知归程的远行。临行时,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庄尚严的手,说:“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
2018年,我在故宫博物院第一次见到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他1938年出生于南迁途中,去台时只有10岁。再见面时,虽已是耄耋老人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那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更是令我如沐春风。我陪他一起走进北京故宫宝蕴楼,那里是文物南迁出发的地方。我们在一张照片前驻足了很久,那是1947年春天,故宫文物在重庆集中之后,故宫南迁人员与家属怀着轻松的心情前往重庆南温泉郊游时拍下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写:“故宫博物院旅渝同人南泉修禊留影”。照片上的庄灵,被父亲庄尚严抱在怀里,当时只有9岁,还不知他未来的岁月将在一个名叫“台湾”的岛屿上度过。照片上许多人的名字,我们已经叫不出来了。我向庄灵先生请教,他竟然能够一个不落地唤出每个人的名字。幸亏见到了庄灵先生,使我得以在《故宫文物南迁》这本书中,准确地写下了照片上每个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永远值得被记住。
那一次与庄灵先生交谈,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感人的细节,后来也写进了《故宫文物南迁》一书:庄尚严先生晚年病重,在台北荣民总院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先生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
“北平。”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还是他的故乡——北平(北京)。
那是故宫文物南迁出发的地方,也是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
当年踏出故宫的时候,他或许未承想到,这趟旅程越走越远,最终在海峡另一端的台湾岛上落脚。
在文字的世界里,重构波澜起伏的岁月
2010年6月,故宫博物院发起了“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南迁路”考察活动,沿着故宫前辈们当年的南迁路线,考察了4省8市,探寻37个重要的故宫文物存放地点。我遗憾未能参加那次考察,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因工作关系,有机会多次造访当年文物南迁所经过的地点。随着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90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逐渐展开。在我心目中,眉目也一天比一天清晰。2019年,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先生为首席专家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学术项目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有幸担任四个子课题之一“故宫文物南迁记忆再现与重构”的负责人。也是在这一课题的督促下,我开始系统性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翻阅尘封数十载的历史文献档案,进而构思一部名为《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之书。
终于,作为历史非虚构作品的《故宫文物南迁》一书问世了。紧接着,我又马不停蹄,投入以故宫文物南迁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国宝》的写作中。多年的积累,尤其是为《故宫文物南迁》一书所做的调研采访、田野考察、文献搜集,使这部小说的写作变得水到渠成。三年疫情,我被困书房,潜心写作这部规模宏大的历史长篇,在文字的世界里,重构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孤苦与无助的日子里,我心中满满是前辈们的果敢与坚韧。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
(作者:祝 勇,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本文图片均选自《故宫文物南迁》)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