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编者按: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1月27日晚去世,享年104岁。杨苡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也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作为译者,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的翻译至今仍然是这本名著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译林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以下简称《杨苡口述自传》)是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学者余斌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将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该书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
2023年1月27日晚,104岁的翻译家杨苡,在“世界文学之都”南京,走完了她传奇而精彩的一生。她将呼啸山庄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也将自己的人生谱写得跌宕起伏。她渴望自由,在山河破碎时,不做金丝雀,大呼“我要做觉慧”;她乐观豁达,在四海无恙后,满怀“等待和希望”,常说“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我们失去了眷恋祖国的爱国女性、崇尚好玩的人生智者、充满温情的翻译大家。她将化作一颗启明星,默默守护文林,供人时时仰望。
杨苡先生原名杨静如,五四运动同龄人,1919年诞生于天津的一个不平凡家庭。她在中西女校接受了十年基础教育后,正值国破家亡,困顿之中受到巴金启蒙,冲破家庭束缚,前往僻处西南的“中国地”,在西南联大接受三年大学教育,密切接触许多著名学者、作家以及进步青年。在此后数十年岁月中,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珊、巫宁坤、许渊冲等人交往深厚,共同见证了国家的深重苦难与日渐昌盛。她因格外高寿,一百零四年的岁月里,见惯了人来人往,送走了故友亲朋,无论是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还是习焉不察的细密往事,均以时间的刻度,或浓或淡、或深或浅地被她铭记于心。二十余年前,因一次偶然的上门送书,杨苡结识南京大学余斌教授。后来,二人无意中以兴趣为导向,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聊天”。杨苡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少女般的细腻心思,以碎碎念的方式,向余斌讲述过往,余斌以巧妙的构思和流畅的文笔,为我们呈现出了这部厚重的《杨苡口述自传》。
冲破旧家庭束缚,“我要像觉慧”
杨苡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曾祖父杨殿邦官至漕运总督,叔祖父杨士骧官至直隶总督,叔祖父杨士琦则是袁世凯智囊,祖父杨士燮中过进士,曾任杭州知府、淮阴知府。杨士燮兄弟几人作为洋务派,思想较为开明,将儿辈大多送出国留学,或日美,或英法。杨苡的父亲杨毓璋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当时的北方金融中心天津做到中国银行行长,善理财,与北洋政府往来密切,徐世昌曾送他“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联语,表彰他的贡献。然而,正值壮年的他因偶感风寒,于杨苡出生几个月时即不治身亡。杨毓璋除太太以外,还有两房姨太太。杨苡的母亲徐燕若是大姨太,杨苡和姐姐杨敏如、哥哥杨宪益属于“庶出”,但因杨毓璋的太太只生了两个女儿,杨宪益自小跟随太太生活,是位名副其实的“少爷”,备受家族宠爱,与杨苡姊妹地位悬殊。父亲去世后,这个庞大显赫的家族逐渐走向衰落,在杨苡十来岁时,因为三叔私自拿钱贩盐,运输船只翻覆,钱打了水漂,杨苡童年生活的花园街大宅院都被变卖以维持家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渴望进步的青年想投入时代洪流,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无数人的爱国情怀被激发。然而杨苡这样生于大家庭、生活优裕的青年,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往往需要挣脱来自家庭的束缚,激烈的冲突之下大多时候比较苦闷,只能通过给友人写信、埋头写作或者参加社会活动、革命运动等来纾解郁结。比如杨苡一生的精神导师巴金,便是从写作中寻找自我的意义与价值。杨苡中西女校的同学蔡惠馨,家里是买办阶级,高门深院,但她也深刻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无形压力,二人因此要好。随着年龄增长,视野逐渐开阔,杨苡越来越想挣脱家庭的羁绊。
高中刚毕业,杨苡觉得家里太闷,出去报各种班,学踢踏舞、画画、钢琴,尽量不待在家里,即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排遣心中苦闷,家庭桎梏和各种规矩却如影随形,“听上去我的生活挺丰富多彩的,事实上那段时间我很苦闷。我的苦闷并不是毕业了之后才有的。上高中时我就经常有这种感觉了,特别是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母亲对我的管束特别严,哪儿也不许去。平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我的好朋友刘嘉蓁可以自由自在地参加各种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我也有参加的冲动,谁甘心做亡国奴呢?但我是根本出不了家门的,对那些同学只有羡慕”“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这也更加坚定了杨苡冲破家庭,走向自由的决心,更促使其不久之后离开家庭庇佑,独自南下求学。
杨苡女儿赵蘅在《为妈妈杨苡画像》文章中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舅舅从英国给外婆写信,劝她允许妈妈离开天津,说妈妈的性格不合适留在沦陷了的天津,外婆这才放手让妈妈去了西南联大。哪知联大偏以自由闻名,教学自由,选师自由,结社自由,师生打成一片,让妈妈觉得自己像只飞出笼子的鸟儿,开心极了。”正是在哥哥杨宪益的“鼓动”下,杨苡得以顺利进入西南联大。从传统家族到西南联大,杨苡崇尚自由、烂漫爱玩的天性得以完全释放,身心得到极大宽慰。虽然物资匮乏,环境艰苦,但对杨苡和她的朋友来讲,西南联大的自由氛围,不拘一格的讲授方式,广大学人的报国热情,各类社团的异常活跃,等等,共同组成了他们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
杨苡能够拥抱自由,冲破家族樊笼,离不开巴金的鼓舞。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就具有颇高知名度,许多进步青年都给巴金写信。杨苡年轻时就读过巴金的作品,他的《家》《雾》《雨》《电》等小说,《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的编译作品,都对青年杨苡产生重要影响,奠定了她追求自由的精神底色。杨苡曾说“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当时十七岁的杨苡大着胆子给巴金写长信,从对他作品的喜爱和对他的崇拜写起,谈到对自己家庭的不满,向巴金表示自己要做觉慧,出走家庭。巴金爱护青年,更清醒地体悟到一个女子想要独自闯荡的艰辛,反而劝她要念好书,有耐心。但是渴望自由的种子一旦种下,很快就会生根发芽,从而一发不可收。
十年中西女校,形塑现代知性女性
中国传统社会不太重视女性的知识教育,而是注重其技能培训和道德规诫。杨苡出生的年代正值传统社会结构崩裂,新文化运动兴起,女性教育逐渐盛行,就此培养出了一代杰出女性。
杨苡能够受到完整教育,与其母徐燕若息息相关。作为庶母,她极其重视子女教育,坚定地认为儿女必须上学才能有出息,将三名子女全部培养成才。杨宪益自英国留学归来,与夫人戴乃迭一起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取得瞩目成就;杨敏如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她的丈夫罗沛霖则是电子学与信息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苡自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教书之余从事翻译工作,首创世界名著《呼啸山庄》译名,撰写诗歌、散文等,她的丈夫赵瑞蕻是南京大学教授,翻译了《红与黑》等经典之作。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傲人成绩,实现了自我价值,有益于社会文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杨家大太太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上过一阵就不上了,小女儿根本没进过学堂,晚年的处境相当不妙。
在母亲的竭力争取下,杨苡八岁便进入天津中西女子中学。从小学到高中,她在这所学校度过了美好纯粹的十年时光。中西女校是一所贵族学校,建筑洋派、设施完备、理念先进。中西女校特别强调团结友爱、平等待人,以及热爱自己的国家、为社会服务,注重学生教养,培养淑女。在这种环境下,全校一百多位女学生关系融洽亲如姐妹,杨苡非常享受这种环境,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无话不谈、友谊长存的知己朋友。
十年间,杨苡接受了身心舒展、发展全面的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她的性格底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终生志业。“中西的课外活动太丰富了,演剧,唱歌,琴房里每月都有学琴的人开音乐会。青年会设德、智、体、群四部,出板报,救济贫民,还下乡。这些是自由参加的,周六的文学会则是师生都参加的。文学会上有演讲,有报告,还有辩论。最最热闹的,是一年一度的恳亲会和体育大会。”斑斓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了杨苡爱玩的天性。
中西女校重视音乐教育的理念,更是长久滋养了杨苡的生命。离开中西女校后,从天津、上海、香港辗转至昆明,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她和其他流亡青年们,在轮船、火车、闷罐车上,一路尽情高唱《松花江上》等抗日爱国歌曲,无所畏惧满怀欢欣去拥抱新生活。开学前的日子里,她还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合唱团活动。音乐的滋养看似无形,力量却不容小觑。中西女校对音乐的重视,天津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学者张绍祖曾特别提及,而同样曾就读于中西女校、沪上传奇女子严幼韵也酷爱音乐和钢琴,饱经生活磋磨的她晚年常常坐在钢琴前弹上一曲,将在战火与黑暗度过的日子唱成一首歌。
中西女校还特别提倡爱护自己的国家,这从学校的校歌中不难看出。中西女校有中英文校歌各两首,中文校歌除了《巍巍乎我中西》外,还有一首《中西女校》之歌,歌词中有“勉为国家栋梁,鹏程万里,不可限量,为我祖国发光”的句子。杨苡的口述中也时时处处能见到她对国家发自肺腑的热爱。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杨苡和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她们内心排斥英文教育,私下开玩笑把说英文叫“放洋屁”,毕业演出时,杨苡更是带头提出要用中文演出《玩偶之家》。她崇拜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大着胆子给她写信,信中特别提出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中国人常常是丑化的,而她从不演辱华的电影,所以对她无比喜爱。瑙玛·希拉给她回了信,寄来亲笔签名照片,这让青年杨苡激动莫名。在毕业时,按照惯例,班级同学要送学校礼物,杨苡主动提议要送学校旗杆,她们班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最深,因为受到日本人的侵略,他们特别想看到国旗飘扬起来。
杨苡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轻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杨苡和她的同代人无须号召,即用坚定不移的行动践行了这一点。
求学西南联大,走上翻译之路
中西女校十年的教育,使杨苡得到全面的素质提升,激发出炽热的爱国精神。中西女校毕业以后,她获得保送南开大学的资格。此时,日军进犯,“七七事件”爆发,天津沦陷,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联合内迁,先落脚长沙后到达云南,共同成立西南联大。而杨苡更为在意的却是终于可以离家,了结她在时代洪流与家庭束缚碰撞下的内心苦闷。
辗转到达昆明以后,在开学前的一段时日,她体会到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报名漫画班,参加百人大合唱,排练抗日歌曲,演话剧拍电影,一切都由自己做主。这段时间她在昆明搬了几次家,青云街8号寓所最值得一提。在这里,她和流亡的国立北平艺专教务长郑颖荪住第一进,杨振声一家和沈从文住第二进,曾经刺杀孙传芳的民国女侠施剑翘和她弟弟住第三进。朱自清和沈从文还曾在杨苡住的房子外编大一国文。这段日子里,她在沈从文等先生的介绍下,接触了大量进步人士,也与沈从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初次见面,沈从文就对她说:“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吗?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岁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在此后的岁月中,沈从文更是成了杨苡的人生导师、莫逆之交。
杨苡十七岁开始写诗,抒发少女心事,虽不喜古典文学,但是对中文产生兴趣,所以保送南开时她选择的是中文系。而在大学阶段,由中文系转到外文系,则是受了沈从文的影响。杨苡回忆道:“我上联大念的是外文系,就是沈先生帮我拿的主意。……沈先生的意思倒是很明确,他不懂外语,对外语却很看重,说我原来在教会中学那么多年,学中文的话,扔了外语太可惜,进中文系,就一天到晚跟线装书打交道了。”杨苡地道扎实的英文基础是在中西女校十年打下的,从小学就开始学英文,到初中开始用英文授课,古希腊史、文学,甚至是数学、物理、化学,都是英文课本。虽然西南联大使用的教材也大多是英文教材,但是杨苡与其他普通学校毕业同学相比,有着十年的英文基础。沈从文看清了这一点,劝她改入外文系。就这样,杨苡学习外文,逐渐走上了翻译之路。
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在特殊时代不得已形成的一个大学联合体,虽地处偏远、条件落后,却孕育出了足以令世界惊叹的文学、艺术、科学大师。诞生于硝烟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从联大走出的学子,无不对之魂牵梦绕,何兆武先生《上学记》就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杨苡在口述中也说“联大气氛特别宽松,学生是很自由的,去不去上课,根本没人管,上哪门课,头一次去的时候,把听课证交给讲课的老师就完了。总之,在联大,大体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这么自由,我特别喜欢联大自由的氛围”。
西南联大上课的老师可谓名家荟萃,皮名举讲“西洋通史”,陈序经讲“社会学”,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等合教“大一国文”,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陈福田讲英国小说,莫泮芹讲英国散文,吴达元、林文铮教法语,吴宓上“欧洲文学史”,外文系主任则是叶公超,这为杨苡将来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极好的基础。除了杨苡,西南联大培养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家不可胜数,许国璋、巫宁坤、查良铮、许渊冲、陈羽纶等等,他们从战火中成长,“学贯中西,心怀天下”,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和文化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谈起西南联大的大师时,杨苡的口气像小女孩一般天真烂漫,“我们也挑老师,有的老师也不好。有的老师明明很有趣,比如闻一多,但他又教《诗经》这些”“吴宓教欧洲文学史,但我们不觉得特别好。发音,陕西调的”。
杨苡从不认为自己是勤学之人,学习也以好玩有趣为导向,这与同在西南联大的丈夫赵瑞蕻的用功努力形成极有意思的对照。但或许正是这种纯粹和不求结果的赤子之心,才使得她在此后翻译作品时做到心无旁骛,灵感迸现。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梁实秋曾译为《咆哮山庄》,杨苡重译时一直觉得译名不妥,在翻译此书期间,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感觉到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宛如凯瑟琳的哭泣,她反复念着Wuthering Heights,现实的感受与书中的情境交织,得出“呼啸山庄”这神来一笔的书名。杨苡始终觉得翻译好玩,对她来说翻译是一种快乐,她秉承“信、达、雅”的翻译理念,忠实作者原文,努力使译文易懂、流畅、文辞优美。
在杨苡的翻译道路上,巴金也是一位重要引路人。杨苡十七岁即开始给巴金写信,1987年二人的通信曾结集出版为《雪泥集》,收录书信六十封。巴金去世后,201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又增订出版《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收录二人书信六十七封。由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巴金始终对杨苡的翻译工作极为关注,虽有严厉的批评,更有热情的鼓励,同时还大力推荐发表,这对早已成名且工作繁忙的巴金来说,实属难得。对于杨苡的代表译著《呼啸山庄》,数十年中,从想法诞生到翻译出版,巴金始终鼓励、不遗余力地督促,最终孕育出这部作品。1945年,巴金来信称“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从沈从文到巴金,前辈的提携、鼓励,点燃了杨苡绚烂华彩的文学翻译生命之光。杨苡则以其独有的豁达随性、机敏聪慧,为中国当代的翻译事业增添了一抹不容忽视的彩色记忆。
2022年10月,杨苡先生103岁华诞之时,中国作家协会特别致以贺信,信中称“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的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奇迹”。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杨苡先生风华百年的人生历程,精准把握了她所取得的众所瞩目的翻译成绩。杨先生从旧时代走来,在山河破碎之际依旧坚持读书,在困顿的生活罅隙中从事热爱的翻译工作,这些对前半生的深情回忆,均凝练在了这本《杨苡口述自传》中。
(作者:井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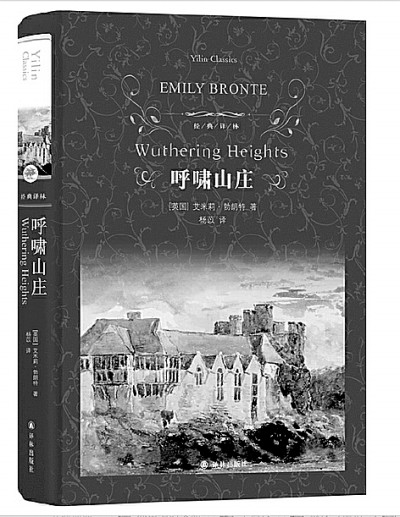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