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若要举出与紫砂结缘深厚的当代作家,徐风,必是头一个。从2005年至今,他持续书写紫砂近20年,创作了关于紫砂的小说,也为两位紫砂大师写过传记。今年,他又拿出了一部新著——《做壶》。
《做壶》,名字着实朴素,却蕴含着对紫砂书写的一次突破。这突破不在“壶”,而在“做”。
一
谈壶,古已有之。晚明时,紫砂壶从日用器具中超拔出来,作为风雅之物,进入文人生活。吴门绅士文震亨在他的“明代男人格调指南”《长物志》里就说:“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文震亨提及了一串紫砂壶的名字,供春、提梁、卧瓜、双桃、八棱细花、青花白地,说它们哪些贵,哪些俗,哪些不雅,哪些古洁,哪些适用,哪些不可用。类似的文字,翻翻古籍,能寻出不少来。
谈及紫砂壶,文人往往舌灿莲花,什么“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但关于如何“做”壶,他们却总是缄默不语。毕竟,占有物品可以标榜品位,使用物品能够制造区隔,至于制作嘛,那是匠人的事儿。雕虫之技,算不得高雅的人文知识,不值得细究,更无须记录。
倒也不必责怪古代文人势利虚荣。他们只谈“壶”,不谈“做”,不全因为“不屑”,也是因为“不能”。紫砂壶的制作,和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技艺一样,属于一种难以言说的“隐性知识”。技艺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包含着无数细小的日常行动,与掌握它的匠人不可分离。它的延续靠的是师徒相授、父子秘传,很难用语言、文字、图表、符号来表述。如此一来,技艺愈是高超,就显得愈加神秘,比如庖丁解牛、扁鹊治病、干将莫邪铸剑、鲁班造木鸢,皆有传奇色彩。然而,神秘也意味着封闭,它或许对创作故事有利,却无益于技术的积累、转移、传递。
懂得了古代文人的不屑与不能,便能明白徐风《做壶》的突破与创新。他用清晰晓畅的文字复原了紫砂古法制壶的技艺:他细细介绍了十几种工具,泥凳、明针、线石、竹篦只、木鸡蛋、独个、木转盘、搭子、虚砣、矩车;从容地讲述着制壶的流程,打泥片、打身筒、一捺底、擀身筒、做壶盖壶颈壶钮、搓嘴、打印章,等等。隐藏的线索被一一揭露,微妙的细节被一个个展示。读了《做壶》之后,我觉得自个儿看待案上那把石瓢壶的眼光都变得温柔起来。之前只当它是个喝茶的器具,是徐风的文字带我追溯了它形成的轨迹,叫我看见了这安静物件中凝聚着的人的丰富行动,和一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精神。徐风说,他写这本书是想“让不懂壶的人能看懂做壶的奥秘,并且生出许多意趣和怀想;让懂壶的人读后也觉得受用,从中获得他们之前没有的视野和认知。”这份野心不小,难度也不小。他坦言“很多生涩的术语、行话,做壶过程中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手势、做法,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常常让我在写作中举步维艰”。是的,驾驭文字的高手,更加深谙文字的局限。无论多么精微的语言,都有难以抵达的地方。徐风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合作者——制壶行家葛陶中先生。他们俩,一个不厌其烦地演示、讲解,一个竭尽全力地追慕、记述;一个要想着如何把技艺从自个儿身上传递出去,一个要思考怎样把默会的知识搬挪到书本上;一个是用紫砂泥做壶,一个是用文字做壶。因此,《做壶》是一本充满力量的书。它消散了制作紫砂壶的神秘光晕,打破了古老技艺的封闭性。它使得“古法制壶”进入了可以分享的知识网络,这对社会、对技艺,皆有益。
《做壶》的这个“做”字,体现出对双手的最大敬意。人们有时会把手和脑对立起来,膜拜智识,轻视劳作。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桑内特在《匠人》一书反思了现代文化的这一弊病,提出“制作就是思考”。《做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制壶的过程中,紫砂艺人要面对各种挑战,小到如何对付泥料,怎样提升壶嘴的精气神,大到如何面对传统,要不要创新,怎样创新。他们必须见招拆招,拿出自己的方案来,每一步都要思考,每一步都得决断。书中收录了许多葛陶中做壶的照片,几乎每张照片中都会出现他的双手。将这些图片浏览一遍,会看到一块泥巴如何在这双巧手的摆布下,层层推展,最终成为一把形神兼备的紫砂壶。图片展现的创造过程,宁静、单纯,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那双手,拿捏着泥巴,却与玲珑的心思、缜密的头脑相连相通。
二
我喜欢“做壶”这个书名,它虽素朴,却有股子勃勃的劲儿。做壶、做事、做人,关键都在这一“做”字。徐风将“做”字背后的道理娓娓道来。比如等待,“如果给一块砂土赋予灵性,它会知道这是成大事之前的必然功课,它是等得起的”;还有顺应,“‘征服’是一个生硬的词,做壶的词典里,应该屏蔽它。顺应,就是延伸、发挥、利用泥性的长处”;至于速度,“片面追求快,壶上就会有火气、暴气、戾气”;还有精神状态,“一张泥凳,就是壶手的精神状态。干净、利落、井井有条。看一个艺人壶做得好坏,瞄一眼他的泥凳就知道了”。《做壶》里有不少这样恰到好处的领悟与生发。做壶与做事,乃至做人,本质并无不同。任何技艺,终究是打磨人生;精进匠艺的同时,也在淬炼着灵魂。
《做壶》里有一份可贵的自觉与担当。徐风说,他之所以决心写一部“古法制壶”的书,是忧心古法会随着艺人的离开而消泯于时光中,自己作为一个“知情者、写作者”,若不详尽地记录、传承,“本身就是一种遗憾甚至罪过”。可是,徐风并不是古法亦步亦趋的“搬运工”,而是将自己对紫砂艺术的心得与洞见融入关于做壶的讲述中。传统本就不是什么纯然客观的存在,它的意义有赖于后人的理解与体悟。认识和体悟到达哪里,传统的价值才能抵达那里。徐风用他的思考和文字,激活了传统,让今天的读者可以从这一古老技艺中获得启发、滋养。凭这一点,我当向他敛衽致意。
(作者:李晓愚,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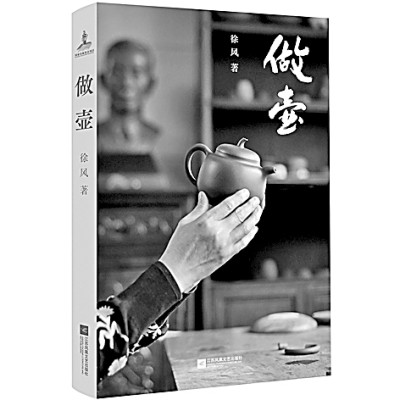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